

↻ 转自“南风窗 ”丨作者:赵佳佳
2025年中秋前,55岁的陈年喜乘坐27个小时的火车,从家乡陕西峡河赶到广州,参加在九龙湖阿那亚举办的新书分享会。
出发前他把原本订好的机票退掉,否则坐飞机的时候,将耳鸣得严重。他的右耳早已听不见。
作为曾经的矿工,炸药爆裂的声响、矿洞低矮逼仄的空间、岩层崩解时弥散的粉尘,在16年间为他带来的不是金沙,而是耳聋、颈椎受损,和尘肺病。
峡河与矿洞,是贯穿陈年喜所有写作的主题,他称之为两套“皮壳”。借助皮壳,他要写的是人,写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时代与命运面前,人的情感和所思所想是什么样。这也是他新出版的散文集《人间旅馆》仍旧绕不开的主题。

《人间旅馆》
在命运跌宕中挣扎半生以后,他自称为“失败者”,浑身集齐了散漫、焦虑、感性、没头没尾的元素。
即便以诗人和作家的身份开启他的后半生,陈年喜也始终认为自己是工人群体中的一员,他讲话的声音沙哑,有金属和尘土的声响。
身体的痕迹提示着他立足的阶层。和他沿途遇见的所有同伴一样,大家都曾妄图通过钻进矿洞改写人生,但最终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一个人成功改变人生巨流的走向。
经历得多了,他从一个“愤青”,最终变成一个对命运束手就擒的人。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叫《微尘》,英文译名是“Nobody”,用来概括他自己,和跟他殊途同归的无名之人。

《微尘》
在他的笔下,再生死攸关的时刻,也罕见纠缠。前一秒还在写即将冻死在岭上,下一秒就开始讲危机解除之后的事情了。
从人生龙活虎到成为烤焦的尸骸,也就只是一台戏的时间。一粒落石、一场山体滑坡、一次公路边的停留,都能摧折人的生命或者意志。但他的笔调始终平实,仿佛人间的困苦不过转瞬。
这是他的哲学和他的史观。他说,本质上历史可能是在原地踏步的,并未曾像河流一样波澜式往前推进。
在时间的伟力面前,人的挣扎是徒劳,而真正重要的是活着本身。

呐喊无声
南风窗:在阅读《人间旅馆》的过程中,我发现你的写作呈现出一种显著的对于人生束手就擒的姿态。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生命的状态?
陈年喜:我始终觉得生活永远是强大的,而我们每个人其实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在现实世界里不断地“缴枪不杀”的过程。我有一本书就叫《微尘》。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粒尘埃,飘飘荡荡,人生朝哪个方向走,朝哪个方向落,常常身不由己。
曾经有一个时代,你觉得人无比强大,人定胜天,人是可以战胜命运、可以左右历史的。但在我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恰恰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的所有作品中能看到的人生,永远是无奈的,永远是无力的。
当然,在无奈无力中也有个人色彩。我觉得文学应该是表现在那样一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命运面前、生活面前、时代面前,个人的挣扎、不甘、呐喊,或者是那种呐喊无声。

陈年喜
所谓的诗歌,永远表达的是人,是人的情感,是人的所思所想。这也是我一直理解的文学。哪怕是借助了我个人的矿山生活这样一个皮壳,借助了我家乡生活这样一个地理的皮壳,其实本身还是表达,在这样一个强大的舞台之下,人是什么样的。
南风窗:在自序里,你写道:“高中毕业那年,苦于我没有出路和希望,母亲翻山越岭去找一位先生为我算命。先生说,此人命带驿马,一生奔波,不得安宁。我一路挣扎,拒绝命运的安排,但历程和结果,仿佛都在验证先生的成谶一语。”
你出生于1970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刚好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那个时候其实高中毕业是一个学历和文化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状态,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之下,在你成年的起步时期、命运奠定的关键阶段,还是有东西阻碍了你的出路?
陈年喜: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南北特别不同,物产和机遇特别不同。
如果在我那个年代,生在南方,可能我首先考虑的不是吃饭问题。但是我在北方,我首先考虑的是吃饭问题,是怎么活下去。
直到现在,在我家乡,如果单纯地依靠当地的条件,吃饭仍非常困难。基本上没有土地,没有任何机遇。所以我在高中毕业后续的好多年里,是非常茫然的,做了很多年的挣扎。

没有土地就没有机遇 / 图源:视觉中国
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回家里,陪着父母劳动了很多年。我们土地广种薄收,种了很多地,收了很少的粮食,吃饭都非常困难。在其中的我特别茫然。
当然在80年代末的北方,高中毕业在乡村里算半个知识分子,还是有机会。我原来在政府做过好多年,帮政府做新闻宣传,当然也是在编制之外。我需要做很多年的努力,可能能进体制,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熬的过程。其实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耐心熬下去。
我在家里还自学过好多年的法律,关于民法的、刑法的。读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书,然后写了很多那些专业的法律文书,我觉得那条路也挺难走的。
后来我也做过好多年关于中国文物的——青铜器的、玉器的、字画的这样的研究。其实我当时的理想是做一个鉴宝人。秦岭的南部和北部诞生过伟大的王朝,它的两边有特别广阔的墓葬,墓葬下有无数多的藏品,所以它有庞大的盗墓人也有庞大的鉴宝人。
我读了很多关于文物的书,但因为永远没有实物对照,纸上谈兵,所以尽管能大致断定一个文物出自什么年代,知晓它的画风、结构、成分,但是鉴定真品和赝品,非常艰难。
总的来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做了很多年的挣扎,但是到了1999年,孩子出生,我和父母完全不在一块生活了,我要承担起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后来我就不得不去了矿山,一去16年,经历了无数的生死。

世界游荡者
南风窗:我在你的作品之中读到非常多关于色彩的呈现。你特别喜欢写“瓦蓝瓦蓝的天空”,特别喜欢写别人有很好看的红色的摩托车、红色的马甲、红色的黄栌树,各种关于红色的意象。
从你对颜色的运用和书写中能够看到,你有一种从人群之中凸显自身的渴望;也能看出你在人生早期的挣扎阶段,曾试图从人群之中跳脱出去,实现个人梦想。
你刚刚提到了1999年,那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那时候你进入矿山也是因为有钱可赚,改变命运是有可能的。但接下来又经历了哪几个重要的转折,让你最终成为了现在这样,对人生感到无奈?
陈年喜:我的人生确实是经历了好多次的转折。1999年的转折,就是我从乡村真正地和世界发生关系,后来的16年中,我经历了天南海北的游荡。但这也是让我对世界有特别不一样的认识的历程。

《十三邀》剧照
乡村世界是特别封闭的,在那里,我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很深刻。我觉得这个世界无非是黑和白、忠和奸、好和坏的二元对立。但后来我发现,这个世界远远不是如此。
我到了藏区,发现所谓的火葬,就是把一个人像烧红薯一样烧熟的过程,他们对人的生死伦理和汉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我到了叶尔羌流域的某个村庄,茫茫戈壁之上,突然有一个很小的湖泊,旁边住了几户人。没有所谓的茫茫草地,没有成片的牛羊,就是依托一个小小的水泡子,祖祖辈辈生活下来。他们和世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们永远没有到过乌鲁木齐,一生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在我们汉文化的眼光里,会觉得这些人是生不如死,完全是一个和任何动物没有区别的人生。但是我到了哈木斯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们也有个人自洽的、完全成熟的支撑着一代代人活下来的伦理。
他们有非常美妙的音乐。当然他们对五线谱完全不懂,但他们能跳出特别美好的舞蹈,也在歌曲当中创造出非常美妙的旋律,能用锅碗瓢盆演化过来的东西作为乐器,吹拉弹唱。他们依然是很快乐的。
于是我发现,汉文化中对人的定义,包括哲学上的定义、社会学上的定义,很多方面是不成立的,或者是狭窄的。现实的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有些东西是我们在纸质书上永远学不到的。至少我对这个世界、对人,有了特别不一样的认识。
当我走在茫茫戈壁之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突然发现人并不是强大的。人特别渺小。
当我走在人群中,走在街道上,我会变得很矫情。因为我有任何困难,别人可以帮到我。但是在一个生死无着的世界中,你和一只蚂蚁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个时候,你会把身上所有的铅华都洗掉,还原到你真正是什么样的人。

《后会无期》剧照
西方有一个哲学叫身体哲学,身体给你的答案可能更准确、更直接。而我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并不来自书本,或所谓的知识结构,大部分来自个人的身体感受。
我的文本,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是出自我个人的感受。所以个人的语言体系,一定和他自身接触的、看到的、经历的那些具体的事物有关系。
南风窗:因为有了黑才能看到白,我现在特别想知道那个白。当你在阅历这些生活的时候,在你写到的那些苦难的背后,你感受的幸福源于哪些地方?
陈年喜:我觉得哪怕是再苦的人生,其实都有个人的幸福。
当我找到一个还算对口的工作时,那一刻我挺幸福的。当我顺利地拿到工资时,那一刻我也挺幸福的。当我碰到一个和我有话可说的工友的时候,也是人生的一个小幸福。
其实我的矿山生活,包括我现在所有的生活,都挺沉重的,也非常孤独。但是依然还是有一些东西支撑着我,不断地去走过。

陈年喜谈矿山生活 /《十三邀》剧照
我常常被作为一个苦难文学的代表。甚至有很多人说,“他就是靠卖惨博眼球”。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首先,我觉得苦难本身就是生活的本色,没有一个人说他人生是特别幸福的。苦难是必然的,幸福是偶然的。我表达的、呈现的、写出的,只是我经历的、看到的那一部分,也是真正生活的一部分。
而文学永远需要给人希望。我虽然写出了生活沉重的那一部分,但是大家在我作品中读到的不完全是绝望。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我们怎样对明天有更好的判断和抉择?还是真正地去看清、认识到某些事物的本质,可能你对未来可以少一些盲判,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判断,这是重要的。

无名的记忆
南风窗:你的每一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可能都有具体的一个人物原型。那些人物很显然都对你非常乐意敞开心扉,我觉得特别神奇,除非是对他人真的抱有纯粹的好奇心,否则他人是无法很容易地跟你交心的。
与人的深度交付这个事情,在人的命运之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些人愿意把自己人生的故事、秘密交付给你?
陈年喜:刘震云有一部长篇小说叫《一句顶一万句》,它有一个主题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孤独的,人终生在寻找的是一个可以和你说话的人。人生确实是如此。

《一句顶一万句》
在这本书中,我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当时在甘南,大家不知道的是,甘肃有一个地方人称是甘肃的江南,就是在秦岭的南部,发现了庞大的金矿。我当时在那里干金矿,认识了一个人。
这个人住在那样一个村子里,村子周围山上有很多的金矿,已经在地表冒头了,矿脉延伸到地里。村子所有人在干什么呢?在挖掘那些冒头的金矿,经过冶炼氰化,这就是他们经济的来源。
他此前是做向导的。这个地方来了天南海北无数的淘金客,这个人给一拨一拨人去当向导,在十年中找了很多的金矿。有些情况他告诉了他的雇主,有些情况他没有告诉。他画了无数的地图,做了无数的标识,他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矿脉。
他的人生理想是,有一天他有能力了,就去开采这些金矿。但是他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个体很难去做这个事情。
但他碰到我了之后,因为我们关系的慢慢加深,他觉得我是可以托付的。我非常熟悉黄金的开采到冶炼,他一直教唆我说:“你不要再干了,你永远没有出息,跟着我干,我们一起去淘金。”

也许有能力的时候就可以开采金矿 / AI制图(诺言)
他甚至有一次带着我还有我一个同伴,专门走了一天,到他做过标识的地方,但是始终没有找到金矿。我觉得很遗憾,但是天黑了,在茫茫大山之中,不得不返回。返回的时候,在一条小河里,我们口渴去喝水,用一个玻璃瓶把砂石摇一摇,发现后面有很多比头发还细的狗毛子金。
但他后来很不幸,在我们计划还没实现的时候,他得了肺癌,再也实现不了这个理想。
他家门口旁边有两棵特别粗的黄栌树,他在走之前有一个理想,说如果能把这两棵树作为棺材,是他最满足的。后来,我和我的同伴用炸药把这两棵巨大的黄栌树炸倒了,给他做了棺材,送上山埋掉了。
这是我在人生当中碰到的无数可以相托的朋友中的一个,也是我在无数作品当中写到的一个人。当然我也写出了他个人的悲剧,写出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的挣扎、渺小、绝望和希望。人永远都是一样,人永远不一样。

《十三邀》剧照
我没有把一个人拔高,也没有把一个人降低。文学没有高于生活,文学永远也不低于生活,它和生活是平行的、互相映照的、互相看见的。
南风窗:为什么你认为写下你经历的所有这些人的生生死死是重要的?为什么你所写作的这个阶层的图景,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甚至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有价值的?
陈年喜:就像本雅明墓碑上的一句话,“历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在真正推动历史往前走的力量里,籍籍无名的人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每一个个体,本无意来推动历史,但是在完成他个人生命的同时,其实也在给世界注入无限的色彩。
我个人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并不是像河流一样波澜式往前推进,可能是原地踏步的,或者是螺旋式的、回环式的。今天的人类并不比200年前、500年前甚至1000年前的人类更高级。写出真正的人的状态,人在这个世界的快乐和无奈,这就是文学应该去完成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不断地愿意去读古典文学,读遥远的唐时代的诗,或更早的《诗经》,目的还是想回看那个时代人是怎么样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去他们身上寻找映照。
在那个时代,他们也快乐,也有过友谊,也有过爱情。我们所有的阅读,也无非是在别人作品当中去寻找你自己而已。
本文作者:赵佳佳
本文授权转载自南风窗
关注它,能让你听到更多真话,
多一分对世界的理解。


文学杂志小传
转载、商务、作者招募合作丨请后台联系,凡本平台显示“原创”标识的文章均可联系编辑转载,未经授权转载视为抄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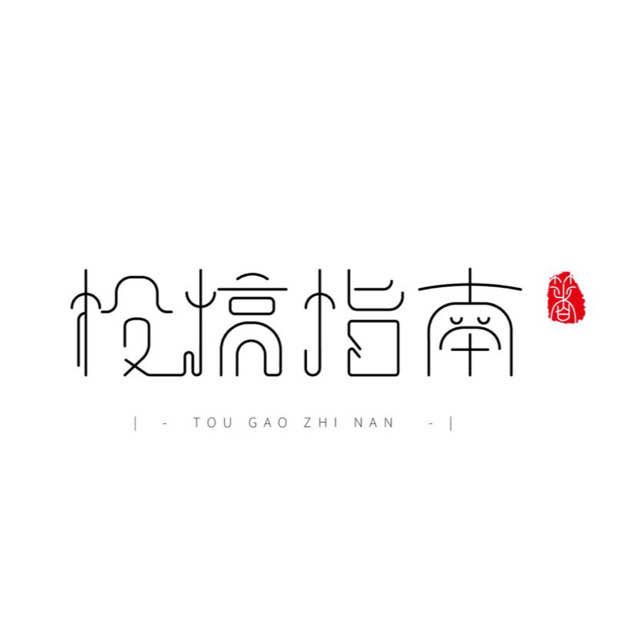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