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们!在下张大少。
本文通过对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装饰艺术的对称性分析,给出了起源于此的不同对称群和反对称群的证据,并作为一种“装饰原型”载入装饰艺术史。
简介
纵观历史,几何学和绘画艺术之间始终存在着联系。当我们把对称理论应用于装饰艺术的研究时,这些联系就变得特别明显了。因此,装饰艺术被H.Weyl [39]称为“以隐含形式给出的高等数学的最古老方面”,被A.Speiser称为“史前的群论”。
Polya[27]和A. Speiser[34]提出的从对称性理论的角度研究不同文化的装饰品的想法,得到了20世纪对称性理论的深入发展支持。这导致了一整套作品的出现,这些作品主要致力于古代文明的装饰艺术,对装饰艺术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文化(埃及、阿拉伯、摩尔人等)[2,14,16,17,25,37],以及民族装饰艺术[9,10,11]。只有在最近的一些作品中,研究才转向了装饰艺术的根源,即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装饰艺术[22]。本文中的图案是从[22]中出现的更广泛的集合中改编的,读者还可以从中找到更详细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具体参考资料。经典的对称-不对称和彩色对称理论的延伸,使得对新石器时代和古代文明的装饰艺术中的“黑白”[19,20,39]和彩色装饰图案进行更深刻的分析成为可能。
这部作品给出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装饰艺术的对称性分析结果。它致力于寻找“装饰的原型”——完整的装饰艺术的普遍基础。观赏艺术的发展与人类的起源一起开始。它代表了人类试图注意、理解和表达规律性的最古老的记录之一——这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
最后的结论是,从对称理论的角度来讨论的大多数装饰图案,其年代比我们所期望的要早得多。这就把装饰艺术——几何认知的最古老的方面——的开始追溯到古代文明之前的几千年,即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由于观赏性艺术大多局限于观赏性图案的二维平面表现,因此,从对称理论的角度来看,这门艺术的主题是平面对称群:玫瑰花结、饰带和装饰物的对称群。玫瑰花结的离散对称群由两个无限类组成:循环群和二面体群。循环群Cn是由n阶旋转产生的。二面体群Dn是由在n阶旋转中心不变点相交的两条直线上的两个反射产生的。七个离散的饰带对称群可用符号表示为:11、19、12、m1、1m、mg和mm。在这些简洁的符号中,省略平移符号p, g表示滑移反射,m表示反射,n (n=1,2)表示 n阶旋转。所有符号都在坐标意义下处理。在第一个位置的对称元素垂直于平移轴,而在第二个位置的对称元素平行或垂直于平移方向(只适用于二重旋转)。
类似地,在装饰物对称群的符号中,符号p表示二维平移子组,而符号m、g、n (n=2,3,4,6)分别具有与饰带对称群相同的含义。当我们谈论饰带对称的连续群时,连续平移的存在用下标0表示,而在反对称群中,反发生器用’表示。反对称群也由群/子群符号G/H表示[30]。
我们所说的 "前科学时期 "是指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涵盖了从公元前25000-10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末的时期,那时我们有了第一个字母表。
在没有书面资料的情况下,对史前时期几何的研究是基于对人工制品的分析,这些人工制品以隐含的形式提供几何知识的信息。在提到的人工制品中,我们很少区分它们。最古老的是装饰图案。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骨刻、雕刻和壁画。后来,我们有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瓷装饰图案,通过雕刻、压制、绘画或着色获得,以及新石器时代的建筑物品和建筑,即所谓的巨石纪念碑。
玫瑰花结
最简单的装饰图案是玫瑰花结,这是具有不变点的对称图形,对应于对称群Cn和Dn。在Shubnikov的表示法中,它们分别用n和nm表示[30]。
图1.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装饰艺术中的太阳符号的变化。
玫瑰花环的连续对称群D∞(∞m)对应于最大的对称花环——圆。由于最大的视觉和结构的简单性以及最大的对称性,圆代表了主要的几何形状——几何原型。在装饰艺术中,它出现在旧石器时代,作为独立的花环或与一些对称程度较低的同心花环相结合,通常被圈在或刻在一个圆里。由于D∞(∞m)组包含了所有其他对称性的花环组,作为子组,较低对称度的花环通常是由圆的去对称化而得到的。由于其视觉上的几何特性:完整、紧凑、有界和结构段的均匀性,圆可以作为完整和完美的普遍象征。在装饰艺术的初期,圆成为太阳的象征,在历史上一直如此(图1)。
玫瑰花环的连续对称群C∞(∞)是围绕固定点的所有旋转的群。对它的物理解释可以是一个围绕中心均匀旋转的圆,所以在静态形式下,这个对称群在视觉上只能用纹理来解释[31]:通过使用一个不对称的图形,按照所需的对称性C∞(∞)进行统计分布。
螺旋是最古老的动态视觉符号之一。在视觉上,它暗示了围绕不变点的旋转运动,并可以作为连续对称群C∞(∞)的符号解释。在装饰艺术中,螺旋已经出现在旧石器时代,作为一个独立的装饰图案,或以双螺旋的形式出现,双螺旋是由两倍旋转产生的对称群C2(2)。
在基本的几何形式中,一条线段,通常按照基本的自然方向——垂直线和水平线放置。线段对应于对称群D2(2m),由两个反射产生:一个是垂直于镜面的线,另一个是与线段平行的反射线。然而,从视觉感知的角度来看,由于视觉和引力主导的作用,垂直线,我们在视觉上体验到线段的对称性为D1(m)。在这种情况下,水平反射被忽略了。垂直和水平线段的组合导致了具有对称群D1(m)、D2(2m)或D4(4n)的交叉形式。具有对称性D2(2m)和 D4(4m)的玫瑰花拥有另一个基本属性:存在相互垂直的、垂直和水平的反射线。具有对称群D4(4m)的十字形的形式常常被主观地、视觉地认为是对称性D2(2m),忽略了四重旋转的存在。
对称群为D1(m)或D2 (2m)的静态玫瑰花结与人的平面对称性、其垂直姿态和与基底的垂直度有关。除了源于自然主题的理性镜像对称之外,我们在装饰艺术中还有符号对称D1(m)的不同方面:复制的图形、双头动物等。这些例子主要源于垂直镜像对称作为视觉优势的普遍使用。
在旧石器时代的装饰艺术中,我们也有对称群Dn(Nm)的玫瑰花环:D3(3m),D4(4m)和D6(6n),以及相应的规则多边形:等边三角形、正方形和正六边形(图2)。对于玫瑰花环,不遵守晶体限制原则(n=1,2,3,4,6)。无论如何,对于上述n值,流行的是具有对称群Dn(Nm)的玫瑰花环。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我们也有使用正五边形和五角形的具有对称群Ds(Sm)的玫瑰花环。公元前7世纪,H.S.M.Coxeter[7,pp.8]首次发现了五角星。具有对称群Dn(Nm)的玫瑰花环的视觉特征是稳定性、平稳性和无对映体。对构,即同一图形的“右”和“左”修饰的存在,所有图形都具有不包含间接对称变换的对称群。
与对称群Dn(nm)的静态花环相反,对称群Cn(n)的花环(如对称群C3(3)的三重花环,对称群C4(4)的卍字花环)在视觉上是动态花环。也有可能出现对映的修改,暗示旋转运动的印象(图2)。
在下一阶段的装饰艺术发展中,在新石器时代,在了解了玫瑰花对称性所依据的对称规律并解决了它们的基本几何结构之后,玫瑰花的多样性就增加了。紧随其后的是植物和动物性图案的应用,以及改变基本区域的形式。此外,同心花环的叠加导致不对称化——降低到较低的对称度——是非常常见的。
图2: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装饰艺术中具有对称群Cn(N)和Dn(Nm)的玫瑰花环实例:(A)法国旧石器时代,D4(4m);(B)Maz d‘Azil,D2(2m)和D4(4m);(C)Laugerie Basse,C2(2);(D)中亚新石器时代陶瓷,C4(4),公元前6000年左右。
在新石器时代,对于双色陶器,我们有反对称的 "黑-白 "花环(图3)。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称性既可以被视为获得某个对称群索引2的子组的去对称化模式,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对称形式。在反对称群的表格中,每个群都用群/子群符号G/H来表示[30],后面有一个(反)生成器的系统。因子群G/H与2阶的循环群同构,即 "黑"-"白 "的颜色变化群。
在反对称群的情况下,有可能把 "黑"-"白 "的颜色变化解释为一些物理或几何二价属性的交替变化。在装饰艺术中,提到的颜色变化引入了空间成分,暗示了 "前面"-"后面"、"上面"-"下面 "的关系。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它引入了重复一致的数字和 "数字 "与 "背景 "的具体对等关系之间的对比,从而在象征意义上表达了一种动态的冲突和二元性。
图3:新石器时代反对称花环D8/C8,Hajji Mohammed,约公元前5000年。
在装饰艺术中,有规则着色意义上的颜色的使用,即反对称和彩色对称,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未被探索的领域。因此,在装饰艺术的历史上,我们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是它的顶峰,在这个时期,在解决了基本的技术和结构问题之后,艺术研究、想象力、各种主题和装饰性的新可能性被打开了。
饰带(一维图案)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马格德林时期文化,约公元前25000-10000年),我们发现了最古老的饰带对称群的例子,即没有不变点和有不变线的平面对称群。我们有所有七个对称群的例子:11,19,12,m1,1m,mg,mm,以及两个视觉上可呈现的连续对称群的饰带om1和omm。
饰带通常是通过应用玫瑰花结的构建方法获得的,即最初的基序——玫瑰花结的平移倍增,玫瑰花结的对称性直接决定了所获得的饰带的对称性。饰带的另一个起源是自然界中发现的模型,它们本身具有饰带的对称性(图4)。
饰带是由自然界中的模型衍生出来的,可以举例说明:鹿群被还原为对称群11的饰带,崇拜舞的图案被呈现为对称群m1的饰带。对称群12和mg的饰带可以被认为是风格化的波浪。自然界中具有19和1m对称群的模型在某些植物的叶子分布中可以找到;它们在装饰艺术中成为建造相应饰带的借口。自然界中平面对称的重要性以及对称群D1(m)和D2(2m)的花冠的数量,导致了对称群mm的饰带的出现和频繁出现。这些饰带可以通过对称群D2(2m)的玫瑰花的平移倍增而得到,其中平移轴与玫瑰花的一条反射线平行。饰带的对称群mm是饰带的最大离散对称群,由反射产生。所有其他饰带的对称群都是mm群的子群。因此,mm群可以通过去对称化推导出所有其他饰带的对称群。所有离散饰带的例子:对称群在旧石器时代的装饰艺术中可以找到。
除了有具体意义的饰带,这些饰带是基于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材料模型,某些饰带的出现也是由于许多自然现象(昼夜的变化、季节、潮汐、月相等)的周期性变化造成的。与此同时,相应的饰带代表了记录自然现象周期性变化的最古老的尝试,即历法的第一种形式。这些饰带也可以被理解为记录数量的一种方式,作为计数板,表明计数的开始和记录计数的结果,即自然数的出现。
图4:旧石器时代装饰艺术中的饰带对称群的例子。
某些 "几何 "饰带由于其象征意义成为了视觉交流的手段。这一点可以从民族装饰艺术中保留下来的饰带名称得到证明[32]。这种在旧石器时代确立的饰带的交流作用,在新石器时代得到了部分保留。随着其他交流形式的发展,饰带失去了其主要的象征性功能,部分或完全被其装饰性功能所取代。这一过程的开始可以在新石器时代的装饰艺术中得到记录。
饰带平移轴的极性、非极性和两极性,饰带对称群内间接对称的存在或不存在所暗示的对映性,等等。[22],代表了一些值得更详细考虑的相关几何特性。同时,它们定义了饰带的视觉特征,因此也限定了具有某些对称群的饰带可能具有的象征意义的范围。
图5:新石器时代装饰艺术中的14组反对称饰带的例子。(a) 希腊,11/11,约公元前3000年;(b) 希腊,12/12;(c) 近东,12/11,约公元前5000年;(d) 近东,1m/1m,约公元前5000年;(e) 近东,1m/11; (f)安纳托利亚,1m/1g,约公元前5000年。 (g) 近东,m1/m1;(h) 近东,ml/11;(i) 希腊,mg/m1;(j) 近东,mg/1g,约公元前5000年;(k) 安纳托利亚,mg/12;(l) Tell el Hallaf,mm/mm,约公元前4900-4500;(m) Hadlar,mm/m1,约公元前5500-5200;(n) 近东,mm/mg。
在出现频率上,除了直接来源于自然界模型的饰带外,在科学前的装饰艺术中,满足视觉熵[22]准则的饰带也占主导地位,即视觉和结构的最简单性和最大的对称性。
最古老的反对称壁画的例子,即所谓的 "黑白 "壁画,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有17个反对称壁画组中的大部分例子。进一步的调查应该表明,是否所有17种反对称的饰带群都来自于那个时期的例子。就出现的频率而言,最多的是 "黑-白"饰带,它是通过使用反对称的非对称方法从最常见的古典对称饰带中衍生出来的(图5)。
反对称条纹的出现频率也取决于反对称特性。因此,更常见的是相邻基本区域颜色相反的反对称条纹。“几何”反对称饰带对反对称饰带的支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由于自然界中动植物模型之间不存在反对称。与此相反,许多自然交替现象都伴随着二价变化(如昼夜变化等)。),早在新石器时代装饰艺术就以反对称饰带为代表。
有可能将二阶反恒等式变换(颜色变化“黑”-“白”)视为在平面上表示空间对称结构-带(其中包含不变平面和线,并且没有不变点的三维对称群)的方式。饰带的31个反对称群(7个生成+ 7个高级+ 17个初级反对称群)对应于带的31个对称群。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给了一种在平面绘画中暗示空间的可能性。除了这种可能性,反恒等式变换还有许多不同的几何或非几何解释。在史前装饰艺术中,“黑白”饰条的主要象征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装饰(二维图案)
在对称性和装饰艺术的理论中,最有趣的研究领域是装饰品的17个对称群,即没有不变的线和点的二维对称群。饰物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离散的二维平移子群,由两个独立的平移产生。发现和构建所有17个装饰品对称群的例子的困难,表现在许多具有非常丰富的装饰艺术的文化在其早期的装饰艺术中并不拥有所有这些群的例子[16,17]。在对称性的数学研究中,只有在1890年,在E.S. Fedorov的作品中才能找到装饰品对称群的完整推导,尽管这个问题也吸引了许多其他重要的数学家(例如,C. Jordan, L. Sohncke)。
图6:旧石器时代装饰艺术中具有对称群p1的装饰物的例子:(a)Chaffaud;(b) 骨刻,欧洲。
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石器时代的装饰艺术中,我们可以找到9个对称的装饰组的例子,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原因:p1,p2,pm,pmm,pmg,em,cmm,p4m和p6m[22]。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发现了另外5组对称的装饰品:pg、pgg、p4、p4g和p6。在古代文明的早期装饰艺术中可以找到p3、p3m1和p31m的对称群的例子,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可以找到。
根据旧石器时代所述的对应对称群p4m和p6m的存在,所有三种规则密铺:对称群p4m的{4,4},对称群p6m的{6,3}和{3,6},都已经知道。在旧石器时代的装饰艺术中,除了正方形、正六边形和正三角形晶格外,还发现了两种布拉维晶格:对称群p2的平行四边形晶格和对称群cmm的菱形晶格。
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装饰艺术中,关于用于获得装饰物的构造方法,我们区分了四种构造方法:饰带倍增法、玫瑰花结倍增法、布拉瓦格法和去对称化法。第一种构造方法基于通过不平行于饰带轴线的离散平移来平移重复某个饰带。由于这种构造的简单性,并且由于所有七个离散对称的饰带组的早期例子的存在,这种方法可能经常被用于装饰物的构造。在旧石器时代,它很可能用于建造对称群为p1、p2、pm、(pg)、pmg和pmm的装饰品。类似的玫瑰花结构建方法是基于玫瑰花结乘以两个独立的离散平移。获得的装饰物的对称性完全由这些平移的性质和玫瑰花结的对称群来定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装饰艺术中布拉瓦格子的出现源于自然界中的模型(例如蜂窝、不同的网状结构)。另一个原因是布拉瓦格的视觉和结构非常简单。最常见的Bravais格,即规则镶嵌{4,4}、{6,3}和{3,6},对应于反射产生的装饰物p4m和p6m的最大对称群,经常作为应用去对称化方法的基础。这种建造方法的重要性随着新石器时代(两种)彩色陶瓷的出现而增加,即随着反对称和彩色对称装饰物的出现而增加。所有这些建造方法都可能被用于科学前时期的装饰艺术。
旧石器时代的装饰品,以骨刻或石刻和图画的形式实现,由于它们指向装饰艺术的根源,因此值得特别关注。
对称群p1的装饰品是基于对称群11的饰带乘以一个离散的平移,或基于一个不对称的图形乘以两个离散的平移。由于对称程度低,它们的出现相对较少,最常出现的是自然界中的风格化不对称模型(图6)。
具有对称群p2的装饰物以最基本的形式出现:作为平行四边形的格子。旧石器时代装饰艺术的一大亮点是饰以回文图案或双螺旋、对称群为Cz (2)的玫瑰花结,其最有可能源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领土(梅津、玛尔塔)。后来,这些图案将经常用于几乎所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装饰艺术中,主要是作为波浪图案的变体。因为对称群p2的形式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所以对称群p2的饰品几乎完全局限于几何图案或象征性的风格化图案(图7)。
具有pm对称群的装饰品,由于反射的存在,属于静态装饰品的范畴。除了几何图案,还经常使用自然界中存在的具有镜像平面对称性的模型。
虽然根据[22]在旧石器时代没有发现具有对称群pg的装饰品的例子,但有理由相信它们确实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装饰艺术中,就像有饰带对称群1g的例子一样。
图7. 旧石器时代装饰艺术中具有p2对称群的装饰物实例。Mezin,乌克兰,约公元前23000-18000年;(b)西欧的旧石器时代;(c)双螺旋图案,俄罗斯Mal'ta;(d)双螺旋图案的应用,Arudy,Isturiz。
图8:旧石器时代装饰艺术中具有pmg对称群的装饰品实例。(a) 乌克兰的Mezin;(b) 西欧;(c) 爱沙尼亚的Pernak;(d) Shtetin。
图9:对称群p6m的规则镶嵌的例子:(A)(6,3),叶利塞维希,俄罗斯,公元前10000年;(B)规则镶嵌(3,6)。
关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装饰艺术中的出现频率及其变化,以对称群pmg和pmm的装饰品为主。这两种装饰物都可以通过饰带的构造方法获得,分别通过饰带mg和mm的平移倍增。对称群pmg的装饰物几乎总是以它们的主要形式出现在几何装饰物中,作为波浪图案的风格化。对称群pmg为不同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在视觉意义上表达了由反射的存在引起的静态视觉分量和由暗示交替运动的滑移反射的存在引起的动态分量之间的特定平衡(图8)。
图10:新石器时代装饰艺术中的23组反对称装饰物的例子。
由反射产生的静态装饰pmm以其最早的形式实现为矩形网格。其他形式是通过垂直于饰带轴的平移,或通过玫瑰花结构造法,将饰带与对称群mm相乘而获得的。在那里,具有对称群D2 (2m)的玫瑰花结通过垂直于玫瑰花结的相应反射线的两次平移而相乘。
对称群为cmm的装饰品在旧石器时代以菱形格子的形式出现。这些装饰物可以通过居中的方式从对称性群为pmm的装饰物中构建出来,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程序,在构成原始装饰物的镶嵌物D2(2m)之间的空隙,用相同的镶嵌物填充。
对称群cm的装饰通过同样的程序——通过中心,从对称群pm的装饰得到对称群cm的装饰。
装饰p4m和p6m的对称群对应于规则镶嵌{4,4}、{6,3}和{3,6}。由规则的六边形组成的正方形,每个顶点都有三个入射的正方形,很可能源于它在自然界的模型:蜂窝(图9)。正方形的{3,6}和{4,4}是来自同一时期,即旧石器时代。
视觉熵原理:最大的视觉和结构的简单性和最大的对称性是所有旧石器时代饰品的共同、普遍的特征。因此,在旧石器时代的装饰中,现有的九组对称装饰中有五组对应布拉瓦格,九组对称装饰中有七组包含反射,属于静态装饰的一类。在它们中,几乎完全没有对称的动力要素——极平移、极旋转和滑移反射,这是很明显的。
在新石器时代,几乎所有剩余的对称纹饰都出现了。“黑白”纹饰,即具有反对称性的纹饰,在新石器时代的纹饰艺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46组反对称装饰中有很多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装饰艺术中,特别是在近东和中东的装饰艺术中(Telel Hallaf,Hacilar,Catal Hiijiik)。如果我们把反对称群为p6m/p3m1的反对称饰品视为用反对称去对称化方法得到的经典对称饰品,我们可以增加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对称群,也可以增加对称群p3m1。
新石器时代的装饰艺术是所有装饰艺术史上不同装饰物最丰富的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装饰艺术中发现的14组对称装饰物和23组反对称装饰物的实例(图10)是关于新石器时代人们艺术创造力的最完整的见证。
对称群为p3、p3ml和p31m的装饰物在结构上存在很大问题。在古典对称意义上,它们最早出现在古代文明的装饰艺术中,或者更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装饰艺术中。
与前科学时期几何学有关的非常有趣而又探索不足的领域有:所有平面对称结构和相应的古典对称、反对称和颜色对称群的出现年代测定,从对称理论和装饰艺术的角度登记最重要的考古发掘地点,不同文化的装饰艺术之间的联系,浮雕、自然数字和历法之间的联系等。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与前科学时期数学史有关的类似问题。
参考文献
[1] Akopyan I.D., Simmetriya i asimmetriya v poznanii, Akad. Nauk Armyanskoi SSR, Erevan, 1980.
[2] Belov N.V., Moorish Patterns of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Symmetry Groups, Soviet Physics Crystallography 1 (1956), 482-483.
[3] Belov N.V., Neronova N.N., Mozaiki dlya 46 ploskih shubnikovskih grupp antisimmetrii i dlya 15 fedorovskih tsvetnih grupp, Kristallografiya 2, I, (1957), 21-22.
[4] Brunes T., The Secrets of Ancient Geometry, I, II, Rhodos, Copenhagen, 1964.
[5] Coxeter H.S.M., Introduction to Geometry, 2nd ed., Wiley, New York, 1969.
[6] Coxeter H.S.M., Regular Polytopes, 3rd ed., Dover, New York, 1973.
[7] Coxeter H.S.M., Regular Complex Polytop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4.
[8] Coxeter H.S.M., Moser W.OJ., Generators and Relations for Discrete Groups, 4th ed., Springer 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1980.
[9] Crowe D.W., The Geometry of Mrican Art I. Bakuba Art, J. Geometry 1 (1971), 169-182.
[10] Crowe D.W., The Geometry of Mrican Art, II. A Catalog of Benin Patterns, Historia Math. 2 (1975),57-71. .
[11] Crowe D.W., The Geometry of Mrican Art m. The Smoking Pipes of Begho, In The Geometric Vein, ed. C.Davis, B.Griinbaum and F.A.Sherk, Springer 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1981.
[12] Crowe D.W., Washburn D.K., Groups and Geometry in the Ceramic Art of San lldefonso, Algebras, Groups and Geometries 3 (1985), 263-277.
[13] Eves 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of Mathematic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64.
[14] Garido J., Les groupes de symetrie des ornaments employes par les anciennes civilisations du
Mexique, C.R. Acad. Sci. Paris 235 (1952),1184-1186.
[15] Hilbert D., Cohn-Vossen S., Geometry and the Imagination, Chelsea, New York,1952.
[16] Griinbaum B.,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Full Regalia, G string, or Nothing, Math. Inteligencer 6, 4 (1984), 47-53.
[17] Griinbaum B., Griinbaum Z., Shephard G.C., Symmetry in Moorish and Other Ornaments, Com put. Math. Appl. 12B, 3/4 (1986), 641-653.
[18] Griinbaum B., Shephard G.C., Tilings and Patterns, Freeman, San Francisco, 1987.
[19] Jablan S.V., Antisimetrijska ornamentika I, Dijalektika 1-4 (1985), 107-148.
[20] Jablan S.V., Antisimetrijska ornamentika II, Dijalektika 3-4 (1986), 13-56.
[21] Jablan S.v., Teorija antisimetrije i visestruke antisimetrije u E i E\{O}, Ph.D. Thesis, PMF, Beograd, 1984.
[22] Jablan S.V., Theory of Symmetry and Ornament, Mathematical Institute, Beograd, 1995.
[23] Lockwood E.H., Macmillan R.H., Geometric 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Melburne, 1978.
[24] Loeb A.L., Color and Symmetry, Wiley-Interscience, New York, 1971.
[25] Muller E., Gruppentheoretische und Strukturanalytische Untersuchungen der Maurischen Ornamente aus der Alhambra in Granada, Ph.D. Thesis, Univ. ZUrich, Ruschlikon, 1944.
[26] Nicolle J., La symmetrie dans la nature et les travaux des hommes, Vieux Colombier, Paris, 1965.
[27] P6lya G., Uber die Analogie der Kristallsymmetrie in der Ebene, Z. Kristall. 60 (1924), 278-282.
[28] Savelov A.V., Ploskie krivie, Gosizdat. fiz. mat. lit., Moskva, 1960.
[29] Shepard A.O., The Symmetry of Abstract Desig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eramic Decoration, Carnegie Inst. of Washington, Publ. No. 575, Washington DC, 1948.
[30] Shubnikov A.V., Koptsik V.A., Symmetry in Science and Art, Plenum, New York, London, 1974.
[31] Shubnikov A.V., Belov N.V. et al., Colored Symmetry, Pergamon, Oxford, London, New York, Paris, 1964.
[32] Smeets R.;Signs, Symbols, & Ornaments, Van Nostrand, New York, Cincinnati, Toronto, London, Melbourne, 1975.
[33] Smith D.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 II, Dover, New York, 1958.
[34] Speiser A., Die Theorie der Gruppen von endlicher Ordnung, 2nd ed., Berlin, 1927.
[35] Stroik DJ., A Concis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2nd ed., Dover, New York, 1948.
[36] Washburn D.K., A Symmetry Analysis of Upper Gila Area Ceramic Design, Carnegie Inst. of Washington, Publ. No. 574, Washington DC, 1977.
[37] Washburn D.K., Symmetry Analysis of Ceramic Design: Two Tests of the Method on Neolithic Material from Greece and the Aegean, In Structure and Cognition in 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3.
[38] Washburn D.K., Crowe D.W., Symmetries of Cultur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Washington, 1988.
[39] Weyl H., Symmet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52.
[40] Zamorzaev A.M., Teoriya prostoi i kratnoi antisimmetrii, Shtiintsa, Kishinev, 1976.
[41] Slavik lablan, Symmetry and Ornament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在下告退。
转发随意,转载请联系张大少本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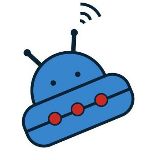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