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引进出版了骆以军短篇小说合集《我们自夜暗的酒馆离开》,这本书收录了《我们自夜暗的酒馆离开》《降生十二星座》《红字团》等十二篇,皆为作家青年时期的经典作品。
骆以军的写作风格华丽、有极强的幽默感、语言生动活泼、叙事方式驳杂跳跃,因其超强的讲故事能力被读者亲切地称为“e时代的小说界一哥”、“骆胖”。
他的作品之前已经有被引进过大陆很多本了,而这本经典《我们自夜暗的酒馆离开》直到现在才和大家见面。这本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有作家年轻骇人的才情和强烈的文字风格,不管你有没有读过骆以军的小说,这本都非常值得一读。
今天的文章是骆以军所写序言。
《我们自夜暗的酒馆离开》自一九九三年初版迄今,已十余载矣。这十多年来,我个人的人世际遇或心境,其变化不可谓不大矣。这期间,真实生命的骇丽风景汹涌、扑面,将我整个吞没,以其对应年轻时小说暗室里精微焊接的纯净结构,真只有用四字套句以概括其体会:“百感交集、无言以对、瞠目结舌。”那互为镜像的两个对立世界,对我而言,同等繁复、庞大而艰难。我有时已分不清自己是在其中哪个世界,较心不在焉或较专注凝神?在哪边较纯真童话而在另一边较残虐暴乱?或是在哪一界面有其不动如山的朴素信仰在另一端则彷徨如在无倒影梦境颠倒行走?
这其中,所收录的短篇《降生十二星座》,几成为这十余年来所有大小选集,我个人的代表作。在某些严肃的场合,仍会有一些文学同好,就这篇小说中的某些症结、或隐喻、或推理线索、或意欲追问的形上核心……向我征询。但我常会陷于“啊,真的不那么清楚记得”,又怕是年岁增长后自己虚荣的添加附会,又怕像矫情避谈少作,这样的尴尬处境。其实在此书之后,我曾有近四五年处于写不出东西,甚至打算放弃写小说这一志业的阴惨时光。后幸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得遇一些“拉了一把”的恩人、长辈(不论是我那流浪汉困顿生涯真正的经济援助;或是某一篇发光的、让我热泪漫流的序文或评论;或是以自身姿态示范的,写小说这一行业的端肃近乎修行,而非弄潮炫技的“未来的时光”),也摸索、攻坚了几本毁誉参半的长篇。这样的时刻(如我一直视为良师畏友的黄君私下劝告:“你已得到过多的宠爱。”似乎一直保持在引擎运转的热车状态,但真正的代表作始终仍未出手),回顾,重读自己的少作,难免兴起一种“难道当真十年只磨一剑”,一切拉成远景,原来仍只在原点蹭蹬打转的躁郁。
我还会写出怎样的作品?
我是否已失去了从前那些美好、不畏人世的质素,我有没有让虚无侵夺,让形式的纷繁遮蔽了,年轻时固执朝人性深井悬垂绳索一探究竟的高烧热情?
我只是在临帖?依傍一种已然成熟的巨大传统(不论中国或西方),在想象中的“理想的读者”的旁征博引中瞎目前行?或一切其实只是匍匐在那些伟大神殿前,“文字即肉身即存在”,挑角,拟仿(再没有能让人惊异的原创了),移转的“自我戏剧化”?(异乡人?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恶汉?换取的孩子?歧路花园?)
我记得写作《降生十二星座》这篇小说时,大约是在我大五那个暑假(我延毕一年,其时已放榜考上戏剧研究所,但因仍得暑修补齐之前被当掉的英语实习课,所以仍得留在除了强烈日光下缓慢移动的老人们,所有大学生全像魔法轰然消失的,空荡荡的阳明山上)。那是一个奇怪的时点,大四时成日聚会酗酒、夜里出没,宛如狐神花鬼的创作同伴们(那时我们弄了一个叫“世纪末”的地下社团)早在一年前各自毕业散去,男孩去当兵,女孩们或回台南台东澎湖鹿港当小学代课老师,或留在台北的小出版社当小编辑,当初和我一同延毕的炮辉那时也不得不应征召入伍。几个和我同一年考上研究所的女孩,也要到九月底才返回山上。
整座山上只剩下我一个人。
那真是一段奇怪的时光。每天早晨,我会抱颗篮球,独自一人跑去前山公园的篮球场,像演独幕剧一样,跑篮、罚球线练投,四十五度角立定跳投,底线跳投,假拟有人防守时的运球过人、翻身跳投……在那球场的四周,浓荫错致、蝉鸣不已。有一些提着铝筒盛装煮沸米粉汤或芋头粥的阿婆或在一旁间散坐着、手摇蒲扇赶苍蝇,或和那些上山泡温泉、赤膊时犹肌肉精壮的阿公们调情打屁。公园里的宪兵队,有时会由值星官带着那些红短裤的平头阿兵哥穿绕那些树丛花丛操跑。从来没有人注意我这个肢体僵硬、一头乱发的怪异青年,自顾自比画地在无人的球场上“练习”各种想象的篮球基本动作。我从来没有参加那些球场上即兴凑合报队的半场斗牛甚至全场比赛。这也是我挑选那日头曝晒的上午,避开傍晚时各路球痞在此会聚之黄金时光的原因。主要是我害羞且自卑,对于在众人面前的某一个出丑,常会耿耿于怀甚至羞惭欲死。
但那真的有点滑稽:没有比赛,没有防守者,却重复着一些自己想象的进攻动作(我还摇头晃脑地做假动作,或踮一步后跳投篮呢)。常常是投出手后,得气喘吁吁自己跑得老远去把球捡回来。如今我耳边几乎像远方的鼓声,犹仍出现那种皮球在水泥地上单调乏味的弹跳声响。
待力气放尽,我会回到赁租宿舍,用冷水将那像太阳能电瓶吸附了炽白滚烫的头发、颅顶、身体里的热冲逼出来,直到浑身发冷。然后回到三坪多的房间,拿出某本伟大的小说,抄读着其中某些段落。
我不记得那个暑假我读了哪些作家的作品。那时没有女友,在山上收养的狗们也送回永和托我母亲照顾,人渣朋友们尽皆散去。那时甚至没有每日读报的习惯,更别提电视了。除非有长辈灵光一闪想起邀稿,不然所写的小说大抵是处在没有预期会发表的漂浮状态。如今回想,那样的书写时光,真像《天平之甍》里,那几个渡海到中国、耗费了大半生抄写经文,回航时却遭逢飓风船难,大批手抄经沉入海底的日本僧人。过去、此刻和未来全在一混沌梦境的状态,像从整个汹涌的“真实世界”之时间河流脱离开来,独自在一封闭淤浅的小水洼里打转。只要有一个念头:“这一切都是徒然罢了。”系住那一切孤独、疲惫、重复行动的执念细绳就会绷断。
我就是在那样一个夏天——那时我或以为我的一生,就是那样纯净状态的无限延续——以后来急行军起来几乎可以写半本长篇的悠长、奢侈时间,磨磨蹭蹭、缝缝补补写完《降生十二星座》。
图:2018年骆以军在北京正午酒馆
来源:正午故事
点击跳转当当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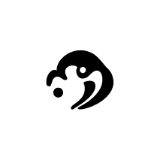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