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们!在下张大少。
是什么让传统的凯尔特结变得美丽?凯尔特结有什么共同的结构和图案,不同的凯尔特结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除了风格和手法,是什么让数学中的扭结看起来像传统凯尔特风格?在本文中,我们试图通过描述、构造、列举和探索凯尔特结设计的空间来回答这些问题。
凯尔特结及其相关结构在数学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Cromwell探索了凯尔特结的对称性[2];Fisher和Mellor计算了某些类型的凯尔特设计的分量[4];Lee和Ludwig对马赛克纽结进行了广泛的分类[8];Gross和Tucker研究了凯尔特纽结的纽带多项式[6]。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列举了各种“类凯尔特”的纽结设计,并使用汉明图来检查密切相关的凯尔特设计之间的关系。
构建凯尔特结设计
凯尔特结的设计通常基于网格[2,9]。为了构建m×n凯尔特设计,我们使用一个2维“双倍”点数组
,其中0≤c≤2m和0≤r≤2n。该数组包含三个子栅格:主栅格由点
组成,其中c和r都是偶数(显示为黑色正方形)。第二个栅格由点
组成,其中c和r都是奇数(显示为蓝色圆圈)。剩下的点(c+r)是奇数,它们构成了凯尔特设计本身的基础(显示为绿色钻石)。我们称这些轴心点(称为构造点[3]),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插入连接任意一侧相邻网格点的断点。这三个网格分别称为一级网格、二级网格和三级网格[9]。在这些轴心点选择垂直、水平或缺失的断点完全决定了独特的凯尔特设计,如下面的3×2设计序列所示:
我们把“偶数”网格上各点之间的断裂线(连接黑色方块)称为0型断裂,把 "奇数 "网格上各点之间的断裂线(连接蓝色圆点)称为1型断裂。因此,每个轴心点都可以是0型断裂、1型断裂,或根本没有断裂的中心。在本文中,我们将注意力限制在封闭的设计上,其中沿边界的所有轴心点都有0型断点。否则,我们就得考虑那些允许曲线"逃离"边框的设计。
要构建一个设计,设想你从其中一个轴心点开始,并以45度角朝设计中心射出一个台球。每当遇到断裂线时,你就会从断裂线“反弹”,可能会沿此过程拉直、平滑或样式化曲线,从而形成一条美观的路径。由于这种“反弹”结构,这样的曲线也被称为镜像曲线[5]。在弹来弹去一段时间后,你最终会回到你开始的地方,形成一个我们称之为条带的设计组件。对你尚未访问的任何轴心点重复此操作,直到你覆盖了所有轴心点,以获得一个或多个条带的完整凯尔特设计。在上面的示例中,左侧有一个垂直的1型断裂,中间有一个水平的0型0断裂,这导致了单条带设计。
凯尔特设计的等价类
我们从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开始我们的旅程:在一定的尺寸和限制下,有多少种不同的凯尔特设计?首先,识别等同于旋转和反射的设计是很自然的。从群论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分别对于正方形设计和非正方形设计,研究在对称群D4和D2作用下的设计的等价类或轨道。另一个最初的限制是要求所有非边界断裂都是1型断裂(根据我们的经验会产生漂亮的小设计)。我们称这种设计为1型设计(类似于0型设计)。通常,设计可以有0型断裂、1型断裂、两者都有,或两者都没有。
让我们从3×2的第一类设计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正好有7个轴心点,在这些轴心点上既可能有1型断裂,也可能没有断裂,因此总共有2^7=128个设计,被划分为图1所示的48个等价类。这种设计有许多可识别的特性。有些有多条带子,有些是连通的(意味着你不能用一条封闭的曲线把它们分成两块),有些则有不受欢迎的冗余。在我们继续阅读本文时,我们将介绍这些属性,并对哪些设计要包括在内作出审美决定。
图1:48个等价类,它们是3×2的1型,其中红色和蓝色的41个是连通的。
1型设计的限制适用于小数量,在开始探索和绘制凯尔特结时强烈推荐。你现在应该把这张纸收起来,看看你是否能自己找到所有48个本质上不同的3×2的1型设计。(另一个很好的起点是探索m×2的1型设计。)。对于那些想要证明恰好有48个这种类型的设计的人,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证明:根据Burnside引理,本质上不同的3×2的1型设计的数目等于由D2的四个对称之一确定的那些设计的平均数。通过在垂直轴上的反射固定的设计由仅四个轴心点的断裂信息确定;对于沿水平轴的反射,由5个轴心点确定;对于180度旋转,由4个轴心点确定。所有2^7=128个设计都由D2的标识元素固定。因此,根据Burnside引理,有(2^4+2^5+2^4+2^7)/4=48个本质上不同的3×2的1型设计,一直到D2对称,如图1所示。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设计的等价类简称为“设计”。
当然,我们也对具有一种以上断裂类型的设计感兴趣,这在传统的凯尔特艺术中是很普遍的。7个轴心点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有0型断裂,或者1型断裂,或者没有,因此有3^7=2817个可能的3×2设计,被划分为648个等价类(见图2)。这是一个很大的设计空间,尽管m和n都非常小。我们的下一步将是消除某些不太理想的设计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更易于管理的集合,并可以直观地了解不同设计之间的关系。
图2:有648个本质上不同的3×2设计;其中293个是连通的。
确定“最佳”设计
即使是在3 × 2的情况下我们也能看到我们想强加的条件。我们追求的设计是美观的凯尔特结。一个重要的属性是设计是否有尾巴。当至少三次断裂开始形成一个正方形时,一个设计就会有一个尾巴。例如,在图1中,48个设计中的最后23个(蓝色和灰色)有尾巴。尾巴是一个条带的一部分,有3种形状:甜甜圈(由于方块中有4个断裂,口),一个转折(由于方块中有3个断裂,任意方向的C),或一个水槽(方块中恰好有一个缺口被翻转,任意方向的C -)。尾巴的这个定义与[3]中使用的尾巴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
把设计限制为连通和无尾巴能使我们大大减少3×2设计的空间。在图2所示的648个本质上不同的3×2设计中,我们可以舍弃355个不连通的设计(灰色),以及另外250个有尾巴的设计(蓝色)。这就给我们留下了43个连通且无尾巴的设计。然而,这些设计中的一些仍然不是很有美感。你能发现是哪些吗?我们认为,第二行中间的8个设计(绿色)也应该删除。因为这些设计都是"拉伸"的等效设计,都是2×2设计的"拉伸"版本(可以压缩成2×2设计)。这些设计都有我们所说的梯子:在0型和1型之间交替出现的连续断点,一直从顶部延伸到底部(或从左边延伸到右边)。
图3:8个连通且无尾巴的3×2设计,带梯子(用红色标记)。
3 × 2设计的空间因此减少到只有35个设计。我们称之为简化。如果设计是连通的、无尾巴,且无梯子,那么设计就会简化。简化的设计在它们的效率和悦目视觉效果。减化的设计也倾向于有足够多的交叉点(如[3]所建议的)。
因此,我们已经确定了几个有用的标准来寻找美观和凯尔特式的设计。特别是,我们利用了无尾巴和无梯子的概念。然而,我们当然不是说所有美观的凯尔特式设计都是无尾巴、无梯子且连通的。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比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继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之后创作的《六节系列图案》系列版画,其中尾巴很常见。
还可以进一步实施哪些限制?一个明显的可能性是减少我们对单条带设计的关注(在[5,7]中也称为单线性)。我们还可以强加一个条件,那就是对称的基本艺术元素。例如,在图4中19种单条带和简化的3 × 2设计中,有9种设计具有旋转或反射对称。因此,我们将2187个可能的3 × 2设计划分为648个等价类,并进一步过滤它们,在这种情况下,19个本质上不同的美丽凯尔特图案,其中9个是对称的。
图4:19个本质上不同的3 × 2简化的单条带设计,其中9个是对称的。
使m和n的值稍大一些,也会有可能的设计组合爆炸,但我们的过滤方法将允许我们将集合简化到可管理的大小。例如,对于4 × 3的设计,有17个轴心点,因此2^17= 131,072种可能的1型设计,划分为33,408个等价类(和3^17 = 129,140,163种可能的设计,划分为32,319,486个等价类)。如果我们过滤1型设计,只包括那些简化的、单条带的和对称的,那么我们只剩下图5中的184个设计。
图5:184个4 × 3的1型、简化、单条带、对称设计。
用汉明图探索凯尔特结设计的空间
既然我们可以将理想的凯尔特人设计空间过滤到更合理的大小,我们就可以开始探索这些设计本身是如何关联的。我们怎样才能以一种好的方式来浏览设计的空间呢?一种方法是将每个设计表示为图中的一个顶点,当两个设计正好相差一个断点时,用一条边将它们连接起来。
让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开始:2×2凯尔特图案的完整空间。这些设计有四个轴心点,因此在开始时有3^4=81种可能的设计,如图6最左边的图表所示。其中一些设计在旋转和反射下是等效的,这些集团在第二个图表中显示为与蓝色边相连。在第三个图中,我们收缩了蓝色边,以便将等价设计分组到21个等价类中(每个等价类的大小为1、2、4或8)。在第四幅图像中,设计本身绘制在顶点前面。最后,通过为每个等价类选择一个代表,我们得到了第五个图。这里,每个顶点现在是设计的等价类,如果每个类中至少有一个设计只相差一个轴心点,则两个等价类与一条边相连。
图6:2×2设计的汉明图。
上面的第一个图也被称为汉明图H(4, 3),它是由{0, 1, 2}中的元素组成的有序4元组的集合,其中每个顶点都是在4个轴心点上选择的断点,边连接着正好有一个坐标差异的顶点图。最后的图是在关系到对称设计的等价关系下的汉明图的商数。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也将把这种商数类型的图称为汉明图。
通过观察凯尔特设计集的这些汉明图,我们可以发现设计之间的有趣关系,并挑选出关键的设计元素。此外,设计集的汉明图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几何结构。例如,在上图的2×2设计集合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三角形结构,因为每个轴心点有三种可能。图7显示了一个类似的进展,从128个不同的3×2的1型设计到图1中确定的48个等价类。
图7:3×2的1型设计的汉明图
现在让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我们前面讨论的一些较大的设计集合。我们在图2中看到,有648个本质上不同的3×2设计。这些设计在图8中最左边的汉明图中显示出来。第二张图显示的是43个相连和无尾的设计。第三张图是这些设计中35个被简化的设计的汉明图。第四张图显示了这些设计中的25个是类型1。颜色表示顶点的度数(红色表示度数较高)。
图8:3×2设计的汉明图
我们在图5中看到,有184个简化的、单条带、对称的4×3 的1型设计的等价类。在不附加对称条件的情况下,有2533个这样的设计,如图9中最左边的两个鸟巢式汉明图所示。施加对称条件后,我们得到右侧显示的高度不连通的图,在顶点上有设计和没有设计。对称设计集合的汉明图子图是如此不连通是有道理的,因为改变任何轴心点的断裂选择可能会删除至少一个对称。
图9:4×3的1型简化单条带设计的汉明图
结论和下一步工作
许多汉明图具有惊人的双边对称性,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工作中对其进行研究。图10中最左边的图是175个简化的3×3的1型设计的汉明图;第二和第三张图是94个单条带的设计。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图中的对称性?我们还可以在这些图中提出关于连通性的问题,例如,图9的第二个图中具有高度的红色设计。
图10:3×3的1型设计的对称汉明图
此外,通过研究各种空间的汉明图的全局结构,我们能够识别出有趣的设计、视觉上相似的设计,以及由于其他原因而突出的设计。其中一些图显然是没有对称性的,这说明凯尔特人设计的空间具有某种纠结的性质。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将注意力限制在填补矩形区域的缩小的凯尔特设计上,但是有许多基于非矩形区域和/或非矩形网格的传统凯尔特艺术的例子[9, 10, 1]。未来的工作可以将我们的列举可视化扩展到非矩形的凯尔特设计。
我们还可以使用凯尔特设计的枚举来进一步研究[8]中描述的马赛克纽结,或者沿着类似的路线,根据它们可能的简化矩形凯尔特设计的最小尺寸来确定纽结的“凯尔特数”。请注意,我们可以用凯尔特设计来研究交错和非交错的结,因为尽管每个凯尔特设计都可以确定一个交错的结[6],我们也可以选择设计交叉来创造非交错的结。这种非交错的凯尔特结很少出现在传统的凯尔特图案中,例如[2]中说明的Govan Stone图案。
对于比我们在这项工作中涉及的更大的m和n的值,即使在计算上枚举减少的设计集合也是令人望而却步的。然而,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过滤条件和第一作者编写的软件工具来制作任何大小的特别令人愉快的凯尔特设计的例子。例如,我们以100个随机生成的具有旋转对称性的3×6简化设计作为结束。
图11:100个随机生成的3×6简化和旋转对称的设计。关于未来工作的更新,更高分辨率的图像,凯尔特结设计的集合,以及更多,见https://rant.codes/celtic。
参考文献
[1] G. Bain. The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of Celtic Art. W. MacLellan, 1951.
[2] P. R. Cromwell. “Celtic knotwork: Mathematical art.” Math. Intell., vol. 15, no. 1, 1993, pp. 36–47.
[3] P. R. Cromwell. “The distribution of knot types in Celtic interlaced ornament.” 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d the Arts, vol. 2, no. 2, 2008, pp. 61–68.
[4] G. Fisher and B. Mellor. “On the Topology of Celtic Knot Designs.” in Bridges: Mathematical Connections in Art, Music, and Science. R. Sarhangi and C. Séquin, Eds. Southwestern College, Winfifield, Kansas: Bridges Conference, 2004. pp. 37–44. http://archive.bridgesmathart.org/2004/bridges2004-37.html.
[5] P. Gerdes. Lunda Geometry: Mirror Curves, Designs, Knots, Polyominoes, Patterns, Symmetries. Universidade Pedagógica, Maputo, 1996.
[6] J. L. Gross and T. W. Tucker. “A Celtic Framework for Knots and Links.” Discret. Comput. Geom., vol. 46, no. 1, 2011, pp. 86–99.
[7] S. Jablan, L. Radovic, R. Sazdanovic, and A. Zekovic. “Knots in Art.” Symmetry, vol. 4, no. 2, 2012, pp. 302–328.
[8] H. J. Lee, L. Ludwig, J. Paat, and A. Peiffer. “Knot mosaic tabulation.” Involve, 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vol. 11, no. 1, Jan 2018, p. 13–26.
[9] A. Meehan. Celtic design. Knotwork, the secret method of the scribes.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1.
[10] A. Tetlow. Celtic Pattern: Visual Rhythms of the Ancient Mind. ser. Wooden Books. Bloomsbury USA, 2013.
[11] Roger Antonsen and Laura Taalman, Categorizing Celtic Knot Designs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在下告退。
转发随意,转载请联系张大少本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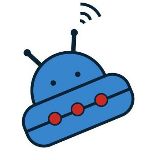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