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中学语文课本,鲁迅先生的文章是重点。《记念刘和珍君》中,有关北师大学潮,打笔仗,鲁迅提及陈西滢。鲁迅不认可的人,与“反动文人”很近,离口诛笔伐不远。学生时代的印象,总是很深刻。陈西滢的妹妹陈汲,嫁与竺可桢。也就是说,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是陈西滢的妹夫。
而陈西滢的妻子,正是此文的女主人公凌叔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评价凌叔华的小说“很谨慎地,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历史如同一张大拼图,昨是而今非,到如今,也许就是“今是而昨非”了。
一
1900年3月25日,凌叔华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父亲凌福彭,和康有为同榜中进士,点翰林,在清末民初,先后担任过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北洋政府约法会议员等职,官运亨通。母亲李若兰,是凌父的第三房太太,生有四个女儿,叔华行三。凌父共有子女十五人,叔华排行第十。
如同生活在大观园中的叔华,虽说没有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的“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但大家庭的明争暗斗,难免不会在她的心中,留下波澜。她擅画,像惜春;她平和,像迎春;她更像探春,敏感细腻,虽然庶出身份,但仍不屈不挠,努力争得自己的一片天空……
多年后,女儿陈小滢写道——我看母亲留下的那些文字,她的家庭,她的互相争斗的姨娘们,还有那么多孩子彼此间的竞争,我在试着了解她,却感到越来越悲哀。
二
凌父不仅为官,还饱读诗书,爱好绘画,交游甚广。当时许多名流,如辜鸿铭、齐白石、陈衡恪等,都是凌家座上宾。
叔华七岁,凌父请来慈禧的御用女画师缪素筠,为她启蒙。叔华曾拜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为师,后又从女画家郝漱玉习画,这使她的绘画技术有了坚实的基础。
叔华在后花园的闺房,被父亲布置成画室,她的《古韵》中这样描述——我的房间布置得像真正的画室,家具都是爸挑选的……面对紫藤的窗前摆放着一条黑漆桌案,光滑透亮,可以反照出美丽的紫藤花……一张红漆桌案放在面朝紫丁香的窗前,这种红漆是北平最好的,红得发亮,看久了令人目眩,简直妙不可言。
辜鸿铭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他被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叔华师从辜鸿铭学习英语,清楚记得——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
名师出高徒,叔华用英文写作,其来有自。但她自言,生平用功夫最多的还是画。
内承文化庭训,外受名师熏陶,叔华的美,带着丰富的内涵,贤淑文静,淡雅秀丽。
三
凌叔华十九岁,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读书,与邓颖超是同窗,比许广平高一级。
1922年,叔华二十二岁,考入燕京大学预科,与即将毕业的冰心同学一年,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周作人任教"新文学"。许广平考入北师大,体育教员是唐筼,而唐筼后嫁陈寅恪。缘份的天空,真是陆离,有机会写写,别有味道。一笑。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此时的叔华,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与担任翻译的徐志摩、参加接待工作的陈西滢,至此结缘。
一天,叔华举行家庭茶会欢迎泰戈尔,作陪的有胡适、丁西林、林徽因、徐志摩、陈西滢等。
叔华这样描写来到书房的诗人——抬头见他银白的长须,高长的鼻管,充满神秘思想的双目,宽袍阔袖,下襟直垂至地。
她顿时觉得自己是“神游在宋明画本之中”,差点连“久仰久仰”都忘了说。叔华称诗人“低沉的声韵,不但不使人生厌倦,且能使人感到如饮醇醪及如听流水的神味。”
那天,叔华和泰戈尔聊了许久,聊到诗歌和绘画,她还得到诗人建议——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找善、找美,找人生的意义,找宇宙的秘密。
四
此前,北京,泰戈尔与学生见面,三人(泰戈尔、徐志摩和林徽因)并立的合影,刊于报纸,人称“松竹梅三友图”。1920年10月,伦敦,留学剑桥的徐志摩,与花季少女林徽因初见。至此,志摩一直难忘徽因。
为此,泰戈尔留有诗句——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不过,泰戈尔对志摩直言,叔华较之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4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去美国留学。此时的志摩,心灰意冷,心无所寄。
意想不到的是,叔华竟肯答应做志摩的“通信员”,枯索期的温润知己。
半年通信,七八十封,几乎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显然超出一般友谊。
徐志摩,除了诗歌,忘不了他的爱情,但他绝对不是常人眼中的纨绔子弟。给梁任公做门生,与胡适为腻友,为泰戈尔做通译,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师门五年记》的作者罗尔纲(曾在胡适家中做学生,整理胡适父亲日记,兼任胡适儿子的家庭教师),记得——在胡适家中往来的名流们,能以朋友对待我,这个处在卑微地位的青年的,只有他(徐志摩)一人!
梁实秋回忆——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欢喜。讨人欢喜不是一件容易事,须要出之自然,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其人本身充实,有丰富的情感,有活泼的头脑,有敏锐的机智,有广泛的兴趣,有洋溢的生气,然后才能容光焕发,脚步矫健,然后才能引起别人的一团高兴。志摩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此时的志摩,需要朋友,需要有展露自己思想的安全空间。叔华性格内敛,不爱多言,也正是得天独厚的“红颜知己”。她最懂徐志摩,深知徐深深地爱着林。当年为了与林在一起,无情地与怀孕的发妻张幼仪离婚。叔华心灵剔透,她深深地被徐吸引,但她不愿作林的替代品……
1983年,垂暮之年的叔华写信给陈从周(陈的岳母,是徐的姑母)——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
爱与不爱,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做给自己的心看。
四
1924年6月,叔华从燕京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1926年7月,与陈西滢结婚。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民国初年,他受表舅吴稚晖的鼓励,赴英国求学。在英国,他修完中学课程后,先进爱丁堡大学,继而转入伦敦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学,最后以博士衔学成归国。
叔华成为西滢的新娘,众人大跌眼镜。
爱一个人,就像在被窝里玩手机,总会有星星点点的光露出。但无人看出,两人在谈恋爱。恋爱中的女人最美,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容光,也许叔华没有。
有一个版本,志摩父亲徐申如,中意叔华,希望儿子与之联姻。阴差阳错,成为徐家儿媳妇的是陆小曼。
志摩,不愧是叔华的蓝颜知己。叔华结婚两个月,徐就看出夫妇二人有矛盾。他给胡适写信——叔华、通伯(陈西滢,字通伯)已回京, 叔华病了已好,但瘦极。通伯仍是一副“灰郁郁”的样子,很多朋友觉得好奇,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外人见得到的至少)太近古人了!
苏雪林提及西滢——喜说俏皮话挖苦人,有时不免谑而近虐的,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
叔华也说过——以前与他(指西滢)出门做客,真是窘得很,不熟的人还以为他很骄傲呢。
最明显的是,叔华夫妇,婚后不在同一书房写作。叔华创作时,总是对丈夫"保密",生怕这位批评家,在她的作品尚未发表时,用冰冷的水,将她的文思和创作激情之火浇灭。而西滢写好文章后,也不给妻子看。只有文章发表,两人才彼此相示。
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其文笔晶莹剔透,无半点尘渣绕其笔端。
多年的留学经历,使西滢习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也使得他对当时中国的一切,带有几分偏见。
清官难断家务事,叔华甘苦寸心知。
数年后,冰心见到叔华,开起玩笑——叔华,你知道俗语说的,江阴强盗(冰心丈夫吴文藻为江阴人)无锡贼(陈西滢为无锡人),咱们俩命真苦,一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
一旁的西滢,苦笑。
五
1931年11月19日,志摩飞机失事,遇难。之后,叔华成了一桩事件的女主角。
志摩去世后,留下一批文稿和日记,有他自己的,也有小曼的,装在一个箱子里,称作“八宝箱”。
1925年,徐去欧洲,临行前,将箱子交与叔华,其间开着玩笑——如果自己在国外出了事,叔华可以箱子里的书稿为材料,为他写一部传记。
没有信任,就没有友谊。叔华,是志摩相信的知己。
后来,徐取回箱子。来来去去,“八宝箱”——志摩的遗物,叔华成为保管人。
不过,箱子是小事,想看的人,却都是“人物”。内有《康桥日记》,徽因想读;涉及为志摩出全集,胡适需要留存文稿;小曼作为家属,更应该拥有……总而言之,叔华将八宝箱,交与胡适,情非得已。
但问题在于,有人怀疑,叔华未交出全部日记。叔华生气,作为遗物的保管人,手中已无一物,竟被人如此相逼。
不满胡适将八宝箱交与徽因,而不是小曼。叔华的回信,也颇具回味——
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罢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总依恋北京。
叔华最犀利的话,不过如此。
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但叔华与徽因,至此不见。而叔华与小曼,多有来往。在叔华的周旋下,徐父答应给小曼一些资助。陈半丁曾指导叔华作画,叔华介绍小曼结识陈师,再习绘画,从悲伤中解脱……
1933年,徐父请托吴其昌,请他托叔华为志摩题写诗碑。志摩的朋友中,俊彦若干,而徐父独请叔华。叔华愿意。
林黛玉“冷月葬诗魂”,叔华易一字,“冷月照诗魂”,用于志摩,贴切自然。碑立了,但后来,横卧泥中……
六
1929年5月,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聘陈西滢为教授,后接任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叔华也到武大执教。叔华与同在武大的女作家袁昌英和苏雪林,过从密切,结为好友,三人在文学创作上盛极一时,有"珞珈三杰"之誉。
1935年秋,相貌英俊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被武大聘用。初期,由陈氏夫妇负责招待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朱利安说——整个下午我都和文学院院长一家待在一块,有他的妻子,还有他六岁的女儿——非常可爱迷人的小女孩。我们谈话的方式很自由——简直是内地的剑桥。
很快,在给友人的信中,朱利安承认爱上了叔华——她敏感而细腻,聪慧而有教养,有时还有点使坏,最爱那些家长里短的故事。她不算漂亮,但是很吸引我。
叔华也投入其中,不能自拔。
东窗事发,朱利安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又来到西班牙,负责开救护车运送伤员,意外遭伏击,身亡,年仅二十九岁。
数年后,朱利安与母亲的通信集结出版。一段不被人所共知的恋情,浮出水面。
1968年,叔华的女儿小滢,从朱利安的书信集中,得知往事。一次出行,女儿问父亲:“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为何仍然在一起?”父答:“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
没有再多的话,也无法再进行下去……
女儿说——父亲其实是个很含蓄的人,他很少说什么,从不说别人的坏话。
倒是叔华,经常“告诫”女儿一句话——女人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七
1946年,西滢被民国政府,任命为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代表,常驻巴黎。
1947年春,叔华准备带女儿出国,与丈夫团聚。上海,赵清阁为叔华饯行,小曼作陪。
巴黎昂贵的生活费用,西滢菲薄的薪金,无奈之下,只好搬至伦敦。只有在开会时,陈才到巴黎。
为了补贴家用,叔华兼事"鬻文和卖画"。
叔华的画,充满文人情趣。朱光潜先生称赞——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规模法度中,流露出她所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看她的画,我们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
客居异国,叔华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也许在画中,她可以梦回故乡。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国建交。翌年,法国政府令陈离开巴黎乔治五世大街11号。
1970年3月29日,陈因病在伦敦去世。渐入老境的叔华,愈发难忍伦敦多雨的天空,空旷的寓所,阴暗的客厅。
他乡不是故乡,叔华思念着北京。
从1960年起,叔华多次回到北京,观光、访友,也曾背着画板,写生。
1985年9月,冰心丈夫吴文藻过世,叔华写给冰心的信——
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望你在这苟酷无情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
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
好了,你已经够难过,我不应再招惹你了!我现定十月二十左右回国,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我俩可以瞎聊一番,五六十年前的老话、乃至于目前有趣有见解的闲谈,都没有关系吧!
写到这里,我真想立刻飞回北京,同你瞎聊一些往事,以解心头悲戚。好在现在已经十月了,还有十几日便可相见。希望我住到复兴路大楼七层后,可以多多相见。我在此一肚子苦恼,谁也不要听,只好憋着气,过着惨淡的时日!
终于,1989年末,叔华坐着轮椅,飞回祖国。远方游子,安居北京。叔华为漂泊的心,找回了故乡。
1990年5月16日,叔华在担架上,一望北海白塔,再别旧居老宅……
六天后,春暖花开的日子,叔华病逝。与丈夫的骨灰,一同葬在无锡陈家墓园,叶落归根。
叔华自己的房间,任何人不得进入,里面有她的秘密。她走后,家人什么也找不到,显然她已处理了,正如女儿所言——母亲一生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
生命中,有些人,是用来陪伴的;有些人,是用来怀念的;有些人,没有在一起,也好。
爱的,不爱的,一直在告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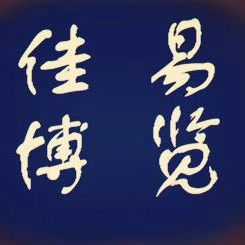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