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8岁的王采玉在弥留之际,叮嘱儿子蒋介石说:“瑞元啊,我不愿跟你父亲合葬,找一个甲字穴,对你的仕途也有帮助。”

蒋介石的父亲是溪口玉泰盐铺的老板蒋肇聪,一生娶了三房太太,前两位都早逝,留下一儿一女无人照顾,经媒人介绍,在45岁时,娶了23岁的王采玉。
虽是半路夫妻,但两人相互扶持,感情很好,婚后第二年就生下儿子蒋介石,按蒋家族谱排序,取名“瑞元”。
之后的七年,王采玉又生下一子两女,蒋家人丁兴旺,一家人热热闹闹,然而,岁月如季节流转,经历了春的温暖,秋的收获后,很快迎来了冬的严寒。
在蒋介石8岁的时候,蒋肇聪因感染时疫病逝,王采玉既要面对继子的驱赶,又要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生活,还要面对一儿一女夭折的悲痛。
这个坚强的女人,靠着自己的毅力和智慧,将蒋介石抚养长大,蒋介石之后能有如此成就,王采玉劳苦功高。
58岁时,她看着儿子成家立业,完成了自己做母亲的使命,一病不起,在弥留之际,她拉着儿子的手说:“瑞元,别把我跟你父亲合葬,找个甲字穴,为娘也就安息了。”
为人母者,必为儿女计深远。王采玉不想跟蒋肇聪合葬,主要有三处考量,第一,当年蒋肇聪离世后,蒋介石跟兄长一起,将他移葬于姚坑山。
墓穴中有四穴,蒋肇聪跟前两位太太一并合葬在其中,留有一穴给王采玉,如今已经过去8年,她不想再开墓穴打扰她们。
第二,作为女人,她是明媒正娶,八抬大轿嫁到蒋家的,如今入土,却成了最末尾的一个,她心有不甘。
第三,王采玉考虑到儿子的处境,不想因为自己是填房而连累儿子被人诟病,于是,她嘱咐蒋介石另选一处“甲字穴”,不仅自己体面,入土后还能不被孤魂野鬼打扰,也能庇佑后世子孙。

王采玉离世后,蒋介石悲痛不已,挥泪撰写下了《哭母文》,将王彩玉自蒋父去世后26年来,在艰难困苦中,培育幼子、重振家业的辛劳和贡献,一一列举了出来。
为了寻找“甲字穴”,蒋介石陪同两位方士在雪窦山、徐凫岩等地勘察了半个多月,最后选中高溪口北三里的白岩山鱼鳞岙中段北面的一块小平地。
按方士的描述,此地像弥勒佛的大肚子,而蒋母的墓穴在其正中,恰好像个肚脐眼,是块福地,定能福泽后代。
墓地的位置选定了,正式动工,为了防止压断龙脉,所选石器不宜过重,也不能多用石板和泥,蒋介石每天亲自去监工,谨慎又隆重。
他还邀请了家族里的贤者,帮着一起筹备丧事,经过5个多月,墓地总算修好了,蒋介石又翻阅黄历,定下安葬的吉日,这才广发邀请贴,其中不乏许崇智,戴季陶,居正等大人物。
送葬的队伍可谓浩浩荡荡,吹吹打打更是不能少,前有“开路先锋”开道,后有六十四名和尚念经。
蒋介石等孝子孝孙,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跟随在二十四名杠夫抬的“龙头杠”棺材后面,哭哭啼啼,让过路的人见者哀思,闻者落泪,王采玉在一片喧闹声中,入土为安,与世隔绝。
落葬完毕后,蒋介石请亲朋好友吃了“豆腐饭”,才依次送客,当天晚上,他按照奉化的风俗,在亡母坟旁守孝。
这一系列仪式走完,王采玉的葬礼才算彻底结束,这种安葬的仪式何其隆重,虽然死者已矣,早已超脱五感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活着的人对他们惦念和哀思,全都都体现在葬礼上。

记得翻译家杨苡在103岁时写的回忆录《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里,也曾回忆过梅兰芳先生为发妻落葬的经历,甚是热闹。
那时,杨苡才十岁左右,被丫鬟来凤喊去看热闹,碍于家中的规矩,她只能躲在影壁后面偷着看。
要看的热闹,就是梅兰芳亲自为原配王明华发丧,像这种大出殡,街坊四邻事先都知道,大家都会到街上来看,但一定会有人提前净街,就是梅家的人把经过的马路扫一遍。
发丧的队伍要一队一队地过,出发前,先敲一面很大的锣,锣声一响,发丧就开始了,前面是撒纸钱的,漫天地落在。
后有影像亭,两人抬一个小亭子,当中放的是死者的黑白大照片,再后面就是诵经的和尚队、尼姑队。
大户人家还有吹笙的道士方队,也有银柳队,每人举着一根银柳枝子,还有纸人纸马,纸糊的汽车、马车。
还有老妈子、丫鬟,虽然比真人一半还小些,但他们有端盘子的,有拿着毛巾的,全都是服侍人的样子,惟妙惟肖。
再后面就是梨园行的人,穿着便装,热闹非凡,最显眼的还是梅兰芳,他走在队伍前头,拿着哭丧棒,边走边哭,伤心极了,鼻涕都流过嘴,拖了好长。
杨苡不明白,这鼻涕都要拖地了,他怎么不拿手擦一下?丫鬟来凤告诉她:“出殡不兴擦掉的”。
不能擦鼻涕这一说法,在鲁迅先生去世的时候还上过报纸,报道的主人公是巴金先生,他是给鲁迅抬棺的八个人之一,上海就有小报讽刺他是鲁迅的孝子贤孙,以鼻涕挖苦他,说快要坠地了。

如今,这种送葬的仪式早已不被年轻一代所重视,知道流程和忌讳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什么流鼻涕不能擦的禁忌,也只能在书本上才能看到。
送葬仪式在新时代新思想里,也许是一种糟粕,被遗忘被抛弃是最好的结局,然而,这种仪式的丢失,何尝不是文化的缺憾,何尝不是亲情淡漠的表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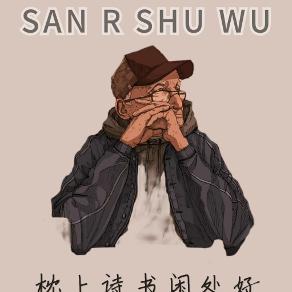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