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5月13日文章,原题:旅程与目的地:马克林和中国 当前,对中国及其文化、人民和历史的了解和理解,可以帮助两国关系回到良好的基础上,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小学和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降到极低水平。
在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方面,澳大利亚曾走在世界前列。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强国,无论好坏,都将影响我们的命运,但很少有学生在中国研究方面深造,那些多年前毕业的学生往往不得不离开澳大利亚,到别处寻找合适的工作。
我属于二战后最早学习中文的一批人。当时人们告诉我这是一门无用的学科,但由于我是女性,这并不重要,因为结婚后丈夫会支持我。上世纪60年代,我第一份全职工作是在香港,证明那些人错了。越南战争期间,我研究中国政策文件,为澳大利亚及其盟国提供了重要信息。回到澳大利亚后,我的职业生涯涉及与中国官员、学者的个人接触,代表澳大利亚的利益建立贸易和文化联系,开拓道路,避免陷阱,将我在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所受的训练用于实际工作,造福澳大利亚。
我并非孤独地在工作。60年代中期,当我在悉尼完成博士学业时,斯蒂芬·菲茨杰拉德和马克林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同样的学位。菲茨杰拉德后来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马克林进入格里菲斯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教授和研究中国戏剧与少数民族政策,成为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先驱。他还经常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其他大学授课。
双向学生交流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国学者从澳大利亚回国后,在全国各地创办了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戴维·古德曼和安妮·麦克拉伦在中国工作了数年,后来利用在中国的经历和人脉推动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两人都曾长期在中国进行研究和学术交流。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中澳贸易和商业往来急剧增长。在此期间,许多中国研究专业的毕业生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企业和国际企业找到工作。2010年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聘请了一批热情的澳大利亚年轻人担任导游和接待员。他们流利的语言能力给中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凯蒂·豪拥有语言技能和海外工作经验,但遗憾的是,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和企业缺乏兴趣,她只能用技能为澳大利亚的竞争对手服务。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研究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的缩影。
上述几人肯定会同意,从书籍、视频和学术讲座中固然能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但在中国的实际经历是无可替代的,尤其是在能够用当地语言交谈的情况下。这一真理不仅适用于澳中交流,也适用于其他双边关系。
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麦克福尔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麦克福尔写道,“我们绝不允许基于误解和错误信息的冲突争端。接触和互动有助于减少误解。即使是那些最强硬的对华鹰派,也应该像孙子所建议的那样,要‘知己知彼’。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学者和学生去过中国,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那里。”他认为,孤立会滋生不信任,美国需要培养更多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前往中国旅行并在中国学习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能重新焕发活力,并得到相关政策的支持。这将有助于我们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迈出正确的一步。这也是对马克林的最好纪念,本月是他首次赴华任教60周年。(作者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首任文化参赞梅卓琳,乔恒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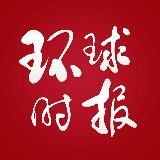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