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殿林老人是我中学时期的体育老师,1974年高中毕业一别五十年,我们师生不曾谋面。今年“五·一”过后,从允铃学兄处得知丁老师具体信息,遂相约去新河拜见老师。
开车的路上,我思绪翻飞,心动不已,中学时代的生活如影如视,和丁老师的过往亦如昨日。我学习不好,唯喜体育,故与体育老师有着特殊的感情。而丁老师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体育素质和对我们如兄如父般的关爱教育、关心体贴,更使我对丁老师有着偶像般的崇拜和尊重。
我极力回忆着丁老师的模样:高挑个子,四肢修长,清瘦脸庞,高高鼻梁,大大的眼睛讲课时常会看着斜上方,钢筋般的十指显示着力量。丁老师有着古铜色的皮肤,那是常年室外上课训练大自然的馈赠;丁老师头发有点稀疏,但都是倔强地向后梳着,偶用热水熨服,上课时又都被风吹起,球场上伴着一纵纵地跑跳,犹如一匹不驯的骏马。特别是丁老师三级跳、撑杆跳、标枪助跑、排球扣球时的潇洒雄姿,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还有丁老师长年穿着紫红色的运动服,配双雪白的田径鞋,更让当年的我们羡慕不已……
五十年过去,我们都古稀左右,丁老师还会像当年那样英姿飒爽吗?听允铃同学说,丁老师今年已经九十有三,想想社会上耄耋老人之状,我的心头不禁忐忑又惆怅。
路很顺,车子一直开到丁老师的家门口。我和允铃迫不及待地下车冲进一个整齐幽静的小院。闻声,造型别致彩钢板房的正室缓缓走出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丁老师!”“周建义!”声音未落我们师生已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其实见到丁老师的瞬间,我还是有些迟疑。面前的老人,慈眉善目,皮肤白腻,面容丰润,无斑无纹,额顶略疏,发乌须黑,俨然无像耄耋老人,如手非略颤,说不足古稀也弗疑。难道这真的是我思念半个世纪的年逾九十的丁老师吗?!待坐定后,我心底仍有些如梦如幻般的犹豫狐疑。
老师的眼睛比五十年前小了很多,但说到高兴处,眸子深处仍闪着当年的明亮。老师的身高从之前的一米八三,缩到了现在的一米七五,但身体仍挺拔如板,体重增加了三四十斤,也未见便便大腹。丁老师很健谈,我也有说不尽的心里话。我问老师铁富中学一别后教学工作及家庭生活的变化,老师问我一路走来的经历和个人家庭的目前状况;老师讲述记忆中我在学校体育活动中的点滴,我请教老师的养生之道……。我们谈地兴奋又激动,尽情又投机,恨不得再走一次浪漫青春,重来一回师生情谊。
本想宴请老师吃饭的,可老师每日两餐,中午不食。我们便遵老师旨意,在家里由老师女儿准备饭菜招待我们,而老师则搬个凳子看我们吃,陪我们聊。从见面到别离,我们的谈话就没停过,且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在说我在听。其间,老师谈及了许多在校时未曾说过的故事,这更加深了我对老师的了解和敬重。
丁老师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秀才,幼年家境尚好,有三百多亩地,为躲避族人伤害,老师十一岁时便独自一人被父秘密送往徐州读书。几经战乱,解放后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与尉天池是同学且多有交往。大学生时代,丁老师就是团支部负责人,大鸣大放及反右运动中,丁老师即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又正确把握运动方向,鸣放时引导同学相互开展批评,后期反右时,所负责的班级没一张大字报涉及对政治政策的非议,故没出现一个“右派”学生。
大学毕业时,丁老师已是党员发展对象并填表待批。工作后,校领导准备发展其入党,经过一些运动后,丁老师认为,以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性格,从政当领导很可能就会犯错误挨批挨整。于是,老师主动向学校表示,自己政治尚不成熟,有待进一步学习提高,之后至退休,始终奋斗在教学第一线。
丁老师本是南师大化学系高材生,参加工作后,正值全国响应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开展体育“大跃进”活动,而体育专业毕业大学生极其短缺,地区体委从已分配的大学生档案中发现,丁老师在校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是体育方面全才。遂主要领导出面动员已教化学的丁老师改行做体育老师。丁老师欣然接受并婉拒了领导其他方面的承诺,从此全身心投入到学校体育事业中,为邳州学生体育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生活的磨砺成就了丁老师善于学习,吃苦耐劳的性格,加之丁老师天资聪慧,谦逊执着,生活技艺无所能、无所不精。丁老师曾拜学校木工师傅为师,做得一手好活,60年代停课那几年,还和师傅一起背上工具去山东给人做过嫁妆、家具等木匠活,至今,家里还保存着他为儿女们做的书柜、饭橱、八仙桌。70年代初,社会推行新针疗法,丁老师很快自学掌握了针灸技术,不仅为同学治疗微疾小病,而且节假日还被铁富公社医院聘去门诊,为农村人民大众解除痛苦。另外,丁老师对烹饪技术也多有研究,连续订了十来年的《中国烹饪》杂志,烧得一手好菜,当年丁老师的宿舍对我们是全开放的,所以我们在那个简陋的单间宿舍里,着实享了不少的口福,而我糖醋蒜的制作既为丁老师传授,也使我受益匪浅。
丁老师一生淡泊名利,洁身自好。两次主动把个人增资指标让给困难老师,即帮领导解了工作难题,又助同事缓了经济困难。丁老师一生桃李天下,特殊时期救助数名领导,但丁老师从未利用其为个人家庭谋过利益,五个子女全部在基层凭自己的努力,生活得还算富足。丁老师说不清楚自己的工资标准,亦不知卡中的钱数,但有子女需要,便拿去自取,取款多少从无过问。按丁老师的话说,钱,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看得开,便活得明白,活得快乐,活得健康,活得长寿。
说到看得开,丁老师最崇拜自己的秀才父亲,当年三百多亩地时,共产党开展减租减息,而父亲竟将土地连同地契全部分给农民佃户。当国民党回来时,佃户担心反攻倒算,要把地契还回,老人家非但不要,还凭个人威望认个国军团长为干儿子,并严厉要求这个国民党团长要保护好当地百姓,不得侵犯百姓,受到乡里乡亲的赞扬和爱戴。我想丁老师如此优秀,应该是其传统家风的优秀传承使然。
说到长寿,丁老师告诉我,他八十五岁后发须由白变黑,目前除一口好牙外,各项生化指标皆如壮年。问其原因,老师说除心态要好就是生活规律。丁老师一辈子饮酒无醉,年轻时曾与几个同事骑自行车去郯城重逢镇与一山东老者斗酒,喝了四斤多仍正常骑车带同事回铁富。现在虽然仍不知酒醉滋味,但老师从不多饮,每次只喝二三两。丁老师常年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每天四五千步。一日两餐,按时按量,从不多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八点之前准时休息。另外,丁老师从不与他人论是非,争高低,生活简单,幸福满意。听老师讲话,犹感老师仍如学生般单纯净直。是老师返老还童吗?还是老师不忘初心,始终如一?
毕竟老师已近百岁,担心老师受累,四个多小时后,我们与老师依依惜别,并相约下次再见。回程路上,思绪如车轮,久不能平复,回味老师畅谈,不由衷感叹,丁老师——真乃聪明智慧老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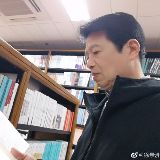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