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落”是一座县城的名字,取材自作家张楚曾经生活的县城。这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主人公万樱,便是他们其中平凡的一个。她的生活沉重平静又总是充满意外。围绕着万樱,许多故事在云落展开。人人都在时代的潮流里潜行,有的迷失自我,有的左右为难,有的笃定前行。
6月8日下午,思南公馆联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新京报书评周刊一起举办了张楚《云落》新书分享会,邀请作家张楚、《收获》主编程永新、《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和主持人罗昕一起分享张楚最新的作品,也是他首部长篇小说《云落》。
对谈中,程永新与黄德海分享了他们心目中的“好人张楚”,以及他们阅读《云落》的感受,小说里有鲜活的生活细节,有浓缩版的县城真实。张楚分享了他的写作人生,和对初次执笔长篇的反思,他庆幸当初没有决绝逃离自以为封闭的县城。最后,张楚回答了书评周刊“2024日常出逃计划”的提问,分享了他如何应对生活的疲惫。
下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内容有删改。

’《云落》
张楚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程永新:一部浓缩版的县城真实

程永新,作家,高级编审,现任《收获》主编。著有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气味》、中短篇小说集《若只初见》《到处都在下雪》、话剧《通往太阳之路》《我们这些人啊》(与人合作)、散文集《八三年出发》以及中国第一部“个人文学史”《一个人的文学史》。
小说原来在《收获》发表的时候叫《云落图》,出书后叫《云落》,“云落”的原型是张楚生活了很多年的一个县城。这是张楚第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他在县城生活的所有体验。这部长篇在我看来就是典型的县城,它告诉我们中国的县城是什么,通过这个县城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县城生活浓缩了中国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的细微生态,中国人怎么去做成一件事。比如我们怎样去开一个驴肉火锅店,我们在火锅店里如何与人交际、接触各个层次的人。官员、税务员、农民、外来者……各种各样的人在县城里都有所展露。
在《云落》之前,张楚有部中篇叫《在云落》,写几个年轻人在云落醉生梦死的故事。它与张楚其他作品的气质不同,写的是人的精神状态。张楚其他作品如《七根孔雀羽毛》等是非常写实的,细节非常扎实。《七根孔雀羽毛》中的“羽毛”是一种隐喻,是一种道具,将家庭生活的复杂、暧昧、难堪暗含其中。张楚很擅长为他的小说找到这种“物件”。《云落》里他写到了风,写到了云落的一草一木。他写的时候是贴着人物写的,每个人物都非常生动、世俗、有烟火气,你会觉得他们很熟悉,有小小的狡诈和算计,但又没有那么坏,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我们在编辑岗位干久了以后,很多东西浏览时会跳过去,但是张楚这部小说会让你我有兴趣读下去。我这次回读主要是看其他人眼中的万樱,细看这些片段能看出他(张楚)用了很大的力气,显示了一个小说家深厚的功底。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复调小说”在慢慢发展。二十世纪很多小说家都自觉把上帝之眼去除,让人物活在生活的状态里,比如《我弥留之际》在这方面就做到了极致,用众人的眼睛合成了一个故事,合成了一个世界。张楚的《云落》稍有不同,他写其他人眼里的万樱同时,也有故事主线,我在阅读时会关心万樱、罗小军、常云泽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情爱关系。当代中国写作的人,较少人能把情爱写得让人觉得不难受,很多人会避开。人有七情六欲,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在情爱中能够展现得活灵活现,写好并不容易。张楚能把情爱关系写得到位且细腻。角色之间的接触,构成了每个人不同的磁场,通过这一个个磁场组成了县城的网络,而这个网络就是浓缩版的中国现实。
黄德海:世界像春天刚刚醒来

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著有《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剑宗读书法》《世间文章》《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虚构的现艺》《驯养生活》等。
文学界有一个张楚,音乐界也有一个。说到歌手张楚,去年我们在北京一个做音乐的朋友说一定要把两个张楚放在一起做一场活动,题目就叫“楚楚动人”,我特别期盼这个活动。
文学界的张楚是一个公认的“老好人”。有一年我出差,跟别人有了言语冲突,特别不开心。回到宾馆以后已经十二点了,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发了一顿牢骚。我一般不太干这种事,发完以后大概不到一分半钟就删了,刚刚删掉,楚哥 (张楚) 的电话就来了,聊了半个多小时。他没有来劝我,也不打听什么事,他知道我不愉快了,就用这种方式安慰我一下。如果要让我把事情重复说一遍,可能会更生气。那天打完电话我睡得特别好。在我们这些朋友这儿,张楚的位置和作用不能用“老好人”来说,而是“有智慧的善良”。
我们从小地方来上海的人,大概都有一段县城经历。我所在的县城是山东最大的农业县,一马平川,我长到18岁,没见过山。来上海生活了十几年后,我忽然意识到,大城市是独门独户,县城是一个“家”,不管你有什么秘密、什么问题,都很难逃离。我们看《云落》也会发现,县城是一个大“家族”,人与人之间都有关系。县城有人情味,找熟人能解决事情,麻烦的是不能得罪人,不然他找两个人就能找到你外婆家。
有时候我做梦梦见我的家乡,冬天,路两旁白杨树落光了叶子,一阵风吹来,路上沙土扬得满天都是,吃的都是地里产的。但滦南(张楚曾经生活的县城)完全不同,那个地方靠海边,物产丰富。《云落》我先后看了三遍(成书前的书稿),最遭罪的一个情况是看着看着就饿了。他写的都是我喜欢吃的。比如书里写的炒青蚕,我没吃过,但是我喜欢吃山东产的豆虫。再比如他写海鲜,写三文鱼哪个部位最好吃,每个细节都活色生香。
《云落》这个小说里的世界,是一个我愿意进入的世界。它不是我非常讨厌的那种“悲苦现实主义”全是人性的黑暗,《云落》就是生活本身,你会喜欢这里面每一个细节,有草木,有鸟虫,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声音和性格。今天活动的主题是“世界春天般醒来”,我们会喜欢这个世界,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活力,像春天刚醒来一样,发现昆虫在活动,眼看一棵草露了头,这个活力一点点传到了小说当中。小说中最动人的活力,正如里尔克的一句诗所述,“如果春天来了,大地就让它一点点变绿”。
小说里我最喜欢万樱这个角色,她就是鲁迅《阿长与 <山海经> 》里的长妈妈,看着傻乎乎的,什么也不干,但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她就能折腾出一个东西给你,作为替代的安慰。长妈妈和万樱身上都没有太多道德伦理的约束,为生活而奔忙的人,顾不得生活应该怎样,为了吃口饭,为了欲望和情感,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万樱展现了特别自然的一面,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明天都会醒来。我喜欢万樱身上又混混沌沌、又活力四射的一面。读《云落》时,你会发现张楚对这些女性角色有一些小心翼翼的感觉,生怕自己哪里写得不准确,让她们受到无辜的伤害。我也从这本书里读出了命运感,每个人不是在按作者的安排前行,而是自己走完了自己的路。
张楚:庆幸没有决绝逃离

张楚,作家,《云落》作者,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中年妇女恋爱史》《过香河》《多米诺男孩》等。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孙犁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
我大学学的财务会计,毕业之后考了公务员,在国税局工作了18年。一开始在乡镇当企业管理员,后来调到县局税政征管科负责盐场和加油站的工作,然后又到办公室当秘书写材料,到党委办公室负责党务工作。
我以前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经常涉及逃离的话题。逃离封闭的环境,或者自以为是牢笼的地方,可能是每一个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轻人共同的愿望,尤其当他的职业和他的爱好不能完全重叠的时候,逃离的念想会更为强烈。
我和同事关系处得非常好,但老感觉自己很孤独。我喜欢写小说,偷偷摸摸地写,不敢让别人知道,和别人交流的愿望也不能实现。应该是在千禧年之后的一两年,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些写小说的人,礼拜六上午我会坐着大巴车去北京,找朋友们喝酒,礼拜天晚上六七点钟又坐大巴车往家走。当我的双脚又踏到县城土地的时候,突然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时隔多年回想那段时光,我很庆幸没有很决绝地逃离自以为很封闭的地方。县城生活为我的写作提供了非常独特的视角,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以前写过一篇随笔,讨论过逃离和回归的问题。我觉得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使命,可能上天自有安排,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不当公务员了,去当一名作家。一切好像都是命运在牵引着脚步往前走。
2015年3月我离开了滦南,调到河北省作家协会当一名作家,在那儿工作了四年后,2019年调到天津。这些年基本上是两地跑,有时候在滦南,有时候在天津。在创作《云落》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天津,因为正好赶上疫情,也很少跑动,每天就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写这部小说。当你在一座城市回望另外一座城市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种仪式感,好像中间穿过无数树木、村庄、铁轨、河流、工厂烟囱,才能抵达你的故乡。这种距离感让我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下意识会做一些美化,当你回想一个亲人或朋友的时候可能会忘记他平时对你的苛责或者对你的不好,这是很常规的人生体验。我在创作《云落》的时候,对小说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感情的,那种爱是发自肺腑的、特别平静的爱。
《云落》里面没有什么坏人,都是最普通的人,最普通的人写起来还是比较难的,我们老说画鬼容易画人难,我们对身边的普通人都太了解了,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要斟酌、要体察、要选择,才会真正写下来、记录下来。在天津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特别想念家乡,恨不得早点儿见到亲人和朋友。但是当我真的回到家里,新鲜劲儿一过,就想还是赶快回到天津吧,因为连续喝七八天大酒,每天都醉醺醺的,疲惫不堪。县城就像我的长辈一样,我从小在它的怀抱里长大,它知道我所有的痛苦和甜蜜,知道我所有的眼泪和欢笑,我无条件信赖它。它就像我的长辈亲人一样,用有点麻木的目光看着我,平静地审视着我,可能我一个眼神它就知道怎么回事,它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它说什么。这种扯不断,理也不乱的关系,可能是我在创作《云落》这部小说时一种长期的心态。
我以前写的都是中短篇小说,对中短篇和长篇的文体差异,认识还是很清晰的,可当我做人物小传或编织人物关系时,发现处理得有些简单和模糊,尤其是小说写到将近三分之一,十多万字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叙事速度很缓慢。我特别纠结,停了一段时间,思索着如何进行技术处理。
很多年之前有个好朋友和我说,将来你写长篇肯定会累死的,用短篇的语言去写长篇,肯定体力不支。我写第一章的时候,还是短篇的写法,后来进入情境、人物慢慢丰满起来之后,发现人物开始带着作者往前走,而不再是作者通过故事来推动人物的塑造。贴近具体生活场景、具体小说情节,你会忘了语言的存在,你只是跟着他们在叙事,在喋喋不休,所以语言没有成为一个困扰我的问题。
最让我觉得难处理的是结尾。原来的结尾是有朋友帮罗小军把麻烦摆平了,大团圆的结局,后来编辑老师看了之后,说罗小军必须失败,他失败了这个人物才成立,于是我又添加了两章,把事件进一步处理。开篇是一个离家出走的人重新回到故乡,结尾是一个新的出逃者诞生了,无论是从结构考虑,还是从人物设置考虑,可能会形成一个闭环,但是出版社的老师说,这个故事万樱是主人公,落脚点最后要回到万樱身上,最后我便以万樱的口吻给罗小军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这部小说里我下 了最大功夫的:要符合万樱的身份,符合她对世界的认识,还得把她对罗小军压抑的爱隐藏起来;另一方面,还要表现她压抑不住的渴望亲近的心态。
“日头出来了,她就睡着了。她睡着了,世界就安静了。”写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心里也安静了,小说里人物的关系也终结了。小说构思、写作、修改的时间可能有七、八年,每天我都和这些人物一起生活。早上起来打开电脑,万樱就出来了,罗小军也出来了,晚上睡觉之后这些人可能还在你的梦里出现。这种亲密陪伴的关系,让我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当小说最后一句话写完,我觉得既轻松又感伤。一方面小说终于结束了,可以给老师和朋友看看,另一方面终结了和小说里面人物的关系,以后可能不会再演绎他们的故事了,大幕落下,万籁俱寂,让写作者内心有一种悲凉之感。特别感谢朋友们平时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大家都提了非常好的建议,小说第一稿和后面定稿区别还是蛮大的。在修改的过程当中,我对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核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为我以后的创作积累了经验。
“2024日常出逃计划”
提问张楚
新京报书评周刊:一翻开《云落》便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你平时如何记录日常生活细节素材,有什么记录习惯与创作习惯?你对日常生活持有的态度是否也在你的表达之中?现在年轻人流行“微出逃”,逃离现在的生活休息一天、一小时再投入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去面对生活的琐碎,你怎么看,你与生活琐碎是如何相处的?
张楚:我是一个比较健忘的人,生活中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细节,或者聚会时朋友们说的俏皮话,我会赶紧用手机记下来。有一次跟散文家周晓枫吃饭,她说的每句话都是金句,你会感觉到被她碾压得一无是处,她一边吃我一边记,那顿饭我几乎没动筷子。还有方言、俗语,包括县城里又出现了什么重大的舆论或者桃色新闻,我都会赶紧记录下来。这些以后可能会变成小说里面很重要的细节。
其实生活中我不是一个特别细腻的人,虽然在和人打交道、观察人的过程当中可能眼光会比较细腻,总体而言还是个粗枝大叶的人,我经常丢东西,背包里特别乱,随手一捞就能捞出香烟、打火机或者一些药物。可对生活中突然超越了日常规范的一些行为和言语会格外敏感,也会在文本中有相应的表达。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太不容易了,虽然受过了良好的教育,可就业压力很大。有一次打出租,司机和我聊天,他原来是机构的英语老师,物质方面的失落和差距可能会让每一个人对生活都有小的抱怨,但是他又很乐观,除了开出租车,还到一家私立小学兼职当体育老师。我调侃说,你戴着近视镜,又这么瘦,体育课怎么给他们上?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我感觉这种微出逃,可能是缓解情绪压抑非常好的方式。他不可能有大把的时间和更多的物质真的去世界各地旅行,去感受不同的阳光和不同的人,在微小的范畴之内伪装成出逃的样子,也是自我安慰中比较有仪式感的办法,蛮好的。
我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有疲惫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写作、工作,生活是一种没有波澜的状态,缺乏一种激情。这时候我会逛逛商场,或者看一场电影。旁边都是年轻的男女,想到自己初恋时候的感觉也挺好的。看一部好的电影,也会打开固有的观念和想法,那些神来之笔的影像会启发我用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日常生活。我们都是普通人,都过着普通的日子,怎么在有限的资源之内让自己的生活不要和这个时代脱节,不要出现大的裂缝或者裂隙 (真的出现大的裂隙可能就掉进去了) ,还得自己来实现调节,来安抚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微出逃,假装休假出逃的做法也蛮好的,如果哪些年轻朋友觉得没意思可以来天津找我,我请你们喝酒。天津菜是一绝,尤其是早餐。天津人没有夜生活,因为他们很着急,要早早休息,满心欢喜地等待着第二天的早餐。吃一顿丰富的早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天津这座城市风景很美,人们豁达开朗,喜欢听相声。我去公园遛弯时,发现有个大姐双腿挂在杠上,在表演“倒挂金钟”,她好歹有七十五六岁了,还悠闲地和两个老头聊天。天津是一座非常有意思的城市,希望大家有时间来逛逛街,喝喝酒,聊聊天。
扫码查看直播回放
运营团队
整理编辑 吕婉婷
海报设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本文校对 刘军
新京报书评周刊
隶属于新京报的文化领域垂直媒体,自2003年创刊以来,新京报书评周刊深耕于文化出版动态,向读者提供有关文学、社科、思想、历史、艺术、电影、教育、新知等多个领域的出版动态与学界动态,提供诸如专题报道、解释性报道、创作者深度访谈等深度文化内容。
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日常出逃计划”
2024年,新京报书评周刊推出年度主题“2024日常出逃计划——一场以阅读为名的脑洞漫游”。在全年的采访与活动中,我们将收集嘉宾面对日常生活,借由阅读与创作获得了哪些超脱生活琐碎的发现性时刻,如何在阅读和思考中,重获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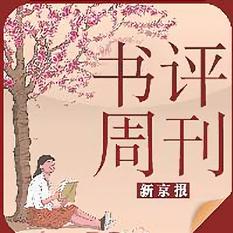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