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一个吉林市人,松花江上有什么奇观,恐怕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起雾凇。凭借银装素裹、晶莹剔透的妖娆丰姿,雾凇与“不冻松江”一起,曾获江泽民总书记盛赞“寒江雪柳,玉树琼花,吉林树挂,名不虚传”,成为吉林市松花江自然风光的特殊名片。然而这一冬季美景并非亘古而来,出现的时间至今尚不足百年,在此之前,吉林城曾有其他与众不同的奇景,在不同的季节增益着松花江的无穷魅力。
一、春季木排漫江
有人说“开江”应该是当年吉林城春季江面上的奇观。然而我觉得在东北地区,江流“开江”流凌并非吉林城独有,也不以吉林城附近的最为壮观,在春季实难与“木排漫江”相提并论。
还是在丰满大坝建设之前,每年春季,大地回阳,冰雪消融,山水汇成川流,滔滔然注入松花江,形成了名为“桃花水”的春汛。清明时分,桃花水顺山势,穿幽谷、越险滩,回旋奔涌着来到了东北最大的木材集散地——松花江畔的吉林城。顺桃花水而来的并非只有春水,这当春之际正是“木帮”放木排之时:一架架木排乘波破浪,在松花江——天江上,由山岭高地“从天而降”,也让那洪涛“汛情”承载了造福民众的“好水”之名。
松花江上的木排为木帮在前一年的十月之后采伐的木料,去掉边枝斜杈为“原木”,牛拖马拽至河川之侧的楞场“归楞”码放。春水起时,人们在原木两端凿出“串眼”,用粗麻绳串联,结成筏子。通常在清明之时,在江边祭祀龙王、河神、风神后,开始放排。放木排过程非常辛苦且危险,尤其是松花江上游水急滩险,但是对靠山林吃饭的人来说,这就是生活,这也是希望。
据记载,水情好时,木排可日行三百里,一般几日就可抵达吉林城。此际从西关的头道码头到东关的东大滩,江面上一时间到处铺陈绵延的都是木排,仿佛是要用木排把江面遮盖起来一般。仔细观看,这气势壮观的木排并非原木结成平板一块,上面还另有风景:木排上建有木板小棚,其中住人的叫窝棚,做饭的灶间叫锅棚。因为尚不确定多久能将原木卖出,木排上甚至还被种植了蔬菜,以备日常之需。于是这木排也成为吉林城春天江上的特殊景观,引得城中好奇之人到江边围观。
二、夏季鸬鹚捕鱼
到了烁玉流金的夏季,吉林城的松花江江面上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这种热闹并非由“千帆竞渡、百舸争流”而生,而是由“渔船往复、水鸟翻腾”而来,这便是当年松花江上最著名的奇景“鸬鹚捕鱼”。在当年,东莱门外的松花江上,相对于主城区码头丛列的江段,则略显安静,江流也没那么湍急,是不错的“渔场”。尤其是木排陆续上岸后。江面上波光粼粼,薰风送暖,此时便有许多渔民挥篙弄桨,驾驶小舟在松花江上游弋穿梭。
就在渔船的船舷上,一排排鸬鹚如水兵一般傲然站立,这些“水兵”是渔夫的捕鱼助手。鸬鹚曲项长喙,有黑、白两种毛色,其中黑色最为常见,因而便有了“水老鸦”的绰号,意思是说鸬鹚像乌鸦一般黑。鸬鹚擅长游泳和潜水,除脚蹼外,甚至翅膀也进化到能够划水。凭此技能,鸬鹚可扎入水中,捕食鱼类和甲壳类动物。鸬鹚在水下捕到猎物后,无法直接进食,会先将其存于喉囊,上岸后再行“享用”。利用这一特点,渔夫驯化鸬鹚,采用“掐喉取物”的方式,把水鸟成了特殊的“渔具”。
捕鱼时,渔夫以长篙为“指挥棒”,驱动鸬鹚钻进江流之中。鸬鹚入水后一旦发现猎物,则半跃出水面,再翻身下潜,不多久,便又挺着变得粗大的喉颈钻出水面,并配合渔夫取出渔获。由于这一过程观赏性很强,总能引来许多人围观,一来二去,就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观光表演”。到后来,甚至有一些游船专程载着游客到渔船旁边,近距离观看。渔夫也乐得在单调的劳作之余,向游客“炫耀”。
在老照片中,就能看到渔夫含笑架起一只白色的鸬鹚,颇有让“名角亮相”意味。到后来,一些渔夫干脆配合游船,把鸬鹚带到游船边表演。鸬鹚捕鱼的情形也被日本人称作“鹈饲”,当成吉林市近郊特色的观光项目大肆宣扬。然而鸬鹚所能捕到的鱼,终究不太大,松花江上最壮观的捕鱼场面是在鸬鹚捕鱼出现之前的年代。
三、秋季“七上八下”
“……小鱼沉网大鱼跃,紫鬣银鳞万千百。更有巨尾压船头,载以牛车轮欲折”。这是清代康熙帝东巡吉林时,观看松花江渔获丰收的场面后乘兴所作《松花江网鱼最多颁赐从臣》中的词句。大轱辘牛车,轮子都要压折了,可见所捕“巨尾”之大绝非鸬鹚所获猎物可比!
在清代,由于清廷修壕插柳,以“柳条边”保护所谓“龙兴之地”,严禁“民人”到柳条边墙外开发土地、森林、矿藏,这使得吉林周边人口稀少,呈现一派“山峰皆有森林覆之,草木到处丛生……”(《满州地志》)的原始风貌。当时江阔水深的松花江,水质清澈,鱼类繁多。在清代道光年间萨英额所著《吉林外纪》中,就记载松花江中产有鲟鳇、细鳞、鲫鱼、鳜鱼、鲂鱼等多种名贵鱼类。
从清初开始,吉林城迤北江段还被清政府划为专供皇室获取的贡品产区,由内务府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管理,该机构所辖旗丁内设“额斤采捕营”,营中又有网达、鱼达、护运拨什库等职务,专司贡鱼的捕捉、驯养、运京入贡诸项差使。由于打牲衙门的垄断,客观上也使得江中渔业资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常言说“物以稀为贵”,在松花江中按季出现的洄游鱼类——鲟鳇名气最大。可换个角度审视,鲟鳇的数量必定有限,收获最大的洄游鱼渔汛通常是指秋季的大马哈鱼。《柳边记略》中记载:“大发哈鱼,一作打发哈,子若梧桐子,色正红, 噉之鲜水耳。其皮色淡黄若文锦,可为衣裳及为履袜、为线”。
大麻哈鱼渔汛出现在立秋之后。《吉林市水利志》记载,大马哈鱼一般在农历七月由黑龙江口逆流而上,蜂拥至松花江上游产卵。到农历八月,小鱼顺流洄游回大海。故而这个渔汛期,松花江上渔船穿梭,江鱼翻腾跳跃。船中渔人喊号奔忙,岸上观众惊呼雀跃,如临盛大节日。吉林城因渔汛时间甚至派生出一个形容场面热闹、混乱的名词——“七上八下”。
在康熙帝的诗歌中就有这种捕鱼场面的描写:松花江水深千尺,捩柁移舟网亲掷。溜洄水急浪花翻,一手提网任所适。须臾收处激颓波,两岸奔趋人络绎……诗句虽不是记录秋季渔汛,但热闹的情形大同小异,借用以描述吉林城松花江的秋季奇景,并无不妥之处。
四、冬季冰上客栈
吉林地区流行的《数九歌》中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在丰满水电站还没有竣工的年代,吉林城区的松花江滚滚江流,会在农历十一月之后逐渐冰封盈尺。每逢此时,江面上就会有人“因岸为屋,凿冰立栅以集行人”(《吉林通志》),设立季节性冰上客栈——“水院子”。
晚清时节,由于东北封禁制度破产,闯关东浪潮已为吉林城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每年冬天,进城销售大豆、杂粮、烟麻、皮张、山珍野味等土特产品以及木柴的农户和客商,会赶着大型畜力爬犁,顺冰冻的“江路”呼啸而下。抵达吉林城后一边卖出产品,一边采购布匹、糖盐、灯油等各种杂货。而水院子就是为这些“老客”提供食宿歇脚的廉价客栈。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行,冰上客栈悄然形成了“行业”,水院子也开始成为吉林城冬日里一道别样的江景。
水院子之所以兴盛不仅源于晚清开始吉林周边开发而产生的经济繁荣,还与吉林城特殊的城市规划有关。吉林城滨水而立,城内的街道“布局不很规整,随着大江弯曲……由河道河床形成的”(《吉林民居》)。在晚清时候,冬季临街住宅、商号,都会将院内积雪随意倾倒、堆置在道路中心,只待开春一并消融。由于缺乏相应的市政管理,雪堆只会越积越大,于是在城内本就狭窄弯曲的街道中间,会形成一条纵贯道路、高低起伏的“雪山”。
空载的车辆、爬犁在城内错综复杂且“雪山连绵”的道路行进尚极其困难——稍不留神就容易打滑、坐坡,甚至碰坏临街住户的木障子,更何况需要会车、调头的重载车辆和爬犁呢?因此,城内虽不乏接待客商住宿的大车店和客栈,但并非冬季客商的首选。反倒是松花江冰面上的水院子,平整宽绰,够“局势”、够“眼亮儿”,停车存货更为方便。
据《吉林旧事》等资料描述,水院子的建造多是由近岸处向江心延伸,建筑面积由经营者按需圈定。边界凿沟立木,再填雪、泼水冻实,形成冰木结合的院栅栏。栅栏留一口,树长杆为门,上悬字号牌匾,“冰上孟尝君子店,八方车马客来投”之类对联贴于门框两厢,另挂三个箩圈为幌,以示开门营业。
水院子名义上是简易的季节旅店,实际上却是一个特殊的交易平台。“爬犁(大车)拉来的货物,有的需要进城去卖,有的坐地就可成交”(《吉林旧事》)。尤其是山里拉来的各种木柴,樵夫为节省开销,往往会直接卖给水院子,这使得吉林城几乎所有的水院子都经营烧柴(俗语柴禾棚子)。集中的季节性客流、频繁的物资交易,让冬季吉林城的江面上,每一家水院子皆爬犁、骡马川流不息,车辆、客商熙来攘往,生意好不火爆。
时光荏苒,自修建丰满水电站开始,旧时江景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松花江并未因此而变得乏味,作为特殊的补偿,寒江雪柳成为吉林市松花江水全新的景观,为这座城市增添着特殊的”水之韵“。近年来,随着市委、市政府对文旅事业的重视,松花江水新景观层出不穷,在老桥遗址复建、新港加速建设、观光航道开通等举措下,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人们有理由相信:新时代的松花江四季奇观即将陆续出现!










本文为优雅的胡子原创文章,其他自媒体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特别鸣谢贾大为(易林学馆)先生对本人撰写此文给予的支持和鼓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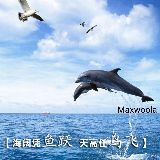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