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宇宙中智慧生命的稀缺现象,我们可以这样来概述费米悖论的精髓:宇宙之浩瀚孕育了无数星系,诸多星球在适宜的环境下,理论上应孕育出众多的文明,其中一些本应与我们有交集,然而现实却是寂静无声。
数学公式可将我们可能与之沟通的文明数量表示如下:

基于现有数据,我对于“宜居星球”以及“生命在该星球的出现”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毕竟地球上生物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已是铁证。
然而,一些人过于乐观地估计了“生命将进化为智慧生物的概率”。似乎有生物存在,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洗礼便会“进化”为智慧生物。这是真的吗?许多人所理解的“进化论”似乎是一种有“方向性”的过程,即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似乎就是进化的“目标”。“进化论”在很多人心中变成了“生物进步论”。
达尔文真的正确吗?
让我们看看乔治·威廉姆斯的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在这部作品中,他提出了质疑,即“高等动物”是否真的比“低等动物”更为先进。
就基因数量而言,人类甚至不如我们日常所食的稻米。水稻的基因数是人类的1.7倍,而简单的线虫基因数也有近2万,与之相比人类是2.7万。甚至小鼠的基因数量都超过了我们。实际上,任何脊椎动物的基因数量都不少。

就复杂性而言,人类确实拥有最复杂的大脑,但我们的皮肤却比不上鱼类的复杂,而鱼类的皮肤复杂性又超过许多陆地哺乳动物。从“适应性”角度来看,最简单的细菌与人类相比毫不逊色,而我们身边的蟑螂适应性也是极强。在人类与细菌的斗争中,人类谈不上全面胜利。还有许多生物出现了“退化”现象,不信就摸摸你自己的尾巴。
简而言之,“进化”是没有固定方向的,它本质上只是变化,是适应环境的变化。
达尔文本人曾说过:“经过长期的思考,我无法认为所有生命体都有着自然的、必然的进化趋势。”
变化实际上是自然选择的副产品。如同古尔德的观点,“适应”只是适应包围着物种的具体环境,在适应过程中,生物可能走向复杂,也可能走向简单。那么如何解释一些生物比另一些更复杂呢?从简单到复杂,在简单的一端虽然生物种类众多,但在复杂的一端也有一些生物存在。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古尔德打了一个比方:
简化的一侧有一道墙,因为简化不能无限进行,到了细菌这种复杂程度就已是极限,不能再简化了。而“复杂”这一侧没有“墙”,可以无限延伸。古尔德做了这样的比喻:一个醉汉在路上摇摇晃晃,他的右侧是一堵墙,左侧是一条沟壑。醉汉可能会向左右任一方向迈步,既无既定的规律也无方向上的偏好。然而,墙限制了他的右侧移动,他时而向右撞墙,时而向左接近沟壑,当某次向右走得更远时,他就会跌入水沟。醉汉们虽然频频跌入水沟,但向左移动并非必然,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偶然,是被动的。

也就是说,生物走向高度复杂是一种被动而偶然的现象,并不是某种必然。醉汉本身并不想落入沟中,是环境逼迫他如此,如果环境足够好,他可以不掉入沟中。这个比喻说明,生物走向复杂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此外,“复杂”并不代表“智能”。这是人类的自负,将自身的特点视作某种顶点和标准。复杂可以是任何适应性的特异化,智能并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现在,你应当理解了,“智慧生物”的出现并不是必然的。如果历史重演,人类可能不会出现。
有人认为“智慧生物”占据了某种生态位,因此一定会有生物出现来填补这个空缺。但恐怕这种想法过于一厢情愿。以澳大利亚为例,这个孤立的大陆上进化出了与其他大陆的许多“平行动物”,但他们并未出现蝙蝠、大象或人类的“平行类”。澳大利亚并没有出现有袋类的灵长类。这一点说明,别说智能了,就连“灵长类”都不是“必然”。即便澳大利亚的动物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祖先。

再以人类祖先为例,现代分子生物学揭示,人类的先祖两次走出非洲。第一次是100多万年前,演化成各地的直立人(包括“北京人”)。

第二次是2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智人最终成为我们的祖先。那些先走出去的亲戚并没有发展出高智能,而是被后来的非洲亲戚所取代。理解了进化的无方向性,你就能解答一系列愚蠢的问题,如“猩猩未来能否进化出智力”,“为何低级的细菌还未进化成智能细菌”等。
即使有地外智慧生物,我对它们是否能发展出高级文明也持怀疑态度,因为智慧生命所处的客观条件可能在文明发展之前就导致了它们的毁灭。
再次回到最初的德雷克公式,其中的生命和智慧生命这两个因素可能非常小,几乎接近于零,因此尽管存在庞大的“基数”,我们可能仍然是“孤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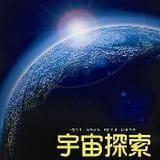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