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白书农的书房, 一张传统中式书桌之上,一颗雪白的“大脑”静静端坐。“这是我的脑子”,白书农笑着介绍道。这是他在北大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磁共振成像中心的朋友帮他做了扫描后,经3D打印而成的大脑模型。作为年近七旬的生物学研究学者,白书农的书房除了此处颇具科技感的“前卫”,其余各处,都有种古色古香的意味。

他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荣休教授, 是2020-2021年博古睿学者, 也是年近七旬的网络专栏作家。 在书页与屏幕之间, 他在植物发育生物学研究领域深耕细作, 为解开生命谜题不懈努力。他 将目光投向人类认知起源的宏大命题, 试图探寻科学与哲学的深层联系, 以“十的九次方年”的时间跨度为线索, 踏上探索生命奥秘的奇妙征程。
人如其名,白老师爱“书”,钻研“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book farmer”的书房,探寻那些隐藏在书籍背后的故事,感受知识碰撞出的独特魅力。

采写 |王梓寒
摄影 |曹梦瑶
农人的云雾斋
白书农的书房门上挂着一块小巧的“云雾斋”牌匾,那是白书农请父亲所题,勾勒出一方雅然天地。目光收回,门内正对着的是一整套老式的组合音响,上置一个小香炉,颇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向左,靠墙两个实木圈椅夹一方茶几,对面是日常阅读的木质书桌。电脑则远离书桌,靠窗放置,似乎与此清净之地画了一条界线。

白书农常说,自己是一个“念旧”的人。这一念旧,体现在家中的陈设上,也体现在书籍上。书架在进门右侧,顶天立地,塞得满满当当。书籍大致按类别摆放,乱中有序,领域宽广,不少书籍已俨然有了些年头。上方是成套的中国古代哲学作品,生物专业类书籍与人文社科类专著交叉而立,其间不乏几本教育学、语言学的书籍。近期在读的书,则放置在最顺手的高度,方便取阅。习惯了纸质阅读,即使是网上觅得的电子书籍,白书农也通常打印下来,占据了书架一隅。

白书农的书籍分布在三处。除了书房的藏书,还有楼梯转角的书柜,收藏的大多是专业类书籍,“不像文科学者,这些零零星星的书,实在不好看,就拿个柜子封起来。”白书农谦虚道。另一处则是楼下客房中四个老式的铁皮文件柜,里面整齐排放着文献资料,“年代感”与“前沿感”咬合得完美无缺。“这是在研究时收集的文献。因为很多资料在写《植物发育生物学》第二版时要用。退休后办公室要还给学院,我就只好把这些文件柜搬到家里了”,白书农笑着说。

白书农从事的是前沿科学研究,可在他眼中,阅读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于实验室中,每日面对琐碎的工作,白书农很早就意识到深度思考的重要性。在负责实验室管理时,他借鉴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的句式,要求同学们每日反思三个问题:
第一,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第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第三,你做这件事预期是什么结果?
对学生如此,他自己也同样以此标准自省,避免在日常琐碎的工作中陷入盲目。
这也是他书房所挂《大学》之言条幅的意义——“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点缀,也是鞭策。

在他看来,阅读恰是打破思维桎梏、实现 “zoom out”(跳出框架)的有效途径。当下的教育环境,往往倾向于“push”大家zoom in,这使大多数人容易过度聚焦于细节。
有些人以为多看文献就视野宽了,实际上不是,你要有纵深感,要从具体问题里跳出来。
白书农对此颇有感触,“怎么跳出来?这时你就要读书,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就像所谓的‘上帝之眼’或‘bird's eye view’”。得益于阅读赋予的宏观视角,白书农在评判具体研究项目时更加得心应手,能够更好地判断研究方向的新颖性、重要性和可操作性。
谈及如何平衡前沿和经典阅读,白书农有自己的理解。“什么叫‘前沿’?”他抛出反问。这个看似不言而喻的概念,在他眼中却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你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他强调,要理解前沿之所以为前沿,阅读经典著作便是关键。
“现在大家读文献只读二十年以内的,”他感叹道,“这对于了解所研究的问题最初是如何提出的,远远不够。”在他的书架上,一本1933年出版的《Sex in Plant World》被悉心保存着。在植物性别研究领域,这本书开创性地用单性花来定义植物性别,对之后90多年的植物性别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实验室对于黄瓜单性花十多年的研究结果,白书农发现主流观念中存在本不应存在的内在逻辑悖论。在追溯主流观念的来源时,他从这本书中找到了源头,并从这本书用单性花来定义植物性别的具体表述中发现了逻辑悖论。由此,他进一步确定,基于自己实验室工作所提出的,植物单性花发育不是性别分化机制,而是促进异交机制的判断,完全可以解决主流观念中的内逻辑悖论。
一场回归之旅
白书农的名字,冥冥之中融合了他所热爱的 “书”与钻研的“农”。说起来,他的专业选择还真的和名字有关。1977年恢复高考,白书农报了三个志愿,却均未被录取。恰是因为名字中的那个“农”字,让他的档案被安徽农学院的招生老师选中,也由此,开启了他与书籍、与植物生物学的相伴之旅。
在他的阅读轨迹中,有一条清晰的“回归”脉络。幼年时,他从热爱“听故事”开启了阅读启蒙。步入大学后,正逢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开始对西方的理论思想产生兴趣,在朋友的影响下,他开始涉猎科学哲学与历史类书籍,拓展认知边界。
然而,彼时植物生理教科书却成了他阅读的 “主角”,这背后是无奈的现实。在武汉大学读研时,经费紧张,一个研究生每年仅有3000元研究经费,投入科研便不够用。他的硕士导师,当时生物系的主任肖翊华老师建议他们,在研究生阶段好好研读教科书,特别是国外经典原版教材。于是,白书农一头扎进这些书里。每一本教科书都犹如一部详实的学科编年史册,将学科起源和发展脉络都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白书农得以对植物生理学这一学科的全貌有了宏观把握,进而清晰地理解所从事具体研究的意义。
我后来做植物研究时有一种历史感,就是从那时候培养出来的。
后来,身为教育者的白书农在课堂上也常会问学生:“你们现在还读教科书吗?”然而,得到的答案却令他忧心忡忡。在他看来,不读高质量的经典教科书无疑是极大的损失。缺失教科书系统知识的构建,知识获取零散破碎,难以稳固地支撑起深厚的学术造诣。

工作后,现实的忙碌与责任让学生时代的阅读喜好不得不暂且蛰伏,专业书籍占据了他大部分的阅读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怎么读书。”白书农坦率地承认。
重拾书本需要时间,有时也需要一定的契机和推动力。直至2012年前后,两位书友的出现,为他的阅读之路带来了转机。一位是经常来访北大生科院的芝加哥大学演化生物学教授龙漫远;另一位则是学院从事生物信息研究的陶乐天。与这两位专业不同的教授均因同在金光楼,在走廊上相遇而结识。在白书农眼中,这二位皆博览群书,博闻强记,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益友影响下,他重新捧起书本,开始比较系统地每天读20分钟。
“贾雷德·戴蒙德的那本《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陶乐天推荐和送给我的。”白书农向来有在书上做笔记的习惯,密密麻麻的字迹承载着他的思考与感悟,因此读过的书一般不便再给他人,便又购置了一本来读。后来陶乐天得知此事,大方地让他安心留存赠书。如今白书农的书架上保存着两本《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也成为他向人推荐的首选。
白书农的阅读经历中,还有一位特别的同行者——华盛顿大学应用数学系教授钱纮。钱纮教授虽置身数学领域,却有着令人惊叹的阅读广度。二人合作期间,经常探讨生命的起源等命题,白书农也屡屡被问道:“这本书你读过没有?”谈及这段经历,白书农诙谐地回忆道:“整个2016年我完全在做他布置的‘家庭作业’”。

“书农”之“书”,亦在岁月沉浮中托举着“书农”之“农”。回顾自身科研历程,白书农感慨颇多。博士毕业之后,他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实际体验与此前从阅读中构建的印象大相径庭。巨大的落差让他一度觉得科学研究工作索然无味,甚至萌生放弃的念头。然而,他心有不甘,“是不是我还没真正了解什么是科学?”1991 年,他选择前往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才在不断探索中发现科学研究真正的魅力所在。
我这一辈子经常退隐,觉得做这事没意思,干脆撤了算了,但阴差阳错又被拉回来。
这般经历,恰似汤因比所述的“退隐与回归”。起起落落间,书籍如海亦如舟,让他在实际工作的发现与困惑和阅读的字里行间彼此呼应中,逐渐明晰科学的本质,也为自己在错综复杂的科研道路上找准了前行的方向。
于白书农的阅读耕耘之旅,我们似乎也能窥见自己的身影——由懵懂开启求知,从迷茫迈向坚定。或许因现实压力搁置热爱,又在偶然契机下重拾书本,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迁,阅读始终有着拨云见日的魔力。而这所有因阅读而生的智慧、力量与成长,都在时间的沉淀中熠熠生辉。
人文学科,应当学一些生物
从搁置到重拾,变化的不仅仅是阅读的时长,更是阅读的选择。“现在读书不是完全随意的,因为书太多了。”如今的白书农,更多践行着“问题驱动”式阅读。“比如《The Equation of Life》这本书,2013年前后,我在想生命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有没有可能用简单的公式来表述。恰好有个朋友告诉我有这么一本书,我就赶快买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现在的读书方式是一种问题驱动,你在思考问题,然后去阅读相关的书籍。

这些问题的来源,一方面源自科研与授课过程中的思考,而深究起来,思索的核心自始至终根植在白书农的学习与研究历程中。“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植物?”他将多数人研究植物的目的概括为两点:“一是把植物当成食物,二是把植物当成玩物。”但除此之外呢?“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么多年研究植物,背后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希望了解生命是什么。而了解生命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了解人是什么。”
正是对“生命为何”这一核心问题的执着探索,推动白书农在书海不断遨游,也让他敏锐捕捉到生物与人文之间隐秘的共通之处。
不能只停留在轴心时代以降的两三千年的时间里,那样没办法回答人之为人的问题。
白书农一直在呼吁,人文学科的人一定要学点生物。“我觉得人文学科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需要了解一点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在他眼中,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关注科学,可那时多聚焦于18、19世纪的数学、物理、化学。近百年来,生物学迅猛发展,这些知识与人类行为的关联其实更加紧密。“但很可惜,我们现在人文学科的老师和学生对生物学的理解,我觉得都是‘令人惋惜的肤浅’”。
从生物学视角出发,有时候能对日常的困扰和焦虑有新的认识。白书农直言不认可“做自己”这种说法,“人作为一个多细胞真核生物,与生俱来地以两个主体的形式存在:一个是个体,一个是居群。”自启蒙时代起,将所有人视为相同个体的这个逻辑前提本身存在偏差,因为它忽视了居群的本质,并不是很多相同个体的集合,而是以个体为载体的多样性DNA序列库。这一点在启蒙时代,先贤们是不知道的。用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说,就是生物学中的濒危物种,其濒危不只是数量少,关键在于DNA序列多样性的丧失,而DNA序列多样性恰是真核生物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因子变化的核心机制。
基于这样的认知,他发现,人类因认知能力出现而衍生出的居群组织中的分工协同现象,使得个体只能在扮演社会角色的过程中获取生存资源。由此,当谈及 “人生意义”的问题时,他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人生意义就是找到能够发挥你长处的社会角色,然后去扮演好这个角色。
在白书农眼中,竞争归根到底是观念问题。他推荐大家阅读《观念的跃升》,书中展现了人类社会,尤其是他刚刚读到的19世纪,因观念局限发生的诸多奇异之事。“人类的历史一直是符号(概念)及其代指对象两者之间分离与整合的动态过程。”

白书农也坦率指出,对生物学了解的缺失,并非人文学科师生的过错,而是生物学研究者自身的问题。在和朋友讨论这个问题时,因为朋友的激将法,2016年他在暑假学期开设了《生命的逻辑》课程,并将授课内容整理成书。如今,白书农仍坚持在暑期开设这门通选课,向各专业学生敞开大门,至今已持续八年。有北大校内文理医工十多个院系、专业,校外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选修过这门课。
这也是他担任博古睿学者、从事大众科学写作的初衷。“用尽可能简明的文字介绍我所理解的‘生命’,来帮助大家面对‘人是生物’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
在授课中,他也在琢磨如何为大家清晰阐释“人是生物”的事实。后来,他找到一个简单的表达方法——数数。从10的0次方年开始,依次递增,10的10次方是100亿年。“整个宇宙的历史也就是10的10次方年,138亿年或者137亿年,对不对?细胞化的生命系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四十亿年。就是十的九次方年。”《十的九次方年的生命》,正是他大众科学作品的标题。
不是科普,而是大众科学
从事大众科学写作,对白书农来说其实是童年时期埋下的种子。那时,家中订阅的《科学画报》与《航空知识》在他心底悄然种下对科学的好奇。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意识到,“科普”这个概念在时代的洪流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拿《十的九次方年的生命》这本书来说,白书农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 “大众科学”作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科普读物。
在白书农心中,大众科学与传统科普有着本质区别。传统科普往往是将知识灌输给受众,而当下的大众科学写作,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用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分享自己的思考过程与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大众科学”作品与学术专著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一些人文学科的书籍,也有类似的特点 “《物种起源》是科普读物吗?”他笑着问道。

回顾中国科学传播的历程,早期以科普形式引进科学成果是合理且必要的,毕竟中国并非现代科学的发源地,在引进过程中需要有效的传播方式。但经过多年发展,白书农认为,中国的科学传播应当有所突破与创新。在给实验室研究生的毕业纪念礼物上,他写下寄语——“让自己的目光越过前人的肩膀,投向广阔的地平线”。在他眼中,每个人都站在未知自然的面前,没有必要一直依赖他人的视角去认识世界,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视角。观察、思考、传递思想,这与使用何种语言无关,关键在于写作者的创作初衷。
然而,如何运用大众日常语言来阐释人类认知中那些鲜为人知的领域,是当下科学传播面临的关键挑战。专业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如同“土匪黑话”,虽简洁高效,却只为同行所理解。当面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时,就必须摒弃这种专业“行话”,转而思考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日常语言把事情的特点讲明白。
“乐高积木的零配件是怎么生产的?”这一看似聚焦工业生产的表述,实则是白书农作为博古睿学者为博古睿中心写的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如同乐高积木零配件生产的流水线,中心法则所揭示的过程,只是以模板拷贝的形式,高效生产蛋白质的流水线。”在其《十的九次方年的生命》中,类似这般生动鲜活的比喻与表达俯拾皆是——借助乐高积木的零配件及其拼搭的玩法,解释生命系统及其组分之间的关系;以“漩涡”为喻,帮助理解生命系统的动态属性;还有“抱团取暖,合则两利”“既生瑜,何生亮”等成语俗语,都成为白书农引人入胜的妙法。
灵感来源固然扎根于生活,而让灵感破土而出的,是实践中遭遇的难题与持续不断的思考。当现有术语难以尽述时,创造或探寻新的符号来加以阐释,便成了必然之举。这也进一步引发了他关于“符号”的起源与功能的思考。
在白书农眼中,科学认知是一种只有500多年历史的独特认知方式。其特点在于以实验这种“双向认知”方式,检验符号及其代指对象的匹配度。这在人类演化进程中第一次可以为认知提供客观性检验。而哲学则是对符号(概念)内涵的辨析、符号间关系的梳理、概念框架的构建与重构。从这个意义上,目前大家所谈论的“科学”其实包涵了两种属性不同的认知过程,即从伽利略时代因实验方法的出现而出现的“科学认知”,和轴心时代就出现的“哲学认知”。很多人将“科学”和“哲学”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其实是对“科学认知”的本质缺乏理解的结果。正是对符号问题思考的驱动,他的书架上才多了那本《From Hand to Mouth: The Origins of Language》,成为他探索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又一把钥匙。

白书农的思考,关乎历史,更关照当下——我们如何在符号化媒介的出现所衍生出的生存能力不断外化的过程中,重新定义学习、思考与存在的意义。在一次讲座中,他向学生抛出问题:AI时代来了,我们还要不要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们揭示了一个事实——科技的进步不会取代人的求索之心。人类的历史,是符号(概念)及其代指对象两者之间分离与整合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符号逐渐外化于创造者的存在而在符号使用者的参与下获得越来越大的独立性,AI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新阶段。面对“人-符(符号)分离”的现实,我们更需要保持思想的清醒,厘清技术与人的边界,探索未来的可能。
而他的书房——这方名为“云雾斋”的天地,正如其名,在浮沉的云雾中,静守一片清明,为思想提供栖息之所,也为求索之路点亮微光。
白书农推荐书单
《历史研究》(英)阿诺德・汤因比
《全球通史》(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
《20世纪的生命科学史》(美)艾伦
《枪炮、病菌与钢铁》(美)贾雷德・戴蒙德
《Knowledge of Life》(法)Georges Canguilhem(乔治・冈圭朗)
《预测算法》(英)安迪・克拉克
《持续焦虑》(美)艾恺
《观念的跃升》(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学者简介
白书农,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荣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雄蕊早期形态建成调控机制和植物性别分化等。1990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991-199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1990-1998年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8-2021年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在Science、Plant Cell、PNAS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
曾主讲“植物发育生物学”“植物形态建成”等课程,获得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秀奖、北京大学优秀班主任、北京大学优秀德育奖等荣誉。目前在北京大学暑假学期开设《生命的逻辑》课程。出版书籍《十的九次方年的生命》《生命的逻辑》《植物发育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原理》等。
2020-2021年担任博古睿学者,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博古睿讲座系列”的首讲嘉宾,在线平台“睿的n次方”(现更名“萃嶺”)的首位专栏作者。

来源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
采写 |王梓寒
摄影 |曹梦瑶
排版 |王俊晔
责编 |曹梦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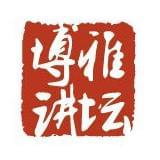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