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离转换性障碍(DID,Dissociative - Conversion Disorder),过去在民间也被称为“癔症”。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它和抑郁症时常一同出现,在临床表现上却有所不同,后者最常出现长期的情绪低落或兴趣丧失,前者则是将情绪低落作为分离或转换症状中的一部分,更多地会在“遗忘”“神游”“身份认知”或者是运动、感觉功能上出现障碍,例如身体木僵、抽搐,甚至是无器质性损伤的失明、耳聋。
✦ 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人数达110万。而世卫组织在2022年发布的《世界精神卫生报告》中谈到:“平均而言,各国用于精神卫生的预算不到其卫生保健预算的2%。在中等收入国家,70%以上的精神卫生支出仍然用于精神病医院。大约一半的世界人口所在国家每20万或以上人口才有一名精神科医生。”也就是说,即使近年来精神类疾病患者数量持续增加,精神卫生医疗的缺口仍然较大,许多患者虽然已面临(严重)精神问题的困扰,却无法获得较为良好的治疗,甚至许多患者难以分清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等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间存在哪些关联或区别。精神疾病教育普及和医疗资源保障同样面临较大挑战。
✦ 去年12月,演员赵露思因罹患分离转换性障碍频频登上热搜,开始使这种在公共讨论中并不常见(相比于抑郁症或焦虑症等)精神疾病受到关注,更多患有相同疾病的患者通过社交媒体透露了自己的病情进展和发病情况,也鼓励了很多可能尚未确诊的病友积极治疗。包括以上谈到的许多媒体的科普信息,也都因为赵露思的知名度而涌现出来。
✦这是件好事吗?当然。最起码让这类疾病成功拥有了话题度,有更多人愿意讨论它、了解它。福柯早就谈过,话语是有权力和力量的。如果想要一件事、一个人、一段历史消失,那便限制它、禁止它;如果想要让众人认可、尊重某个对象,那便推行它、解释它,为这段话语重新赋予意义。一位明星带来的流量与热度足以让一种原本潜藏在社会主流话语之下的疾病获得更多的关注,让相关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的媒体科普,也使其能因看到更多“同伴”而抛弃“疾病羞耻”。这就是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需要的意义:当我不再是异类,我便能重新获得身份认同,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去。
✦但为什么明明横看竖看都应该是件「好事」,最后却变成了一场针对赵露思的“群体嘲讽”?
✦ 我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围观了这出剧目的始末,与身边不同的人交谈,相互交换观点。 有嗤之以鼻的,有同情理解的,也有痛斥与避之唯恐不及的。理性的人说,营销号不能全信,有机会我们还是看看她的原话;感性的人讲,痛苦不是件那么容易自我消化的事。但大多数人,最后的结尾都落在那句:
✦ 但她其实可以不用这样的,生病了,就好好休息吧。
✦ 这么看来,我身边无论是理性的、感性的人,都是些心肠柔软的好人。
/⇠ 赵露思你好,
/⇠ 展信佳。
去年12月,听闻你生病的消息。请原谅,我从未看过任何一部你出演的影视剧,但我知道你,我的朋友常说,你的那部《传闻中的陈芊芊》演得很好,很有灵气。可我实在不爱古装剧,只能从几次或好或坏的热搜或是你漂亮的ins上零散地了解你几分。除此之外,便是你急诊住院的画面在无数条信息流里一闪而过。
和所有娱乐圈的八卦绯闻一样,你的生病对普通人来说隔着屏幕,远在千里,情绪跋山涉水而来,太过漫长。我也只当茶余饭后的闲聊谈资,偶然和朋友聊到,随后这些令你感到痛苦的疾病,可能使你倍感折磨的病症,便再没了踪影,甚至不比我窗前日日枯黄下去的桂圆树,桌角突然出现的不起眼的裂缝来得重要。
请不要责怪我将你的难捱与这些生活中的琐事相提并论。虽然社交媒体让几乎所有人变得可见,使许多人原本秘而不宣的生活更直接地曝光在镁光灯下:死亡、悲恸、欢喜、思念,情绪无一不赤裸,举止无一不为他人审视;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只是观看者,如同看台上抱臂旁观的观众,有时欢欣雀跃地鼓掌,有时昏昏欲睡,有时则怒目圆瞪,批判指责。我相信你比我更理解、更深知这些声音的摇摆不定,爱你时将你捧为星月,憎你时又如同吃人的魑魅,只靠那唾沫星子,便能使人溺毙。因为无论如何,无论你是谁,拥有怎样的鲜活血肉,对观众来说,台上站着的,都是那无关紧要的、不触及自身利益的陌生人,是已经被电子屏幕切割好的扁平化标签,是比那泥塑的庙堂菩萨还苍白几分、浅显几分的角色。
无人在乎你悲喜,无人识得你真心。在这种言难自明的痛苦上,明星看似与任何一个普通人无异。这倒是当下为数不多的公平之事。
“公平”,这是一个在围绕你的非议中经常出现的词汇。我翻阅了诸多社交媒体账号,他们总是说到这句话:“疾病会无差别地攻击每一个人。”这大概也是你试图分享病情,让更多的人看到心理的疾病与身体上的苦痛同样重要,而那些压在你身上的“努力”“期待”“向上”和“奋斗”,那些在职场中遭遇的不公与苛责、在“努力后却没有回报”时的低沉煎熬,似乎也是大部分与你同一年龄段的青年人正在经历的痛苦。或许站在你的角度,知名度能使你帮助到同样饱受精神疾病影响的人获得抱团取暖的慰藉,让深陷“优绩主义”中不断扑腾着向上的年轻人学会驻足于一场日落,享受午后静谧的乡村,夜晚夏日的蝉鸣。
回到“附近”。悬浮在现代社会,必须依靠持续不断地挥动翅膀才能让自己保持静止的蜂鸟们,应该学会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对伟大和成功祛魅。“舒服”,这是在你去到甘孜雅江县之后的第二天傍晚,你和与你同去的小朋友闹闹坐在炉火前反复说的一个词。于是我想,你大概也会赞成前面,我所说的那些话:感受生活,畅意自由。
作为一位观看者,也作为一位与你同龄的年轻人, 我冒昧地想,这大概也是在《小小的勇气》里,你想要表达的观点。
截图来自“芒果TV”《小小的勇气》第一期
我很想要认同你,感受那些镜头下,让你看起来熠熠生辉的阳光和清风,它们可能正在治愈你的痛苦、焦虑,让勇气重新回到你的身体。它们让你“舒服”。但我却难以真正地进入这些情境中去,因为春天来了,大部分的年轻人,却只能享受“公园20分钟”的漫步;因为鸡鸣寺的樱花开了,可被困在工位上的人们,直到它被突如其来的夜雨打落成脚步匆匆之下的一团泥泞,都没见过花朵在阳光下绽放的样子。
冬天的毛衣起了球,团团耸立,纠结成难看的模样;昨天来不及吹干的头发,脸上冒出的油光,递不出去的简历,手边来不及收拾的外卖盒。和你同一代的年轻人们,大多埋头于生计,用着那些琐碎的、辛苦的劳动换来的工资,挤在假期的人流里,低头是掰着指头算的银行存款,抬头是一条望不到头的未来。
我们很难再与你“同病相怜”。因为你看,大部分悬浮在这个世界上的蜂鸟,都必须努力地振翅,才能保持不动;而我们光是踉跄地站在时代的洪流中,便耗尽了大半的精力。
这是一个已经被“货币独裁”的社会,每一个机会和选择都被标好了价格。就连“疾病会无差别地攻击每一个人”,都还有下一句话:“但每个人能够接受的治疗和享受的资源是不同的。”
昨天我看了篇「真实故事企划」的文章《》:每20天一次化疗,讲述人说,周六化疗后,到周二是最难捱的日子,只要熬过去,慢慢都会好起来。
截图来自“真实故事企划”4月7日推文
詹青云问:“世界上到底有哪条路这么难走,要让我们把四季都错过?”你说,世界上有多少难走的路,硬生生逼得人,错过了一切。
但谁又敢放手,真正享受悠长假期?那些舒服的生活,或者只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样样件件,都要用存款担保,都要向那货币低下头来,用劳动和工作,换来片刻的休息。
截图来自《我的天才女友》
我们就是活在这样一个高度货币化、物化的时代,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资本量化的对象。所以请你体谅我们的“共情能力”在逐渐衰退,因为个人的背后,是一套又一套的规则体系,是一层又一层的金钱关系。我们无法脱离你的社会阶层和身份角色谈问题,也无法忽视你所拥有的,是站在湍流中的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资源。 每当我试图换位思考时,才惊觉自己其实从未感受过你的生活。共情是平等的对话和理解,但你却高高在上。总在仰视的时候,人是很难感同身受的。
你说,《小小的勇气》是你的一趟治愈之旅。或许你不想再把自己作为生活的客体,为了那些“向上的欲望”而忽略自我的诉求。或许你想要重新获得生命的主体性,在清晨收露时,在遇到路边的动物时,在与那些质朴的人交流时,再次感受真实的生命力量,那些蓬勃的,不断破土而出的力量。你拒绝再将自己当作是生活的手段,而是想要成为生活的目的。
这些词藻和镜头太美妙了,以至于一切都像是装在展示柜里的瓷娃娃,精致、漂亮,像是前几年那场盛大的谎言:
“逃离轨道,奔向旷野。”
我们逃了,奔了,跳下那列车才发现,除了媚俗刻奇的理想词藻、被制造出来的景观想象外,这出席卷社交媒体的“旷野谎言”里,只剩下中关村永远明亮的写字楼,只留下一个个站在拥挤地铁里,疲惫不堪的劳动者。
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大部分的人只能把自己活成生活的“手段”,原来那些“勇敢的人先看世界”,那些所谓的“旷野”,都需要入场的门票。
你看呀,在你的手中,是不是那些“小小的勇气”,也有一张明码标价的入场券。
洋洋洒洒地,我说了很多,对一个陌生人来讲,这些话有的尖锐,有的坦诚,但请你一定相信,它们没有半字出于指责或是厌恶。因为我知道,会受伤的人,肯定是因为她拥有会被伤害的,柔软的部分。社交媒体上的声音太多太杂,模糊了真实,也消解了初心。而这些声音,许多的因果关系,我也絮絮叨叨地说了多半:
出于你的身份、阶层,这趟治愈的旅程或许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精神疾病,让疾病的话语进入了公共讨论空间;但也是因为你的身份、阶层,使这趟旅途显得更像是纳西瑟斯的顾影自怜,是一场注定难以为更多人认同的自我展演,也让一次本应严重的精神疾病变成“小布尔乔亚”的矫饰,成为一种“精致的阶层生活”。而后者带来的舆论排斥和敌意、嘲讽,已不断削弱前者带来的意义和价值。
当然,这不是在否认你的痛苦,也无意消解疾病使你遭受的煎熬,更不会说出那套“世界上痛苦的人比比皆是,你的痛苦又当如何”。痛苦是真实存在的。当它是社会性的问题时,它可以是公共的痛点,为社会大多数的个体所共情,但当它是独属于某一阶层或群体的时候,它将不再被公众所接受,更适合自我感受,自我消化——没有能够得到多数人认同,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没有展示在众人面前的治愈之路,也不代表你从未踏足。
我想,也许那句“在社交媒体上,‘ 无人在乎你悲喜,无人识得你真心’”并不是公平的,于普通的我们来讲,能获得朋友支持,家人慰藉已不可多得,而你,还有很多很多喜欢你的人,与你同在。
这是何其幸运,而又弥足珍贵的事。
我好像说得太多了,几乎都要成了有那说教意味的老学究了。实在抱歉。可能是第二人称的关系,也可能是这封电子书信的原因,我发现自己好像不再与你是绝对的陌生人了,我既向你诉了衷肠,倾倒了真心,那便没有再站在观众席冷眼旁观的道理。
即使我与你的经历难以实现共情,但还是希望你理解,社会的规则已不仅是袒露真心,还要审时度势,有些伤口,只能自己舔舐。
希望你快乐。
写下这五个字的此时此刻,没有阶层、金钱、社会地位和资源背书,只是作为一个人,希望你快乐,希望我也快乐。
晚安。
◟✦✩‧₊˚
* ᴳᴼᴼᴰ ᴺᴵᴳᴴᵀ *
First thought Best thought
「去更大的世界 做更有趣的人」
值日生酒醒时间:9:00-2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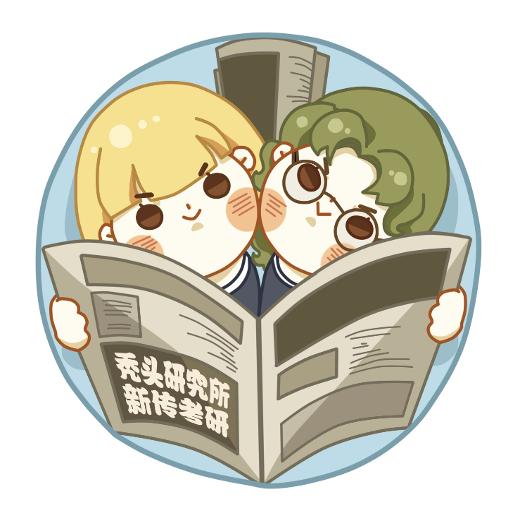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