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买湾一处不断被海水轻轻拍打的海角向着这座城市远眺,黄色的玄武岩拱门以其粗犷而巍峨的身姿出现在天际线上。一个斜坡状的水泥平台从拱门一直延伸到海边,海湾里的波浪很舒缓,几乎无法搅动平台周围那些浮在水面的绿色油泥。拱门投下的巨大阴影覆盖着一个奇特的世界:耍蛇人和算命师、乞丐和游客,蓬头垢面并且因药物作用而表情呆滞的嬉皮士,整个城市因为贫穷而变得奄奄一息。没有人会抬起头来去端详拱门上方那些清晰可见的题字:“为纪念帝国陛下英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于1911年12月2日驾临印度而建”。
然而,这座拱形的印度之门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胜利之门。对于好几代抛弃了在英国中部以及苏格兰山区的村庄而漂洋过海来到印度的英国人来说,他们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从船上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巨大的拱门。这些从拱门下鱼贯而过的人当中有士兵和冒险家、商人和官员,他们的到来是为确保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世界长盛不衰,是为对一个已经被征服的大陆进行攫取,是为承担起白种人自认为不可动摇的责任,那就是他们生来就是世界的统治者,他们的帝国注定将永远存在下去。
所有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早已遥不可及。如今,这座距今半个世纪的印度之门只是又一堆石头而已,与尼尼微城和提尔城被人遗忘的纪念碑别无二致。
钟声响起,是灾难还是解放?
尼赫鲁
印度第一任首相
1947年8月15日的午夜,印度独立。国会大厅通宵灯火通明,成为第一任首相的尼赫鲁在国会宣布印度独立并发表演说:“在很久以前我们曾经和命运有过约定,现在履行誓言的时刻已经到来,虽然说并不完全但却是非常实质的。当午夜钟声响起全世界都还在沉睡的时候,印度将苏醒并迎接生命与自由。”
但就在几百公里外的边境线,无数家庭正在仓皇出逃。英属印度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随即爆发的是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大规模强迫迁徙和宗教暴力: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在铁轨上、路途中、村庄中遭遇屠杀、强奸、掠夺。仅在最初数月,便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于非命,超过一千四百万人流离失所。
这一夜,在德里,政要们谈的是命运与民主;在旁遮普,平民却陷入最原始的求生本能。这不是宏大叙事中常见的“自由的欢呼”,而是无数个“身份即原罪”的沉默挣扎。
自由的味道
没有人想到数百万人在瞬息之间会做出迁移和投奔另一方的举动。
在地图上,这不过是多了一道红线。但在土地上,它撕裂了千年交融的村庄、家庭与日常。边界划线仓促、民众通知不及、管理机制瘫痪,最终引发了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为人口迁徙,短短几个月间,约千万人被迫迁徙,是当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人口流动。火车、牛车、滑板车,甚至赤脚徒步,百万人在烈日与暴力中穿越边界。仅在旁遮普,就有高达500万人行进在灼热田野与尘土公路上,穆斯林向西迁往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向东进入印度。许多迁徙者是农民、妇女、老人与婴儿。他们甚至不知道“分治”为何物,只知道“今天必须走”,否则就会死。
西里尔·拉德克里夫爵士(中)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国法学家,在旁遮普和孟加拉地区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划界的艰巨任务就是由他完成的。(来自作者收藏)
“一个人睡在印度,醒来就成了巴基斯坦人。”边界线荒谬至极。一间房屋的前门开在印度,后窗属巴基斯坦。一条运河头归印度,尾归巴国。红线之下,是无数人的归属错乱、身份重组与生死一线。
一位商人告诉在得知边界划定后48小时内,烧毁了所有账本与库存记录,只为迅速动身。
一个记者回忆,一位老人将孙子硬塞进他的吉普车里,哀求道:“请至少让他活着到印度。”还有出生几小时的婴儿,被母亲抱着从车上下来,踏上了漫长的跋涉。
有人撕下学生本的纸,上面写着他在巴基斯坦失去的一切:牛、床、锅碗瓢盆。他执拗天真地说要拿去找“我的政府”。当记者问:“哪个政府?”他茫然地回答:“你能告诉我去哪里找我的政府吗?”
印度为自由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蒙巴顿夫妇在旁遮普总督埃文·詹金斯爵士的陪同下视察在第一波暴力狂潮中遭到毁灭的村庄废墟。(布罗德兰兹档案馆提供)
而在另一个难民营里,一个年轻人守着奄奄一息的母亲,不是为了告别,而是为了在她死后能顺利继承那条盖在她身上的毛毯。
这场迁徙与“和平”无关,而是伴随着系统性暴力。1947年9月,一列从拉合尔开往德里的火车,在途中被拦截,全车乘客被杀。这不是个案,而是当时边界沿线多地的常态。有女性在火车上集体被剥夺衣物以示“清洗”,男童被遗弃在路边,整车尸体运抵车站。整列难民火车被屠杀的事件不止一起。女人被掳走,男人被砍死,尸体挂在铁轨两侧,铁锈混着血味。在精神病院,印度教与锡克教病人请求转移至印度,遭拒。几日后,他们集体死亡。
有的人逃出来,还带着五十万卢比。他哭着说:“我要把每一分钱都用来杀掉尼赫鲁和甘地。”
有的人什么也没剩,只想找到走失的母亲、女儿、丈夫,哪怕只剩尸骨。
自由呈现出三种不同形态
作为幻象:
独立并不等于获得真正的社会公正。帝国留下的并不是真空,而是复杂的社会断层和结构性问题——种姓制度、宗教冲突、区域分裂。这些问题在英属印度时期被以强权手段“管理”,而独立后反而在真空中爆发出来。自由没有解放旧制度,反而释放了其深层暴力。
作为伤痕:
独立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失所者的流亡、难民营的扩张、边界暴力的反复上演。自由成了一道新旧秩序之间的裂缝,民众在废墟上重新拼凑生活。“分治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开始。”
作为过程:
自由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午夜钟点”,而是一个不断被重塑、检验、挑战的过程。即便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已经转移,但真正的“平等权利、公民参与、社会安全”仍遥不可及,尤其对于边缘群体而言。这种自由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一场漫长的未完成工程。
“独立”并不等于完全“去帝国化”。殖民时期的许多制度与观念不仅存续至今,甚至成为新国家治理的基础工具。
制度与语言:
司法体系、税收结构、英语行政语境,这些英属印度时期的遗产,并未随着殖民者离去而废止,反而被接续沿用。
宗教与种姓标签:
英国人为管理复杂的印度社会,引入了大量“身份归类”手段,如宗教人口普查、种姓文书、行政边界划分。这些在独立后并未消除,反而成为选举政治与民族主义的重要动员资源。
城市与阶层结构:
殖民规划下的城市空间,形成了“欧洲人区—原住民区”的等级化布局。独立之后,这一空间逻辑未被颠覆,而是被以新的阶层结构所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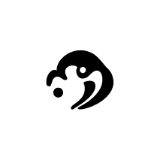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