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早已习惯被欺负。他出生在禁酒令时期的底特律,家境艰难,父亲是名锅炉工,事不顺心就会挥拳相向。邻里的男孩们也好不到哪里去。1935年的一个下午,他们追得皮茨在街头四处逃窜,直到匆忙闯进当地的图书馆,才算逃出生天。
这间图书馆对皮茨而言再熟悉不过了,他在这里自学了希腊语、拉丁语、逻辑学和数学——相比那个执意要他辍学去做工的父亲,这里似乎更像是他的家。馆外的世界混乱不堪,馆内却井然有序、一切都有理可循。
为了避免当晚再遭遇纠缠,皮茨得躲到图书馆闭馆再出去。独自徘徊在书架间,他邂逅了《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这套厚重的三卷本出自两位数学巨匠之手——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与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他们在1910至1913年间倾力合著,试图将所有数学知识简化为纯粹的逻辑。
皮茨坐下来开始阅读,接下来的三天里,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图书馆,不仅逐页通读了全套近2000页的内容,还找出了其中几处错误。这个男孩认定,罗素本人应当知晓这些问题,于是他便写信给罗素详细指出了这些错误。而罗素不仅回了信,还对这个男孩印象极深,甚至邀请他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以研究生的身份师从自己。但皮茨无法应允——那时他只有12岁。不过三年后,15岁的皮茨得知罗素将到访芝加哥大学,便离家出走,前往伊利诺伊州。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家人。

▷沃尔特·皮茨(1923-1969):沃尔特·皮茨的一生从无家可归的离家出走者,到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先驱,最后沦为一名孤僻的酒鬼。
1923年,也就是皮茨出生的这一年,25岁的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也在研读《数学原理》。但两人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麦卡洛克的出身背景与皮茨截然不同。他生于东海岸的富裕家庭,家人多从事律师、医生、神学家与工程师等职业。麦卡洛克先是就读于新泽西州的一所私立男校,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弗福德学院学习数学,又在耶鲁大学攻读哲学与心理学。
1923年,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实验美学”,且即将获得神经生理学专业的医学学位。但麦卡洛克本质上是一位哲学家,他想弄明白“认知”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时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刚刚问世,精神分析学说正风靡一时,但麦卡洛克却不为之所动——他坚信,心智那些神秘的运作机制与功能缺陷,必然以某种方式根植于大脑神经元纯粹的机械放电。
尽管麦卡洛克与皮茨的社会经济地位天差地别,但他们注定要相遇、共事,直至相继离世。在此过程中,他们创造了首个心智机械论、首个神经科学计算方法,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逻辑设计基础,也为人工智能搭建了核心支柱。但这个故事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段富有成果的研究合作,它还关乎友谊的羁绊、心智的脆弱,以及逻辑在拯救混乱而不完美的世界时所存在的局限。

跨域相逢与神经建模:
麦卡洛克与皮茨的逻辑共鸣
麦卡洛克与皮茨,即使相向而立,也仿若来自不同的世界。
与皮茨相识时,麦卡洛克已42岁,他自信满满,灰眸深邃,络腮胡肆意生长,常年烟不离手,身上兼具哲学家的睿智与诗人的浪漫,日常靠威士忌和冰淇淋度日,从不在凌晨4点前入睡。而18岁的皮茨身材瘦小、性格腼腆,额头偏长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戴着眼镜的脸庞矮胖,模样有些像鸭子。麦卡洛克已是受人尊敬的科学家,皮茨却只是个无家可归的逃家少年。
那时的皮茨一直在芝加哥大学附近徘徊:打些零工糊口,偷偷溜去听罗素的课。就是在这些课上,他认识了年轻的医学生杰罗姆・莱文(Jerome Lettvin),在他的引荐下,皮茨才得以与麦卡洛克相识。
两人一经交谈,竟发现彼此心中都崇拜着同一个偶像——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这位17世纪的哲学家曾试图创造一套“人类思维字母表”:每个字母代表一个具体概念,可依据一套逻辑规则组合推演,最终计算出所有知识。这一构想的核心,是要将那个混乱不完美的外界世界,转变为像图书馆般理性有序的庇护所。
麦卡洛克告诉皮茨,他正在尝试用“莱布尼茨式逻辑演算”为大脑建模。他的灵感源自《数学原理》:在这套著作中,罗素与怀特海试图证明,所有数学知识都能从最基础、无争议的逻辑出发,一步步构建起来。罗素和怀特海构建理论的“基石”是“命题”——即最简单的陈述,非真即假。在此基础上,他们运用逻辑的基本运算,如合取“且”、析取“或”、否定“非”,将单个简单命题连接成越来越复杂的逻辑网络,最终推导出了现代数学的全部复杂体系。

▷《数学原理》
这一思路启发了麦卡洛克开始思考神经元的运作机制。他知道,大脑中的每个神经细胞,只有在达到某个最低阈值后才会放电:必须有足够多的相邻神经细胞通过突触向它传递信号,它才会释放出自身的电脉冲。麦卡洛克突然意识到,神经元的这种运作机制是“二元”的,要么放电,要么不放电——这意味着,神经元信号本质上就是一个“命题”,而神经元的工作模式与“逻辑门”极为相似:接收多个输入信号,最终输出一个信号。通过调整神经元的放电阈值,就能让它实现“且”、“或”、“非”的逻辑功能。
到了深夜,就只剩麦卡洛克与皮茨两人:他们倒上威士忌,潜心投入,试图从神经元层面起步,构建出一个具备计算功能的“大脑”。
恰好此前,麦卡洛克读到了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的一篇新论文,文中证明了“通用计算机”的可能性:只要某个函数能通过有限步骤完成计算,就存在一台机器可以实现该计算。这篇论文让麦卡洛克进一步确信,大脑正是这样一台机器——它通过编码在神经网络中的逻辑来完成计算。在他看来,神经元可依据逻辑规则连接起来,构建出更复杂的“思维链”;这与《数学原理》中通过连接“命题链”构建复杂数学体系的思路如出一辙。
当麦卡洛克向皮茨阐述这个研究构想时,皮茨不仅瞬间理解了他的研究方向,甚至能精准指出需要运用哪些数学工具。麦卡洛克被这个少年的天赋深深震撼,当即邀请这个少年搬去自己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小镇欣斯代尔(Hinsdale)的家中同住。
麦卡洛克的住所是个“波西米亚式”居所——热闹非凡、自由气息浓郁。芝加哥的知识分子与文学名流常登门造访,伴着留声机里播放着的西班牙内战歌曲与工会歌曲的激昂旋律,围坐畅谈诗歌、心理学与政治议题。而到了深夜,当麦卡洛克的妻子鲁克和三个孩子入睡后,喧闹散去后,客厅里只剩麦卡洛克与皮茨两人。他们斟满威士忌,潜心投入于他们的研究,试图从神经元层面起步,构建出一个具备计算功能的“大脑”。
在遇到皮茨之前,麦卡洛克一直被一个棘手问题困扰:神经元链会无可避免地形成闭环——链末的神经元的输出信号,成为起始神经元的输入,整个神经网络首尾循环。对于这种情况,麦卡洛克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建立数学建模。这种循环看似构成了一个逻辑“悖论”:结果变成了前提,结果变成了原因。麦卡洛克原本采用时间戳标记法,比如第一个神经元在t时刻放电,下一个就在t+1时刻放电,以此类推。可一旦神经元链形成回路,t+1就会突然出现在t之前,整个时间逻辑体系彻底崩塌。
皮茨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模运算”——让数字像时钟刻度一样,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他向麦卡洛克证明,“t+1出现在t之前”根本不是悖论:在模运算体系中,“先后”这一时间概念本身就不复存在,时间被彻底从方程中剔除了。
举个例子:当人眼捕捉到天空中的一道闪电,视觉信号会从眼睛传入大脑,在神经元链中逐级传递。此时,只要从链中任意一个神经元出发,追溯信号的传递路径,就能算出闪电发生在多久之前。但在闭环系统中,规则完全改变了。编码闪电信息的信号会无休止地在回路中循环,而完全脱离了与闪电的实际发生时刻。用麦卡洛克的话说,它变成了“脱离时间的想法”——“记忆”。
皮茨的计算模型让他们的心智机械论模型终于成型,这将计算方法首次引入大脑研究中,并率先提出“大脑本质是信息处理器”的理念。他们通过将简单的二元神经元连接成链与回路证明了,大脑能够执行所有可能的逻辑运算,且能处理图灵设想的通用计算机所能解决的任何计算问题。
不仅如此,得益于这些衔尾蛇式的回路,他们还发现了大脑处理信息的关键机制:先抽象出一段信息并将其保留,再对其进行二次抽象,最终在我们称之为“思考”的过程中,构建出丰富而复杂的持续性概念层级。
后来,麦卡洛克与皮茨将这些突破性发现整理成论文《神经活动中内在思想的逻辑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发表于《数学生物物理学通报》(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这篇论文如今已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尽管相对真实的生物大脑,这个模型显然过于简化,但这并不妨碍其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原理验证。他们证明:思想无需笼罩在弗洛伊德式的神秘主义之下,也不必归因于“自我”与“本我”的斗争。甚至,麦卡洛克曾对着一群哲学系学生自豪地宣称:“纵观科学史,我们首次真正理解了‘我们如何认知’。”

▷ 作者:Julia Brekenreid

伯乐识才与学术崛起:
皮茨在控制论与计算机领域的突破
皮茨在麦卡洛克身上找到了自己渴求已久的一切——认可、友谊、学术上的知己,以及从未拥有过的父爱。尽管只是在欣斯代尔住了短短一段时间,但从此以后,这位流浪少年始终将麦卡洛克的家称作“家”。而麦卡洛克对皮茨同样满怀欣赏。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灵魂、他的“地下合作伙伴”,以及一个能将他那些尚不成熟的想法变为现实的实力派“智囊”。正如他在为皮茨的推荐信中写道:“我多希望他能一直留在我身边。”[1]
不久后,皮茨也给20世纪一位顶尖学者留下了相似的深刻印象。这个人便是数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控制论创始人的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43年,莱文带皮茨来到了维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维纳既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寒暄,只是直接带皮茨走到一块黑板前,上面是他正在推导的数学证明。
在维纳演算的过程中,皮茨不时提出问题、给出建议。据莱文回忆,当他们转战到第二块黑板前时,很明显,维纳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新得力助手。后来维纳曾这样评价皮茨:“毫无疑问,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如果他最终没有成为他那一代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我会感到极度惊讶——不仅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也同样如此。”
维纳对皮茨的欣赏如此之深,甚至承诺为他争取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学位,尽管皮茨连高中都没毕业,这种破格录取在芝加哥大学的严格规定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面对如此难得的机会,皮茨无法拒绝。1943年秋天,他搬进了剑桥市的一间公寓,以特殊学生的身份进入麻省理工就读,师从这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与他出身的底特律蓝领阶层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维纳希望皮茨能进一步完善他与麦卡洛克提出的大脑模型,使其更贴合现实。尽管皮茨与麦卡洛克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他们的成果在脑科学家群体中却反响寥寥——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使用的符号逻辑难以理解,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们的模型过于简化,无法充分体现生物大脑的复杂全貌。而维纳深知这项研究的潜力,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更贴近现实的大脑模型将具有划时代意义。
维纳还意识到,皮茨提出的神经网络应能在人造机器中实现,而这将推动他所憧憬的控制论革命成为现实。维纳认为,若要构建一个能模拟大脑千亿个相互连接神经元的真实模型,就离不开统计学的支持。而统计学与概率论正是维纳的专业领域。毕竟,正是维纳提出了信息的精确数学定义:事件概率越高,熵值就越高,信息含量则越低。
在场的科学家们都大为震惊。但所有认识皮茨的人都坚信,他一定能做到。
皮茨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展研究后逐渐意识到:尽管基因必定会编码大脑的宏观神经特征,但人类基因绝无可能预先决定大脑中数万亿个突触连接——要实现这一点所需的信息量,根本难以实现。他由此推测,我们每个人刚出生时,大脑本质上都是随机的神经网络,高概率状态所包含的信息量极低(这一观点至今仍存在争议);随着时间推移,通过调整神经元的放电阈值,随机性或许会让位于有序结构,信息也会随之产生。于是,他着手用统计力学为这一过程建立模型。维纳对此满怀期待,全力支持他。因为维纳清楚,若这样的模型能在机器中实现,那台机器便能具备学习能力。
“如今维纳说的话,我一下子就能理解七分之六——别人告诉我,这已经算得上是一项成就了。”1943年12月,也就是抵达麻省理工约三个月后,皮茨在给麦卡洛克的信中这样写道。他与维纳合作的研究将成为“首个充分探讨统计力学的研究,这里的统计力学采用最广义的定义,所涵盖的问题包括从神经生理学的微观规律推导出心理学或行为学的统计规律……听起来是不是很棒?”
那年冬天,维纳带皮茨参加了一场他与数学家、物理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在普林斯顿共同组织的会议,冯・诺依曼也同样被皮茨的才智深深打动。于是,一个后来被称作“控制论学者”的团体就此萌芽,其核心成员包括维纳、皮茨、麦卡洛克、莱文与冯・诺依曼。
在这个精英云集的团体中,这位曾无家可归的逃家少年依旧格外耀眼。“没有他的修改和认可,我们谁都不会考虑发表论文。”麦卡洛克这样写道。莱文则评价道:“毫无疑问,他(皮茨)是我们团队里的天才。在化学、物理学,乃至历史、植物学等所有你能想到的领域,他的学识都极为渊博。你问他一个问题,他能给你讲出一整本教科书的内容……世界在他眼中是以一种极为复杂且奇妙的方式相互关联的。”[2]

▷冯・诺依曼的《EDVAC报告初稿》. 图源:Amazon
1945年6月,冯・诺依曼撰写了一份后来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EDVAC报告初稿》(First Draft of a Report on the EDVAC)。这篇文献首次公开描述了“二进制存储程式计算机”,也就是现代计算机。
EDVAC(电子离散变量自动计算机)的前身是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费城的一台ENIAC占地1800平方英尺,与其说它是计算机,不如说更像是一台巨型电子计算器。可以对ENIAC进行重新编程,但却需要几名操作员花上几周时间,重新连接所有线路和开关才能完成。
冯・诺依曼意识到,若想让机器执行新功能,或许不必每次都重新布线:如果能将开关与线路的每种配置抽象出来,以符号形式编码为纯粹的信息,就能像输入数据一样将这些信息输入计算机。只不过此时的“数据”,还包含了操纵数据的程序本身。如此一来,无需进行任何重新布线,就能得到一台通用图灵机。
为实现这一目标,冯・诺依曼提出以皮茨和麦卡洛克的神经网络为蓝本设计计算机。他建议用真空管替代神经元,这些真空管将充当逻辑门;只需完全按照皮茨和麦卡洛克发现的方法将真空管连接起来,就能完成任何计算。而要将程序作为数据存储,计算机还需要一个全新的部件:存储器。这正是皮茨提出的“回路”派上用场的地方。
“一个能自我刺激的元件,会无限期保持刺激状态,”冯・诺依曼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既呼应了皮茨的观点,也运用了他的模运算方法。”他详细阐述了这种新型计算架构的各个方面,而在整篇报告中,他仅引用了一篇论文,那就是麦卡洛克与皮茨的《神经活动中内在思想的逻辑演算》。

▷麦卡洛克(左)与皮茨(右)合著的《神经活动中内在思想的逻辑演算》
1946年,皮茨搬至波士顿比肯街,同住的除了老友莱文,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奥利弗・塞尔弗里奇(Oliver Selfridge,日后被誉为“机器感知之父”)、未来的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当时的皮茨不仅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数理逻辑,还与维纳合作研究大脑的统计力学。次年,在第二届控制论会议上,皮茨宣布自己正在撰写关于“概率性三维神经网络”的博士论文。在场的科学家们都大为震惊。用“雄心勃勃”一词,远远不足以形容完成这一壮举所需的数学功底。但所有认识皮茨的人都坚信,他一定能做到。众人都屏息以待。
麦卡洛克曾在给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信中,细数了皮茨的成就:“他是涉猎最广的科学家与学者。他既是出色的染料化学家、优秀的哺乳动物学家,还熟悉新英格兰地区的莎草、蘑菇与鸟类。他可直接阅读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德语的原始文献,来研究神经解剖学与神经生理学——无论需要哪种语言,他都能迅速掌握。至于电路理论以及供电、照明、无线电电路等实际焊接操作,他也能亲自完成。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博学且真正具备实践能力的人。”
这也引起了媒体的瞩目。1954年6月,《财富》杂志评选40岁以下最具天赋的20位科学家,皮茨与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一同入选。尽管命运多舛,沃尔特・皮茨还是一跃成为了科学界的明星。

重逢变故与认知崩塌:
皮茨的自我毁灭之路

▷皮茨(右)、杰罗姆·莱特文(左)和他们视觉感知实验的对象(青蛙)(1959年)。
几年前,皮茨在给麦卡洛克的信中曾写道:“如今几乎每周,我都会无比思念能和你彻夜长谈的时光。”尽管事业有成,皮茨却愈发思念“家”——对他而言,“家”就是麦卡洛克。他渐渐坚信,若能再次与麦卡洛克共事,自己会更快乐、更高效,也更有可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而没有这位“地下合作伙伴”在身边,麦卡洛克似乎也陷入了困境。
转机突然降临。1952年,麻省理工学院电子研究实验室副主任杰里・威斯纳(Jerry Wiesner)邀请麦卡洛克前往麻省理工,主持一个全新的脑科学项目。麦卡洛克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只为能再次与皮茨共事。他放弃了正教授职位和欣斯代尔的宽敞住所,换来麻省理工研究助理的头衔和剑桥市的一间简陋公寓,即便如此,他却依然无比开心。
这一项目计划运用信息论、神经生理学、统计力学和计算机等全套研究手段,探索大脑如何产生心智。麦卡洛克、皮茨在瓦萨街20号组建了新办公室,共事的还有莱文与神经科学家帕特里克・沃尔(Patrick Wall)。他们在门上贴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实验认识论”(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如今皮茨与麦卡洛克重逢,维纳、莱文也在其中,一切似乎都为取得突破、掀起变革做好了准备。神经科学、控制论、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这些领域都即将迎来一场知识爆炸。天空(或是心智),就是他们的极限。
此后,皮茨开始酗酒,渐渐疏远了朋友,还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连同所有笔记与研究手稿也一并焚毁。
然而,这场重逢中,有一个人始终不悦,那就是维纳的妻子玛格丽特・维纳(Margaret Wiener)。众所周知,她控制欲强、思想保守且拘谨古板,尤其反感麦卡洛克对丈夫的影响。麦卡洛克常在自己康涅狄格州老莱姆镇的家庭农场举办热闹的聚会,那里思想自由交流,大家还会一起裸泳。麦卡洛克以前在芝加哥,这种事玛格丽特还能眼不见心不烦,但如今他要来剑桥,她绝不能容忍。
于是,玛格丽特编造了一个谎言。她跟维纳谎称,他们的女儿芭芭拉之前在麦卡洛克芝加哥的家中借住时,被“他那群年轻伙伴”引诱了。维纳立刻给威斯纳发了一封怒气冲冲的电报:“请告知(皮茨与莱文),我将永久终止所有与你们的合作项目。此后他们归你管了,维纳。”从此,他再也没有和皮茨说过话,也从未向皮茨解释过原因。[3]
对皮茨而言,这成了他人生衰败的开端。维纳曾是他生命中的父亲般的存在,却如此毫无预兆地抛弃了他。这对皮茨而言远比简单的失去更可怕,一切毫无逻辑。
另一边,麻省理工20号楼的地下室里,就在一只装满蟋蟀的垃圾桶旁,莱文养了一群青蛙。当时生物学家普遍认为,眼睛就像一块相片底片,会被动记录光点,再将这些光点逐点传递给大脑,由大脑承担解读信息的主要工作。莱文决定验证这一观点:他切开青蛙的颅骨,将电极连接到它们视神经的单根纤维上。

▷亨贝托・马图拉纳的《青蛙的眼睛告诉青蛙的大脑什么》 图源:swarajyamag
莱文与皮茨、麦卡洛克,以及智利生物学家兼哲学家亨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开展合作。他们给青蛙施加各种视觉刺激,如调节光线的明暗、展示自然栖息地的彩色照片、用磁铁吊着假苍蝇,然后记录下青蛙眼睛在向大脑传递信息之前,对这些刺激的“感知”。结果令所有人震惊:眼睛不仅会记录所见景象,还会就对比度、曲率、运动等视觉特征信息进行过滤和分析。
1959年,他们在《青蛙的眼睛告诉青蛙的大脑什么》(What the Frog’s Eye Tells the Frog’s Brain)一文中报告了这一发现,如今这篇论文已成为该领域的开创性文献。文中写道:“眼睛以一种高度组织化、经过编码的‘语言’与大脑交流。”
这一结果彻底颠覆了皮茨的世界观。在他此前的认知中,大脑会借助严谨的数理逻辑工具,以数字方式逐个神经元地处理信息;但事实却是,眼睛中混乱的模拟过程承担了至少部分解读工作。莱文回忆道:“我们完成青蛙眼睛的研究后,他很清楚,即便逻辑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其重要性和核心地位也远非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这让他很失望。他从未承认过这一点,但这似乎让已失去维纳的友谊的他更加绝望。”
一旦万物都被简化为受逻辑支配的信息,其实际运作机制便不再重要——而实现通用计算的代价,便是对“本体论”的牺牲。
接连的坏消息,让皮茨长期以来的抑郁倾向愈发严重。“我有件个人烦恼,想听听你的建议。”皮茨曾在一封给麦卡洛克的信中写道,“过去两三年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陷入一种忧郁的冷漠,或是说抑郁状态。这种状态带来的影响是,让世界中的积极意义似乎都消失了,以至于没有任何事看起来值得费力去做,无论我做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什么,都变得无关紧要……”
换句话说,皮茨正被他毕生所追寻的“逻辑”本身所困扰。他在信中写道,“这种抑郁或许“在所有接受过极度逻辑化教育、从事应用数学工作的人身上都普遍存在:这是一种悲观情绪,源于无法相信人们所说的‘归纳原理’,或是‘自然齐一性’。既然我们无法先验地证明太阳明天会升起(甚至无法先验地确定其可能性),那我们就无法确信它会升起。”
与维纳疏远后,皮茨的绝望开始危及生命。他开始酗酒,渐渐疏远朋友。当学校为他颁发博士学位时,他拒绝签署相关文件,还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连同所有笔记与研究手稿。多年的心血——那项学界众人翘首以盼的重要研究成果——被他付之一炬,珍贵的研究资料最终化为熵与灰烬。威斯纳甚至提出,若莱文能找回论文的任何片段,就为实验室提供更多资助,但一切都已化为乌有。
皮茨仍保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但这不过是名义上的安排。他几乎不与任何人交流,还时常无故失踪。“我们每晚都要出去找他,”莱文回忆说,“眼睁睁看着他自我毁灭,简直是一种折磨。”从某种意义上说,皮茨始终还是那个12岁的孩子——依旧带着被殴打留下的创伤,依旧像个逃家的少年,依旧在躲避这个世界。只是当年那间能庇护他的发霉图书馆,如今换成了酒瓶的模样。

学术遗产与生命终章:
皮茨与麦卡洛克的未尽之路
皮茨同麦卡洛克一起,为控制论和人工智能奠定了基础。他们将精神病学从弗洛伊德式分析中抽离,引向对思维的机械论式理解。他们证明了大脑具备计算能力,而心理活动本质就是信息处理。在此过程中,他们还揭示了机器的计算原理,为现代计算机的架构设计提供了关键灵感。
得益于他们的研究,历史上曾短暂地存在这样一个时期:神经科学、精神病学、计算机科学、数理逻辑与人工智能融为一体,让莱布尼茨的最初构想“人类、机器、数字与心智,均以信息作为通用媒介”得以延续。金属块、灰质团块(大脑)、纸上的墨迹(文字信息),这些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世间事物,本质上均可相互转化。
然而,隐患随之而来:这种符号化抽象虽让世界变得清晰可解,却让大脑本身愈发晦涩难明。一旦万物都被简化为受逻辑支配的信息,其实际运作机制便不再重要——实现通用计算的代价,便是对“本体论”的牺牲。
冯・诺依曼是首个察觉到这一问题的人。在给维纳的信中,他表达了这份担忧并预见了人工智能与神经科学日后终将分道扬镳。他写道:
“在图灵、皮茨与麦卡洛克的重大积极贡献被吸收理解后,情况并没有变好,反而比以往更糟。诚然,这些研究者以绝对且无可辩驳的普遍性证明了,任何事物都能通过合适的机制(尤其是神经机制)实现——甚至某一种特定机制能具备‘通用性’。但反过来说,若不开展‘微观’细胞学研究,我们对有机体功能的所有认知与探索,都无法为神经机制的进一步细节提供任何线索。”
这种通用性,让皮茨始终无法提出一个实用的大脑模型,他的研究因此被摒弃,几乎被大脑研究领域遗忘。更重要的是,青蛙实验已然揭示了纯粹以大脑为核心的逻辑思维观的根本缺陷:大自然选择了生命的混沌与复杂,而非逻辑的秩序与精确。而这一真相,皮茨或许始终无法理解。
他更无从知晓,尽管自己关于生物大脑的构想未取得成效,这些想法却推动了数字计算时代的到来,催生了机器学习的神经网络方法,以及所谓的心智联结主义哲学。在他自己看来,他早已一败涂地。
1969年4月21日(周六),波士顿贝丝・以色列医院的病房里,皮茨因酗酒而震颤性谵妄,他双手颤抖地给麦卡洛克写下了一封信。彼时麦卡洛克也正在困于彼得・本特・布里格姆医院的心脏重症监护病房。“听闻你轻度冠心病发作……现在身上连了许多传感器,接着护士持续监测的面板和警报器,连翻身都做不到。毫无疑问,这很有控制论的意味。但这一切都让我无比难过。”而当时皮茨已住院三周,入院原因是肝脏问题与黄疸。
1969年5月14日,沃尔特・皮茨在剑桥的一间寄宿公寓里孤独离世,死于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一种肝硬化的并发症。四个月后,麦卡洛克也与世长辞。失去彼此,对他们而言或许才是最大的悖论。那个延续了二十六年的回路,就这样断了。无声,却有回响。

▷1949年,麦卡洛克(右)与皮茨(左)图源:semanticscholar.org

编译后记
编译沃尔特・皮茨的故事时,最直观的感受是其学术贡献与人生轨迹的强烈反差:他以逻辑为核心,为控制论、人工智能及现代计算机架构奠定基础,却因人际变故与认知冲击陷入困境,甚至焚毁手稿。
编译中,我重点梳理了神经逻辑模型、控制论发展等复杂概念,以及皮茨与麦卡洛克、维纳的关系脉络,力求平衡专业性与可读性。仍有疑问:若他的博士论文留存,是否会为神经科学带来更多突破?深入了解可参考《信息时代的隐秘英雄》与麦卡洛克《心灵的化身》,以补充更多背景细节。
原作链接:
https://nautil.us/the-man-who-tried-to-redeem-the-world-with-logic-235253/

1. All letters retrieved from the McCulloch Papers, BM139, Series I: Correspondence 1931–1968, Folder “Pitts, Walter.”
2. All Jerome Lettvin quotes taken from: Anderson, J.A. & Rosenfield, E. Talking Nets: An Oral History of Neural Networks MIT Press (2000).
3. Conway F. & Siegelman J. Dark Hero of the Information Age: In Search of Norbert Wiener, the Father of Cybernetics Basic Books, New York, NY (2006).








关于追问nextquestion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旗下科学媒体,旨在以科学追问为纽带,深入探究AI与人类智能相互融合与促进,不断探索科学的边界。欢迎评论区留言,或后台留言“社群”即可加入社群与我们互动。您也可以在后台提问,我们将基于追问知识库为你做出智能回复哦~
关于天桥脑科学研究院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是由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出资10亿美元创建的世界最大私人脑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围绕全球化、跨学科和青年科学家三大重点,支持脑科学研究,造福人类。
Chen Institute与华山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设立了应用神经技术前沿实验室、AI与精神健康前沿实验室;与加州理工学院合作成立了加州理工天桥神经科学研究院。
Chen Institute建成了支持脑科学和AI领域研究的生态系统,项目遍布欧美、亚洲和大洋洲,包括、、、科研型临床医生奖励计划、、、大圆镜科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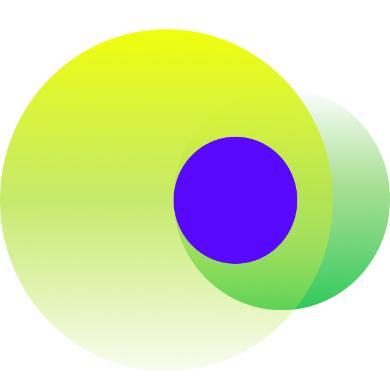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