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廊的内部或远景
1
江南小镇。闷热就像乌托邦。
电扇吹得所有人的骨头飘起来,
但谁也不许散架。小石桥上,
游客三两,点戳风景,其中一个
是从北方畏罪潜逃的税务官。
2
我也是一个有好几种化名的人,
正憋住暴笑,筷子伸向醉虾。
空气之空被旋搅得残破不堪。
老板的第六十四副面具开口了,
说的仍是一个哑谜:“干净,
我是它的奴隶,因为它是明摆着的,
因为它也是无止境的,
你得时刻跟在它后面收拾。”
一个女人插嘴说:“我们老板
人好。一次我从楼上望去,
看见他醉了,跪在马路中央,
他挽着袖子要把斑马线卷回家来。”
3
我睡在凉席上却醒在假石山边。
蝴蝶携着未来,却重复明代的
某一天。这一天,你只要觉得
浑身不适,你就知道未来已来临,
你只要觉得孤独,你就该知道
一切全错了,而且已无法更改。
无风之际只有风突然逆着流水
站起身来,像一个怒者,向前扑着,
撕着纸,当你的真名
如鸣蝉的急救车狂奔而来。
张枣去世后,杨炼无意中发现这首张枣作于1999年的诗歌,未收入诗集和在国内发表。张枣遗作由颜炼军提供。

厚积
在这座十多层的黑色高楼底下有一间地下室,门上封满了尘埃。我终于有一天下决心去问管理员借来了钥匙。进去,我多年前某次失败的气味扑面而来。那里面的东西东倒西歪,雕塑般再现出各类搁置者在暗处置放事物时的马虎心态:一摞盘子,轮胎,大半把小提琴,破椅子,纸牌,衣架,灯罩,雨鞋,工具箱,手电筒……这被遗忘的帝国里可谓应有尽有,甚至还包括一对哑铃。对了,我想,这对哑铃正是我十多年的一个秋天上午要找而没找到的那个关键词。那天我鼻尖发冷,瘫在沙发上,一动也不能动。那天仿佛也是一千年后的某一天,印度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一对哑铃。声音的肌肉。心如狮子。那儿,仿佛有一个贫穷的但有着美丽耳饰的小女孩在对着乡村发誓:她要拎着一对哑铃成熟并且生活。

Osnabruecke
K 教授在电话里说4点半他会准时派他的助手H博士来车站接我。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提前了一个小时从我的住地动身。到曼汉姆换车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地又提前一小时赶上了每一小时一班去Osnabruecke的车。我下车,时间是3点半。我没有见过H博士,我也知道他还没有来。还没有来,我开始闲逛起来。看着站台上候车和接车的人越来越多,熙熙攘攘,我感到我的那个作为被接的抵达者的身份已被掩埋起来。另一种现实开始朝我敞开:是的,跟大家一样,我在等。但我在等什么?我在等那个将在人群中等我的人。还剩五分钟,在四周微微骚动的紧张之中,在真相大白之前,我想依靠某个“直觉的奇迹”来辨认出那个也要辨认我的人。当我注意到一个抽着卷烟偎着廊柱张望,高瘦、戴眼睛而近身处又没有任何行李的中年男人时,列车正好停靠站了。他的眼睛四下忙碌着。是他的侧影使我直觉到他是一个脆弱易悸的人。我便悄悄地从他身后绕过去,混同旅客们再次登上车,又迅速地挤到他眼前的那节车厢,并左顾右盼地提着公文包走了下来。我露出微笑,径直朝他走去,伸出手,嗫嚅道:“哈罗,H博士!”他的目光移向我,表情彬彬有礼,很快把烟头扔到地上。他侧头扔烟的那一瞬,列车启动,而我看到我们四周的宇宙因恢复其内部的那个似是而非的正常编码而焦虑地颤抖了一下。

Umweg
在撒旦的阳光下
我们执迷得宁愿绕道
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
我们固执得不顾风暴
也许事情十分微小
去道一声别,或者买一盒烟
首先是往常的过道堵了
黑白分明的纸条在警告
“真噁心”,我们诅咒一声
转身下一层玻璃楼,再试试
出去,这时秋天又来阻拦
它把天桥损坏了;那个
上去的螺旋梯呢,拦了一根绳索
那个寒风中立在桥上的工人
我们只瞟见了他一瞬
事后回想起他的眼神和姿态
他手上“哗哗”的小黄旗
虽只是那么一瞬,但我们知道
他就是那个亚伯利恒人
那个殉难的人
那之后他的样子真变了不少
他当然也看见了我们
当然也想阻挡;不过他不是门吗?
既阻挡又让进
他不也是道路吗?
于是我们继续前进,我和我
陌生的同伴
当我们接近最后一张门
她朝我会意地,嫣然一笑
于是我们通过自己到达了
那个永远去不了的地方
去买一盒烟,或者道一声别
在希望的黎明的预感中
我们不是曾发誓不去吗?
在撒旦的阳光下
我们痛苦得象天空
让你对撒旦说:我在这儿
让我对天空说:我不存在
22. okt. 1988. Trier
张枣(1962年—2010年3月8日),湖南长沙人,诗人、翻译家。著有诗集《秋天来信》,代表作有《镜中》《何人斯》。
足下有路 诗行万里
微信号:qrsgwl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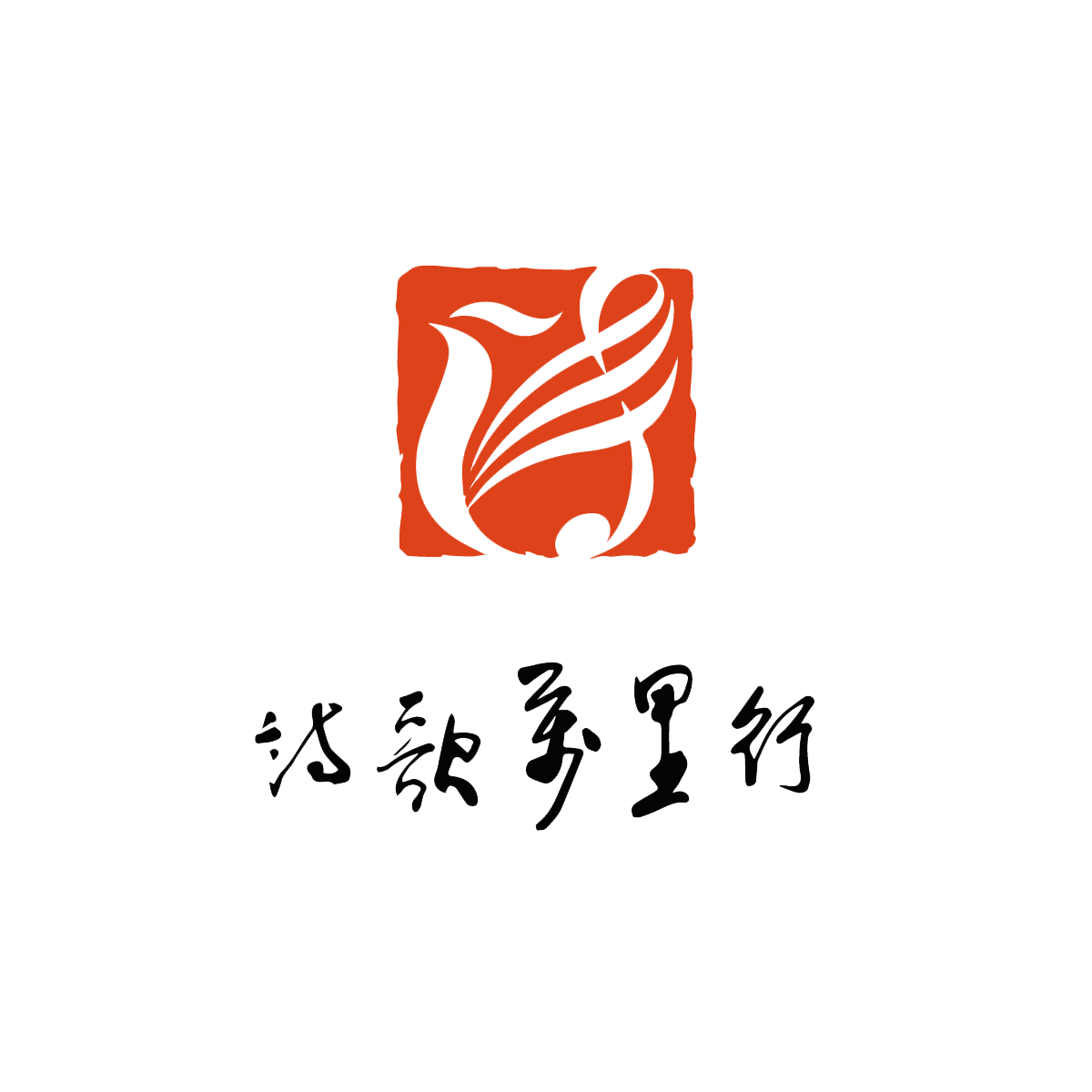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