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博事件”的持续发酵,关于庞家与南博双方争论的点也在不断细节化,具体化。其中有些问题已经逐渐清晰,但还有一些依然迷雾重重,有待进一步揭示。笔者不揣冒昧,想根据自己二十余年的从业经验,就现在大家激烈讨论的一些点给出个人的猜想。如果将来被证伪,那也请诸位口下留情,多多包涵。
一、关于南博方面出示的1961年鉴定意见是否可靠。
庞叔令提出,南博方面未出示1961年、1964年的鉴定意见原件及材料全貌,进而质疑两次鉴定意见(主要是1961年那次)是否真实有效。

由于南博方面宣称参与1961年鉴定工作的韩慎先、谢稚柳两人,工作笔记没有公开出版,而在张珩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又查不到相关的记录,故而网上对此事的质疑之声一度很高。但随着张珩关于此次巡回审查工作致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等领导的《报告(手稿)》(以下简称“《报告》”)被披露,可以确认张珩的确是参加了本次鉴定。

但韩慎先、谢稚柳是否参与了工作,目前还无从确认,但我有怀疑,谢稚柳很可能缺席了在南博的鉴定工作。依据有三:
- 张珩在《报告》中明确提到“除韩、谢两同志或因到宁稍晚,或因事提前返沪外,我自始至终都参加了。”而“稍晚”与“提前”在程度上显然不同。
- 鉴定意见“江南春图卷,伪,一般。陈鎏题引首真,后面题跋完全不对。伪做得很好,原庞家是当真的藏的”。这三句话,除了第一句是依凡例作的结论外,第二、三两句在语意中其实有些微冲突。既然“后面题跋完全不对”,那又何来“伪做得很好”呢?而这更像是记录了两个人的观点。那么第三人呢?而且熟悉《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朋友会发现《图目》中谢稚柳表达鉴定意见的口气与此不尽相同。
- 谢稚柳之子谢定伟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提到,从未听其父在生前提到过1961年的南京之行以及关于《江南春》图卷真伪的讨论。
- 谢稚柳“提前返沪”能合理解释郑重《谢稚柳年谱》中未记载1961年11月南京之行的原因。

至于南博方面没有出示鉴定意见原件以及网上很多人强调没有看到鉴定人员的签名,这倒很可能是因为不熟悉此类书画鉴定工作而产生的误会。由于此类鉴定活动的工作量极大,通常都是由鉴定专家口述鉴定意见而由工作人员记录整理后再形成正式文本。通常鉴定专家是在材料的最后一页签名,甚至有可能因当时制度的不完备而根本没有签名。

“主要由于数量大,时间短,我们最多几天平均要看到一千七百件一天。”——张珩《报告》
二、1986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以下简称“七人小组”)在南博未看到《江南春》图卷,其背后是否有隐情?
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未收录,杨仁恺、刘九庵的工作笔记中未记载来推论,当年“七人小组”在南博应该是没有看到《江南春》图卷,那这是由于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是否存在如某些人猜测的,当时的管理者已有将之处理掉的打算呢?
以我个人的看法,很可能是“小私心有,大猫腻无”。“七人小组”成立的背景是文革结束后,各地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内收藏了大量未经鉴定的书画作品,而当时的原则是,“七人小组”到某地,某地的文博单位准备待鉴定的书画作品。
而这其中有的单位格局较大,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尽可能多地将库藏作品都拿出来请专家鉴定,并在鉴定结束后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大力支持了兄弟单位的书画收藏事业。比如“七人小组”在上海朵云轩花费了23个工作日,鉴定了近一千六百件(套)古代书画,而事后上海朵云轩以此为基础,向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提供了300多件元、明、清书画、书札精品。而辽宁省博物馆的杨仁恺也因此与上海朵云轩及其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而有些单位的格局就比较小,生怕由于此次“巡检”而漏了库底,导致将来作品被上级调拨或讨要(因为有不少作品系“十年动乱”期间由抄家而来,从法理上来说应当发还原收藏者)。因此南博方面是不是因为这种考虑而将之前被列为“伪作”的《江南春》图卷藏着掖着,不愿拿出来请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刘九庵等人过目,我以为还是很有可能的。
至于认为当时的领导已经有将其私下处理的想法,则略显“阴谋论”了一些。毕竟给南博方面后续一系列操作留下政策空间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1986年版)当时刚出台,而最终出售作品的“江苏省文物总店”要迟至1990年12月才成立。

但无论如何,南博方面没有将《江南春》图卷交“七人小组”复检,也使其失去了避免后续一系列争议操作发生的机会。
三、南京方面提供的江苏省文物商店发票是否可靠?
“新华社”的报道援引南京方面提供的说法,认为《江南春》图卷于2001年以人民币6800元的价格售出,至此离开文博系统,流入私人藏家手中。并提供了相应的发票作为佐证。

可随后马未都在视频中声称当年的文物商店发票,抬头处应该实名登记而不应该写“顾客”二字,进而质疑该发票的真实性。由于马未都在圈内外的影响力,这一说法也为广大网民所采信。
但我以为发票的真伪应该毋庸置疑。且不说发票造假极易被识破,尤其在当时江苏省文旅厅已组成工作专班作联合调查的前提下,南博方面绝不至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更关键的是我手中就有2004年苏州文物商店开具的发票,“购货人”一栏索性就是空白的。

当时国内的文物商店数量非常多,我们不能仅凭马爷一句话就认为江苏省文物总店的那张发票就有问题。
那么马未都是不是就纯瞎掰呢?其实也不是。只不过是他老人家岁数大了记岔了,当时在文物商店买东西,在一种情况下确实必须实名登记。那就是在“内柜”购买所谓的“线上文物”。比如下面这张我2005年在上海文物商店购买文物时开具的发票,不但登记了我的名字,还登记了我的身份证号码。而两种发票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字样是“外销”发票而后者是“内销”发票。马未都这样的大咖,当年在文物商店购买的基本都是“清三代”往上的文物,自然是需要实名登记了。

在文物进出境审核中,传统上“乾隆六十年(1795)”是一个分界线,在此年份之前的被称为“线上文物”,反之则称之为“线下文物”。在《江南春》图卷调拨调剂到江苏省店的最后一次鉴定的材料中,也出现了“线下”的字样。原则上“线上文物”不允许出境,故而在文物商店销售时只允许境内人士购买且必需实名登记,开具内销发票。这种柜台因此也被俗称为“内柜”。

至于有些人认为该发票是江苏省文物总店在私下处置掉《江南春》图卷之后为了平账而后补的票据也不符合常理。因为当年“艺兰斋”在获得该卷后是公开向外宣传,并广邀同好赴宁鉴赏的,可见在陆挺看来此项交易光明正大,无需遮掩。而该卷从南博调拨调剂到江苏省店手续都是齐全的,江苏省店的销售也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根本没必要鬼鬼祟祟搞张财务上不知该如何处理的后补发票出来。
那么是不是这张发票就没问题了呢?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发票是真的,但其上的“仿仇英山水卷”对应的根本不是《江南春》图卷,而应该就是一件普通托名“仇英”的“苏州片”。

“苏州片”是指明晚期至清代以苏州地区为核心,托名仇英、文徵明等大家而制作的工笔绘画作品。通常以绢本重彩的山水、人物手卷最为常见。
依据有三:
- 丁蔚文在其硕士论文《仇英<江南春>考辩》中提到“艺兰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获得此卷;
- 有网友发现2000年4月下旬出版发行的《读者》杂志第33页左侧的广告彩页中赫然印着“艺兰斋另存有仇英《江南春卷》图”字样,而此日期早于南博所出示发票上的2001年;
- 发票上人民币6800元的售价与该作的现实状况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文物商店的商品销售,其定价是要经过店内合议环节的。以《江南春》图卷这样名家递藏,钤印累累,长达7米的巨制,根本不可能在2001年能以此价格对外销售,更遑论业内一直有传闻,陆挺获得此卷的成本是人民币16万元。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该作是领导私下低价卖给陆挺以便从中牟利。但试问有如此“好事”,明明1997年就已调拨到店,为何要时隔四年之后才会以如此容易引起他人猜疑的价格销售?
因此我的推测是,当此事件引起舆情,江苏省文旅厅已决定组织工作专班开展联合调查的当口,由于时隔已久,实在找不到《江南春》图卷当年出售的材料,为了形成逻辑闭环,不知道哪位大聪明找了张2001年的发票出来,并指鹿为马,声称其上的“仿仇英山水卷”即《江南春》图卷,以图蒙混过关。只可惜这届网友不好骗了,这才导致如今破绽百出,顾头不顾腚。
“江苏省文物总店”已于数年前出售给“苏豪”集团,当年的原始材料即便没有处理销毁,短时间内要厘清也是难于登天。很难想象南博方面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找出这张2001年的发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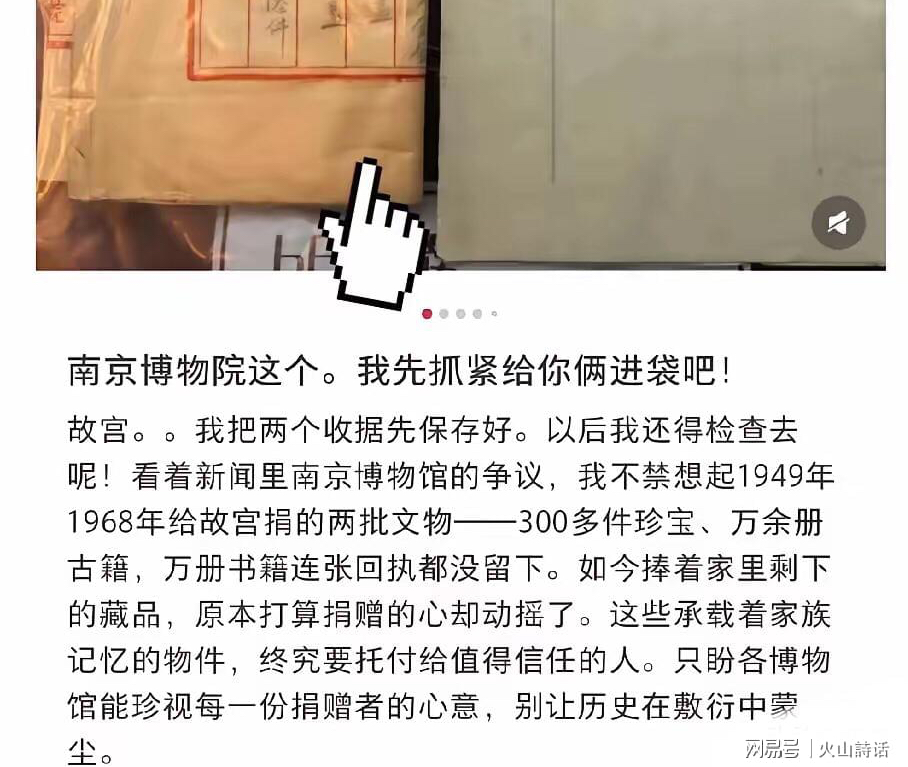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