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
引子
1936年8月2日,一列火车从哈尔滨开往珠河。车厢里,一个浑身是伤的女人向日本宪兵要来纸笔,写下了一封信。
信很短,只有一百多个字。收信人是她7岁的儿子,她已经6年没见过他了。
信的末尾,她写了一个名字:赵一曼。
这是一个化名。她的儿子不知道母亲叫赵一曼。她的丈夫不知道。她的姐姐也不知道。
整整20年后,她的儿子才知道,银幕上那个让全国观众落泪的抗日女英雄,就是他苦苦寻找的母亲。

01
1905年,四川宜宾白花镇,一个地主家庭迎来了第七个孩子。父亲李鸿绪给她取名李坤泰,字淑宁。
"淑宁"两个字,寄托的是父母的期望——希望她做个安静贤淑的大家闺秀,嫁个好人家,平平安安过一辈子。
可这个女孩,从小就不安分。
八岁那年,家里要给她裹脚。她拿菜刀把裹脚布和小尖鞋全剁了,家里人气得直跳脚,却拿她没办法。十几岁时,她在村里组织了个"妇女解放同盟会",专门反对封建陋习,会员很快发展到180多人。她们在闹市贴标语、画漫画,把那些欺压妇女的乡绅画成狐狸、恶狗。当地的封建势力恨得牙痒痒,扬言要用粪水泼她们。
家里人怕她惹事,把她关在房间里九个月,让她学绣花。九个月过去,一朵花都没绣出来,倒是读完了一屋子的进步书籍。
1926年,21岁的李坤泰做了一个决定:去武汉,考黄埔军校。
那一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一次招收女学员,全国只录取了195人。李坤泰是其中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事院校的女学员。她们剪短发、穿军装,和男学员一样训练、一样上课。
1927年,大革命失败。李坤泰被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个湖南人,陈达邦。两人都是黄埔出身,都是共产党员,志趣相投,很快坠入爱河。1928年4月,经组织批准,他们在莫斯科结婚。
蜜月还没过完,李坤泰就怀孕了。
可她没能享受多久初为人母的喜悦。国内革命形势紧张,组织决定调她回国。1928年11月,怀孕五个月的李坤泰踏上了归途。
那是一段难以想象的旅程。为了躲避盘查,他们不能坐火车,只能徒步穿越冰天雪地的国境线。大雪没过膝盖,寒风刺骨,她挺着大肚子,一步一步往前挪。
后来她对朋友说:「我们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用绳子捆起来推出国境线。这孩子也命大,居然在肚子里安然无恙。」
1929年1月21日,李坤泰在宜昌生下了儿子。这一天,是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她给儿子取名"宁儿",希望他一生安宁。
可她自己的人生,注定与安宁无缘。
孩子生下来才一个月,麻烦就来了。
当时李坤泰住在一个码头工人家里。一天,她需要用钱,把自己的结婚戒指拿去典当。谁知这个举动被特务盯上了,她的身份暴露了。
情况紧急,她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连夜坐船逃往上海。
1930年,李坤泰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宁儿送走。革命工作越来越危险,带着孩子实在不方便。她把宁儿送到了丈夫的堂兄陈岳云家里,托他抚养。
临走前,她抱着宁儿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
这是母子俩唯一的一张合影。
她不知道,这一别,就是永诀。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李坤泰主动向组织请缨,要去东北参加抗日。
组织批准了。
临行前,她去陈岳云家看了宁儿一眼。两岁多的孩子已经会说话了,见到妈妈来,抱着她的腿不让走,哭得撕心裂肺。李坤泰硬是掰开孩子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刚转过身,眼泪就唰地流了下来。
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儿子。
她化名"赵一曼",踏上了白山黑水的土地。
有人问她为什么叫"赵一曼"。她说:「我喜欢'一'字,'一'代表一生革命、一心一意、一贯到底。」

赵一曼到东北后,先是在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1933年4月,她策划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把城市交通瘫痪了好几天,最后迫使日伪当局答应了工人的条件。
但她真正让日军胆寒,是在山林里。
1934年,赵一曼被派到珠河县(今尚志市)开展抗日游击工作。她到的时候,手里一无人,二无枪。几个月后,她从农民会里挑了三十几个青年,组建起一支游击队。没有枪?她就带人去摸日军的岗哨,一点一点地缴获。
很快,这支队伍扩编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赵一曼担任政委。
战士们叫她"我们的女政委",老百姓叫她"瘦李"、"李姐"。日伪报纸用另一个称呼来形容她:"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
有一次,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团在侯林乡被两个团的日伪军包围,苦战一天也没能突围。就在最危急的时刻,敌人背后突然响起枪声。赵一曼骑着白马,手持双枪,带着游击队旋风般杀入敌阵。敌军阵脚大乱,仓皇溃逃。
日军悬赏十万元通缉她。可落到他们手里时,没人敢看她的眼睛。
1935年11月15日,赵一曼率领的第二团被日伪军包围在一座山间。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打退了敌人六次进攻,击毙日寇三十多人。可敌人越围越多,必须突围。
团长让赵一曼带队撤退,自己留下掩护。赵一曼不同意:「你是团长,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团长说她是女同志,她火了:「什么男的女的!谁说女同志就不能打掩护!」
掩护突围时,赵一曼左手腕中弹。她带着几个战士潜入村里养伤,三天后被敌人发现。在激战中,她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失血过多昏迷过去。
醒来时,她已经被捆在担架上,周围全是日本兵。
04
日军把赵一曼押到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他们知道她的价值——这可是"红枪白马女政委",抗联的核心人物。只要她开口,整个东北抗联的活动机密就全暴露了。
审讯开始了。
据后来解密的日伪档案记载,日军对赵一曼使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鞭打、吊拷、老虎凳、竹签夹手指脚趾、拔指甲、拔牙齿、压杠子、搓肋骨、灌辣椒水、灌汽油、烙铁烫……
她的腿伤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伤口化脓溃烂,脓血浸透了棉被。日军用马鞭狠戳她的伤口,想用剧痛让她开口。
赵一曼疼得几次昏死过去,醒来后只说了一句话:「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日军疯了。负责审讯的军官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席上供述:「她那种激愤之情,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控诉日军的罪行,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
他还说:「她从容地抬起头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步。」
酷刑持续了近一个月,赵一曼什么都没说。她的伤口严重感染,高烧不退,生命垂危。日军担心她死了就什么都得不到了,1935年12月13日,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
在医院里,看守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27岁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山东人,老实本分;一个是17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还是个孩子。
赵一曼没有放弃。她躺在病床上,身上缠着绷带,却开始给这两个年轻人"上课"。她给他们讲抗联的故事,讲日军在东北犯下的罪行,讲亡国奴的屈辱。她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抗日。」
董宪勋和韩勇义被她打动了。他们从羡慕这个女英雄,到同情她,再到下定决心:要帮她逃出去。
1936年6月,董宪勋听说自己可能要被调走。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赵一曼,三个人开始密谋越狱。
韩勇义把父亲留给她的嫁妆——两个金戒指、两件呢料大衣——全卖了,换来60块钱当经费。董宪勋找人做了一顶小轿,因为赵一曼的腿伤还没好,不能走路。
6月28日。他们定在这一天动手。正好那天董宪勋值夜班。
1936年6月28日夜,哈尔滨下起了暴雨。
一辆白俄司机开的出租车停在医院后门。董宪勋和他的堂侄董广政把赵一曼从病房背出来,穿过板障子的缝隙,上了车。韩勇义早已在道外五道街等着,雇好了轿子和五个轿夫。
他们换上轿子,冒着暴雨,向宾县三区的游击区进发。
暴雨下了一整夜。乡间土路泥泞不堪,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走到阿什河边,发现"万缘桥"被洪水冲垮了。没办法,只能趟水过河。齐腰深的河水湍急,几次差点把人冲散。
天亮时,他们到了金家窝棚——董宪勋远房叔叔董元策的家。稍作休整后,又换上马车,继续赶路。
只剩20公里了。再走20公里,就能到游击区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20公里,会成为赵一曼生命中最漫长的距离。

赵一曼失踪的消息,像炸弹一样在日军中炸开了。
警察署的军官暴跳如雷,下令全城搜索。他们很快从那个白俄司机那里得到了线索,又从轿铺老板嘴里问出了去向。
日本军官立刻带人追击。可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阿什河的桥被洪水冲垮了。没办法,他们只好到附近村庄征了几匹马,骑马直追。
6月30日清晨。
马车正行驶在阿什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地方。赵一曼躺在车上,身边是董宪勋、韩勇义和董广政。再走一小段路,就能看到游击区的哨卡了。
突然,身后传来马蹄声。
赵一曼的心沉了下去。她知道,完了。
日本军警追上来了。几个人被当场抓获。
赵一曼看着董宪勋和韩勇义,心里比刀割还难受。她知道,这两个帮助她的年轻人,不会有好下场。
审讯时,她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她说是自己用重金贿赂了董宪勋和韩勇义,他们只是贪财。可她哪来的重金?逃跑的经费,是韩勇义变卖嫁妆换来的。
日军不信。董宪勋被关进监狱,酷刑折磨,最后死在狱中。韩勇义虽然被释放,但身体已经被摧垮,几年后病逝,年仅29岁。
这两个年轻人,用生命为赵一曼换来了两天的自由。
赵一曼被押回哈尔滨后,等待她的是更疯狂的报复。
日军彻底放弃了从她嘴里套出情报的念头。他们现在只想折磨她,想看看这个女人到底能承受多少痛苦。
7月25日,日军决定对赵一曼实施最残酷的电刑。
根据日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档案记载,负责审讯的军官林宽重说:「用刚从本土运来的新式电刑器具对赵女士实施电刑。总之,要慢慢地跟这个女人耗,不能停,不能让她有喘息的机会,直到电刑摧垮她反满抗日的意志,撬开她的嘴。」
电刑开始了。
电流一次次穿过赵一曼的身体。她的身体剧烈颤抖,惨叫声在审讯室里回荡。大野泰治后来供述:「那声音,好像来自地狱一样。」
七个多小时。电刑断断续续持续了七个多小时。
赵一曼的头无力地垂了下来,全身像被抽掉筋一样软软地挂在刑架上。她昏死过去了。
日军的报告里写道:「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他们不明白,一个看起来那么瘦弱的女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志。
他们永远不会明白。
1936年8月1日,日军做出了最终决定:把赵一曼押回珠河县,公开处决,"杀一儆百"。
第二天凌晨,赵一曼被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
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段路了。
火车在黑暗中行驶。赵一曼突然想起了宁儿。
六年了。她已经六年没有见过儿子了。那个在她怀里哭着不让她走的小男孩,现在应该七岁了吧?上学了吗?长高了吗?还记得妈妈的样子吗?
她向看守的日本宪兵要来纸和笔。
宪兵犹豫了一下,给了她。
赵一曼开始写。她的手被酷刑折磨得几乎握不住笔,但她还是一笔一划地写了下去: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落款: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
她故意没有写自己的真名。她怕日军顺藤摸瓜,找到她的家人。
火车到站了。
赵一曼被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街道两旁站满了被日军逼来观看的百姓,人们低着头,不敢出声,眼眶却都红了。
大车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停了下来。
几个日本兵举起枪,对准了赵一曼。
一个日军军官走到她面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赵一曼抬起头,目光像刀子一样看着他。她把手里那张写给儿子的纸递过去:「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然后,她高声唱起了《红旗歌》,又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日军军官猛一挥手。
枪响了。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倒在了珠河县小北门外,倒在了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她只有31岁。
一个目击了行刑过程的日本警察后来写道:「她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08
赵一曼死后,那封遗书被日军收进了档案,锁进了柜子里。
远在武汉的宁儿,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妈妈很早就离开了,说是去"做事",一直没有回来。他在伯父家长大,别的孩子有爸爸妈妈,他没有。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待着。
1950年,电影《赵一曼》上映,轰动全国。那个在日军酷刑下宁死不屈的抗日女英雄,让无数观众落泪。
21岁的陈掖贤(宁儿的大名)也去看了这部电影。他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的女人被日本兵折磨、被处决,心里很难过。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女英雄,就是他苦苦寻找的母亲。
六年后。
一模一样。
赵一曼就是李坤泰。这个秘密,终于在二十年后大白于天下。
1957年,陈掖贤得知了真相。
他呆住了。然后,他哭了。放声大哭。
他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在母亲的遗物前站了很久。那封遗书的原件就放在那里,字迹歪歪扭扭——那是母亲被酷刑折磨后,用几乎握不住笔的手写下的。
「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陈掖贤一字一句地把遗书抄在笔记本上。抄完后,他做了一件事:用钢笔蘸着蓝墨水,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了三个字——赵一曼。
这三个字,一直留在他的手臂上,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政府通知他去领母亲的抚恤金。他拒绝了。
他说:「我不要。那是妈妈的鲜血钱,我怎么能花那钱?」
后来,他连烈属证都没有去办。
陈掖贤的一生,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从来没有松开过。
他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性格孤僻。他不善交际,不会打理生活,甚至连自己的衣服都不会洗。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当政治课老师,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1957年,他和一个叫张友莲的女学生结婚了。两人生了两个女儿。可婚姻并不幸福。他们性格不合,经常吵架,后来离婚了,又复婚了,又离婚了……
1966年,父亲陈达邦被诬陷打倒,陈掖贤百思不得其解,写信给中央为父亲申辩。因为信中说了一些敏感的话,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隔离审查。
1980年代初,妻子张友莲病逝。
陈掖贤彻底垮了。
1982年8月15日——这一天,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工厂的同事发现陈掖贤连续旷工好几天,去他家看望。
门是锁着的。撬开门,他们看到了陈掖贤的尸体。
他自杀了。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53岁的生命。
他的手臂上,那三个用钢笔刺的字——"赵一曼"——还清清楚楚地留在那里。
他留下了一封遗书,是给两个女儿的。遗书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一句叮嘱:
「千万不要以烈士后代的身份自居,不要给国家找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
还有一句:「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的自杀而看低我的母亲。」
10
赵一曼有两个孙女,大的叫陈红,小的叫陈明。
陈红和奶奶长得很像。很像很像。矗立在四川宜宾翠屏山的赵一曼塑像,就是以陈红为原型塑造的。
后来,有一个日本老兵找到了陈红。
这个老兵参加过侵华战争,晚年良心不安,想当面向赵一曼的后人忏悔。他还请来了电视台,准备全程拍摄,想给自己的晚年留一个"功德圆满"的结局。
陈红拒绝了。
她说:「你们犯了罪行,承认自己的罪行我是赞同的。但我无法代替我奶奶去接受,我做不到。说小了,我们有家仇;说大了,我们有国恨。」
日本老兵又拿出钱来,说要给她经济补偿。
陈红说:「这就更不行了,先生。我,赵一曼的孙女,怎么可能要日本人的钱呢!不但是我,就是别的中国人,也不会。金钱不能赎回战争的罪恶,请你收回去!」
日本老兵悻悻而去。
2008年,日本《朝日新闻》想采访陈红,请她到赵一曼故居做画面介绍。
陈红说:「我听了你们的采访计划,表面上看是好的。可是,你们国家对侵华战争死不认罪的态度,你能如实报道吗?对不起,我不能接待你们。」
有人问陈红,为什么这么倔。
她说:「奶奶是一个弱女子,甚至给自己取的字都是'淑宁',希望安宁平静地生活。但时代没有给她一个安宁的立锥之地。她没有屈服,而是选择了反抗,选择了一种为更多人的安宁而不惜牺牲的信念。」
如今,在哈尔滨市中心,有一条街叫"一曼街"。这条街上有东北烈士纪念馆,门牌号是"一曼街241号"。
像是在等着什么。
像是在等着再一次出发。
参考信息来源
东北烈士纪念馆馆藏档案
日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档案
《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央视纪录片
中国军网、共产党员网相关报道
赵一曼孙女陈红采访资料
《赵一曼家事》系列报道(人民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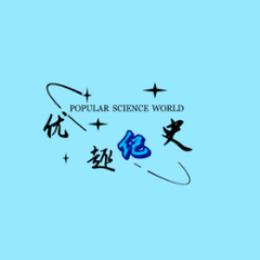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