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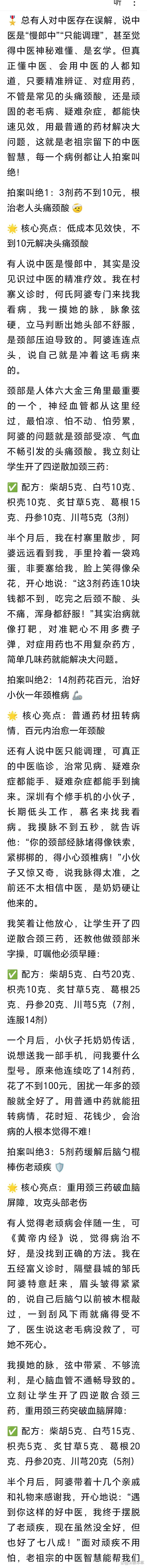


黄昏的光,斜斜地,懒懒地,从西窗棂格子里筛进来。书房里浮尘静静旋舞,像一场无人观赏的梦。我就在这梦的边缘,拂开《辞海》厚重的暗红色封面,触到了底下那本笔记。
蓝布封面,是洗得发白的雨过天青色,边角被岁月磨得起了毛,软软的,像鸟腹的绒。翻开,纸页脆黄,窸窣作响,声音干干的,像秋天踩过积叶。墨是褪了色的蓝黑,字却工整,一笔一划,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用力。开篇便是“应知应会”,底下,祖父的笔迹便开始铺展了。
“六亲不认:父、母、兄、弟、妻、子。”
我的指尖抚过那六个字。眼前仿佛不是字,而是六根沉默的、深扎在血脉与伦理里的桩。它们圈定了一个人最原初的、不可挣脱的根系与牵绊。祖父写下它时,是在怎样一个夜晚?煤油灯的火苗,大约也是这样昏黄地跳着,映着他清癯的脸。他或许在想着那个即将离家的儿孙,怕他在外头失了根基,忘了来路,才要这样一笔一划,将这人之为人的“根本”,像刻碑一样,刻进纸里。这不是注解,是锚,一个老人为漂泊的船,在纸上定下的锚。
再往下翻,世界便在纸上哗啦一声,热闹了起来。“五花:金菊花、木棉花……” 旁边蝇头小楷注着:“茶、医、歌、伎、役”。我读着,耳畔竟无端响起市声来。是茶楼里跑堂清亮的吆喝,是江湖郎中叮当的虎撑,是勾栏瓦舍间咿呀的水磨腔,是码头脚夫沉实的喘息。一个“五花八门”,原来不是虚的,它曾是一个多么热气蒸腾、活色生香的人间!祖父用几个词,就为我推开了一扇门,门外是整条长街的烟火,那烟火的颜色与声响,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依旧扑面而来。
然而热闹很快便静了下去,一股寒意悄然爬上脊背。停在“株连九族”那一页。祖父不仅写了,还在页边,用极细的笔尖,画了一个小小的、树根般虬结的族谱。墨迹在“己身”那个位置,洇得格外深,纸面都微微凹陷下去。我盯着那个点,像盯着一个黑洞。这不是词,这是一张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冰冷坚硬的巨网。那些被墨线无情串联起来的名字,他们是谁的父亲,谁的儿子,谁在春闺梦里等待的良人?在最后的时刻,那张网收拢,他们可曾在恐惧中相拥,还是在绝望里互相怨怼?一个词语的骨骼里,竟能藏着如此庞大而寂静的腥风血雨。书房里浮动的尘埃,那一刻,仿佛都带着铁锈的气味了。
“人有三急:性急、内急、心急。”
旁边,祖父画了个小小的、笨拙的笑脸。笔墨很淡,却让整页纸都暖了起来。下面一行小字:“人同此身,身同此理,毋苛责,存厚道。” 我几乎要笑出声,眼里却蓦地一热。原来,在那些关乎宗法、生死、行业的大词之下,在最沉重的历史阴影里,先人竟还留着这样一份体己的、温热的人情。它像寒夜里一件悄悄递过来的旧棉袄,不华美,却足以御人世的霜,让你觉得,生而为人,那点最本能的仓皇与窘迫,是被看见的,也是被原谅的。
夕阳沉得更低了,光变成了浓郁的金色,像融化的蜜,涂满了书桌的一角。我的目光落在最后,那是父亲的笔迹,飞扬跋扈,带着他那个时代特有的、要刺破一切的锐气。他在“三妻四妾”的词条下,用力划了两道深深的横线,像是斩断什么。旁边批道:“旧时秽制,今日观之,乃女子血泪史。我儿谨记:心唯其一,白首不疑。”
那“不疑”两个字,写得力透纸背。金色的光恰好落在那里,将字迹照得微微透明,边缘融化在光里,又坚定地浮现出来。尘埃在那束光里舞得更欢了,无声,却喧嚣。
我合上笔记。蓝布封面贴着掌心,被我握得微微发烫。书房重归寂静,可这寂静,已然不同了。它被那些词语填满了,被两代男人的沉默与诉说填满了。祖父的“应知应会”,是交给我的,关于这个庞杂世界的说明书,冷静,清晰,带着旧式文人的考据癖。父亲的“我儿谨记”,则是他交给我的,一把用以劈砍荆棘、在荒原上开辟道路的斧钺,炽热,决绝。
从此,这些词语于我,便有了骨血,有了魂灵。再说“三生有幸”,我会想起前生、今生、来生那漫长而无垠的时间之河;再说“五体投地”,我的膝、肘、额,会记得一种最谦卑也最虔诚的姿态。词语的密码被破译了,背后连通的,是一个家族沉默的呼吸,是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是无数个在黄昏里,将一生感悟与祈愿,默默写给后来者的,那些无名者的面孔。
我将笔记放回《辞海》之下,那最初的所在。光移走了,书房暗了下来。可我知道,有些什么已经被点亮了,就在我心里,像一颗被擦亮的、温润的旧星子,悬在认知的夜空里,从此,它将为我映照出词语背后,那些更深、更远的东西。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