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理论开始之前,在一切定义下达之前,我想先请你闭上眼睛。忘掉你手中的手机,忘掉窗外的车水马龙,忘掉2026年的秩序与安稳。跟我走。我们要穿越回1871年5月的巴黎。
请深吸一口气。你闻到了什么?没有左岸的咖啡香,没有香榭丽舍大街的香水味。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烧焦的橡木味,还有一种更令人作呕、黏腻在鼻腔里的味道——那是尸体在高温下腐烂散发出的甜腥味。你现在站在塞纳河畔一栋灰色的老房子里。你透过那一扇满是灰尘和裂纹的窗户,向外窥视。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法兰西帝国的象征,那座金碧辉煌、见证了无数王权更迭的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此刻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狰狞的火炬。烈火冲天而起,把巴黎的夜空染成了惨厉的血红色。那红光映在塞纳河上,像是一条流淌的鲜血。
再往下看。街道上没有警察,没有士兵,没有法律,没有秩序。只有人。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挤在一起、蠕动着的人。他们手里挥舞着松脂火把,挥舞着从废墟里捡来的铁棍,挥舞着还在滴血的刺刀。他们是谁?仔细看他们的脸。昨天,他可能还是那个对你脱帽致敬、一脸谦卑的面包师,为你烤出松软的牛角包。昨天,她可能还是那个在街角缝补衣服、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家庭主妇,温柔地哄着孩子睡觉。昨天,他可能还是那个在教堂里虔诚祈祷、看起来老实巴交的鞋匠。
但是今天,此刻。你看着他们的脸,你会感到背脊发凉。那上面涂满了黑色的烟灰和红色的血污。你看不到一丝“人”的表情。你看不到犹豫,看不到怜悯,看不到恐惧,也看不到理智。他们的眼睛里只闪烁着一种光芒——那是一种混合了狂热、迷醉和绝对虚无的兽性之光。他们嘶吼着,像野兽一样咆哮着:“烧光它!杀光他们!把旧世界的

一切都砸个稀巴烂!”这不是革命,这是一场集体的癫狂。这就是“巴黎公社”最血腥的一周。
在窗户后面,站着一个30岁的男人。他的名字叫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请记住这个时刻,朋友们。这本《乌合之众》里所有的刻薄、所有的毒舌、所有的洞见,甚至那让人听起来刺耳的傲慢,都诞生于这一秒钟的颤栗。勒庞是谁?他不是那种躲在象牙塔里、喝着红茶写论文的老学究。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英。他是医生,他懂解剖学,见过人体的内部构造;他是人类学家,他跑遍了世界,研究过所谓“低等民族”的头骨;他甚至还是个物理学家。他的大脑,是用最严格的逻辑、最冰冷的理性、最精密的科学训练出来的。他信仰秩序,信仰等级,信仰“精英治国”。他坚信,人类之所以能建立文明,是因为理性战胜了本能。
但是这一刻,他的信仰崩塌了。他看着窗外那群疯狂的暴徒,他感到了一种生理上的恶心,和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为什么把这些单独看起来如此正常、如此懦弱、如此温顺的个体,加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能够吞噬一切的怪物?那个面包师的理智去哪了?那个鞋匠的道德去哪了?那个作为“人”的灵魂,是怎么在瞬间蒸发的?他亲眼看着那些暴徒推倒了雄伟的旺多姆圆柱,那可是拿破仑战功的象征;他亲眼看着他们把巴黎大主教拖出来,像宰杀牲畜一样枪毙。勒庞意识到了一件事:逻辑死了。在这个新的怪物面前,你跟他讲法律?讲道德?讲因果关系?讲历史传承?就像你试图对着一场海啸念诵《圣经》一样可笑。海啸听不懂,海啸只会淹没你。
这场大火,烧掉了巴黎的皇宫,也烧穿了勒庞的内心。他透过火光,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这一夜,不仅仅是建筑的倒塌,而是一场文明的葬礼。他意识到,拿破仑的英雄时代彻底结束了。路易十四的君权时代也成了灰烬。历史的转盘,带着生锈的摩擦声,转到了一个最黑暗的刻度。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来自底层的、盲目的、破坏力惊人的力量,正在从地狱的裂缝里喷涌而出。这股力量不讲道理,不听指挥,没有逻辑,只有纯粹的破坏欲。勒庞给这股力量起了一个名字,叫——群体(The Crowd)。
他在书里写下了一句让所有统治阶级、所有知识分子、所有中产阶级都瑟瑟发抖的判词。如果你手里有书,请翻开导言,用红笔狠狠地画下这句话:
“大众阶层进入政治生活,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惊人的特征。”
(The entry of the popular classes into political life i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epoch of transition.)
这句话听起来很学术,很客气,对吗?让我给你翻译成“人生实话”:“完了。野蛮人破门而入了。那些没脑子的家伙要掌权了。我们要完蛋了。”在勒庞看来,文明是什么?文明是极其脆弱的瓷器。它是由少数精英——那些有智慧、有克制、有长远眼光、懂逻辑的人——小心翼翼地搭建起来的。文明需要规则,需要压抑本能,需要深思熟虑,需要延迟满足。而群体是什么?群体是洪水。群体是细菌。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分解尸体。当一个文明变得衰弱、腐朽时,这群乌合之众就会冲上来,把一切理性的规则踩得粉碎,把一切高贵的建筑烧成废墟,让世界重回混沌。
所以,朋友们。当我们今天打开这本《乌合之众》的时候,我要你们调整一个心态。千万、千万别把它当成一本枯燥的心理学教材。也别把它当成百度百科里那几条干巴巴的定义。那是误读。这是一本遗书。这是一个旧时代的贵族,站在文明的废墟上,看着远处滚滚而来的尘土,发出的绝望尖叫。这也是一本求生指南。勒庞是在对着未来的我们——对着20世纪、21世纪的你和我大喊:“小心啊!那头野兽已经冲出来了!如果你们不了解它的习性,如果你们不解剖它的大脑,你们所有人,都会被它吃掉!”他之所以把笔触磨得像手术刀一样锋利,之所以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把群众骂得一文不值。不是因为他傲慢。而是因为他害怕。恐惧,才是这本书真正的墨水。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了勒庞的身边,我们感受到了他那颤抖的呼吸,也闻到了窗外那股硝烟的味道。那么,他眼中的这头怪兽——“群体”,到底是个什么生理构造?为什么一个博士进群就会变成傻子?为什么一个好人进群就会变成暴徒?在这个炼金炉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下一章,我们将穿上白大褂,拿起解剖刀。切开这个怪物的头颅,看看里面的脑浆到底变成了什么颜色。
01
什么是“乌合之众”?
我们把镜头从燃烧的巴黎拉回来。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一个最核心、最基础,但也最容易被误解的概念:到底什么才是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是不是你早上挤的地铁,那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厢,就是“群体”?是不是菜市场上,几千个讨价还价的大妈,就是“群体”?是不是整个法兰西民族,甚至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就是“群体”?勒庞摇了摇头,冷冷地说:“不。那只是一堆肉体的堆叠。”
在勒庞的显微镜下,一千个人偶然聚集在广场上,跟一千个石头堆在路边,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小算盘。你在想今晚红烧肉要不要多放糖,他在想明天的股票会不会跌,那个穿西装的在担心迟到扣工资。你们的大脑是隔离的,你们的灵魂是独立的。这时候,你们还是一群“人”。但是,听好了。如果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比如,突然有人高喊一声:“抓小偷!打死他!”或者,在这个国家面临巨大的危机时,一种狂热的爱国情绪瞬间席卷了所有人。就在这一秒钟。奇迹——或者说灾难——发生了。那一千个独立的大脑,仿佛突然被插上了一根看不见的网线。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感情,瞬间被强行同步,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个独立的“你”,死了。一个全新的怪物——“心理群体”(The Psychological Crowd),诞生了。
为了解释这个过程,勒庞用了一个极其精彩,也极其恐怖的比喻:化学反应。各位,你们初中都学过化学。你看,钠(Na),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很活泼,扔水里会爆炸。氯气(Cl),是一种黄绿色的气体,剧毒,吸一口能要你的命。这两个东西,性质完全不同,长得也不一样,对吧?但是,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让它们发生反应。它们变成了什么?氯化钠(NaCl)——食盐。那个白色的、晶莹的、咸咸的、你可以撒在薯条上吃的盐。请问,你在盐里面,还能找到金属钠的影子吗?还能找到毒气氯的影子吗?找不到。它们原有的性质彻底消失了,生成了一种全新的物质。
勒庞告诉我们:群体,就是那把盐。你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博士(就像金属钠)。你平时说话轻声细语,看到红灯绝对不走,连踩死一只蚂蚁都会觉得罪过。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流氓(就像氯气)。他平时满口脏话,以欺负人为乐,看到警察就跑。在平时,你们俩是两个物种,你们生活在平行的宇宙里,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一旦你们俩卷入了一场狂热的游行,或者加入了一个充满仇恨的激进组织。博士消失了。流氓也消失了。你们俩融化了,结合了,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群体细胞”。在这个新物质里,博士的智商不会拉高流氓的智商。博士的修养也不会中和流氓的野蛮。恰恰相反。一种全新的、原始的、只有脊髓反射的性质,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在那个燃烧的巴黎之夜,许多平日里的绅士、学者,竟然会和暴徒肩并肩,一起把那座精美的皇宫付之一炬。因为在那一刻,他们不再是绅士。他们只是这块“巨大的盐”里的一颗微粒。
勒庞给这个现象起了一个学术名词,叫:“自觉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自觉的个性消失了,感情与思想转向同一个方向。”
(The disappearance of conscious personality and the turning of feelings and thoughts in a definite direction.)
这听起来有点绕,让我用“人生实话”给你翻译一下:你的大脑皮层断电了。什么是“自觉人格”?就是那个叫“我”的东西。是那个会权衡利弊、会害怕坐牢、会讲逻辑、会因为羞耻而脸红的你。这个“我”,是我们受了几十年教育,读了无数本书,挨了无数次社会的毒打,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理性防线。但是,这道防线极其脆弱。一旦进入群体,那种巨大的情绪浪潮,那种“千万人吾往矣”的归属感,会像海啸一样,瞬间冲垮你的理性防线。“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在这个过程里,你不会感到痛苦。相反,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你不再孤独了,你不再渺小了,你不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琐事烦恼了。你融入了一个伟大的整体。你觉得自己变强了,你觉得自己代表了正义,代表了上帝,代表了历史的车轮。为了这种快感,你愿意交出你的脑子。你会跟着人群一起吼叫,哪怕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吼什么。你会跟着人群一起砸车,哪怕那辆车是你邻居辛苦攒钱买的。在那个时刻,你不是邪恶的。你是被催眠的。
所以,勒庞得出了全书最著名、最让精英阶层点头如捣蒜、也让大众恨得牙痒痒的结论:“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注意,是“总是”。没有例外。为什么?难道大家聚在一起,脑细胞就集体缺氧死亡了吗?逻辑很简单:因为群体要行动,要达成共识,就必须“向下兼容”。想象一下,如果一群人要一起走路。这群人里有博尔特(飞人),也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请问,这个队伍的行进速度取决于谁?取决于博尔特吗?不,博尔特如果跑快了,队伍就散了,就不叫“群体”了。为了保持“群体”的完整,博尔特必须停下来,慢下来,在这个队伍里,他的速度只能等于老太太的速度。
智商也是一样。在群体里,爱因斯坦不能讲相对论,因为大家听不懂。苏格拉底不能讲辩证法,因为大家嫌烦。为了让几万人都能听懂,都能跟着喊口号,都能产生共鸣。所有的思想,都必须被简化、被阉割、被拉低到最低的那个水平。所以:群体不讲逻辑,只讲情绪;群体不看证据,只看画面;群体不求真相,只求痛快。当你走进那个狂热的人群,或者当你点开那个几千万人在线的直播间时。请记住勒庞的警告:你正在把你的智商存进门口的更衣室柜子里。从这一刻起,你就是一个没有脑子的细胞,你唯一的任务,就是跟着那个巨大的怪兽,一起蠕动,一起咆哮。那么,这个怪兽到底有多可怕?当几万个没脑子的细胞聚在一起时,它们会产生怎样惊人的破坏力?勒庞总结了“三道诅咒”。这三道诅咒,彻底封印了我们的人性,释放了我们的兽性。
02
群体的第一道诅咒:匿名性
朋友们,让我们先来做个诚实的心理测试。此时此刻,如果我给你一个按钮。只要按下这个按钮,你讨厌的那个上司就会立刻破产,或者那个每天半夜制造噪音的邻居就会立刻爆胎。并且——请注意,这是关键——没有任何人会知道是你干的,你也绝对不会受到任何法律或道德的惩罚。你会按吗?别急着回答“我不按,我有道德”。在你的内心深处,哪怕只有一毫秒,你犹豫了吗?
弗洛伊德早就告诉过我们: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头野兽(本我)。平时这头野兽为什么不出来咬人?不是因为它死了,也不是因为它被感化了。而是因为它被关起来了。关它的笼子,叫“法律”,叫“舆论”,叫“责任”。我们不敢裸奔,是因为怕“社死”。我们不敢打人,是因为怕坐牢,怕赔钱,怕留下案底。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我们是脆弱的,我们是透明的,我们时刻处于被监控、被审视的状态。这种“被抓住的恐惧”,是维持人类文明运转的唯一底线。但是,勒庞告诉我们:群体,是一把钥匙。一把打开笼子的万能钥匙。
当一个人融入了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时,发生了什么?勒庞写下了一句精准的判词:
“群体中的个人,仅凭数量上的优势,就会产生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感。”
(He gets a sentiment of invincible power which allows him to yield to instincts which, had he been alone, he would perforce have kept under restraint.)
想一想,当你一个人面对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时,你会瑟瑟发抖。你会算计:我打不过他,我会被抓。但当你身边站着十万人,大家都在怒吼,都在推搡,都在向前涌动时。你会觉得那个警察很渺小。你会觉得法律很遥远,甚至很可笑。你会觉得:“我们这么多人,难道还怕他不成?”“法不责众!这是历史的洪流!”这就是第一重幻觉:力量感。数量本身,就是一种烈性毒药。它能让一个平日里斤斤计较、唯唯诺诺的会计,瞬间觉得自己是斯巴达勇士。它能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瞬间觉得自己拥有了审判世界的权力。在这种力量感的灌注下,那头野兽开始撞击笼门了。
紧接着,是更可怕的第二重幻觉:免责感。勒庞一针见血地指出:
“群体是匿名的,因此也是不负责任的。”
(Crowds being anonymous, and in consequence irresponsible, the sentiment of responsibility which always controls individuals disappears entirely.)
在群体里,“我”消失了。既然没有了“我”,那谁来承担责任?没人。是“大家”干的,是“局势”干的,是“情绪”干的。反正不是“我”干的。你捡起一块石头,砸向那个无辜的窗户。作为“王小明”,你不敢。但作为“愤怒人群的一分子”,你敢。你的心里不会有任何愧疚。你会想:“所有人都在砸,我只是跟风而已。”“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我只是一片小雪花啊,我有什么罪?要抓你也抓不住我。”这种“责任感的彻底归零”,是释放人性之恶的最强催化剂。当一个人确信自己不需要为行为买单时,他内心的那个恶魔,那个原始人,就会立刻冲破牢笼。残暴、破坏、嗜血,这些在文明社会里被压抑了几千年的本能,会在一瞬间全部爆发。
现在,让我们把勒庞的理论,映射到2026年的互联网。勒庞当年的“广场”,今天变成了“屏幕”。勒庞当年的“人海”,今天变成了“数据”。互联网,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匿名暴君生产线”。看看那些在评论区里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别人去死的人。看看那些搞人肉搜索、把别人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挂在网上的人。他们在现实中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可能是写字楼里给老板端茶递水、唯唯诺诺的实习生。他们可能是回到家对老婆言听计从、不敢顶嘴的丈夫。他们可能是还在考研、连只鸡都不敢杀的大学生。
如果在现实中,你让他面对面,看着别人的眼睛,骂出一句脏话,他们都会脸红,都会结巴,都会害怕被打。但是,一旦连上了网,一旦披上了那个匿名的ID(面具)。笼子开了。他们发现:“我骂你,你打不着我。”“我毁了你,警察很难顺着网线抓到我。”“有几万人在跟我一起骂,我代表正义!我是网络法官!”于是,最懦弱的人,变成了最残暴的刽子手。最无能的人,变成了最高傲的审判官。勒庞说:“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但在群体里,他敢。在互联网上,他敢把一个活生生的人逼死,然后关掉电脑,心安理得地去吃一碗泡面,甚至还能睡个好觉。这就是群体的第一道诅咒:它赋予了你虚假的力量,剥夺了你真实的良知。它让你以为你是神,其实你只是变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暴徒。




03
群体的第二道诅咒:传染性
但是,朋友们。只有胆量还不够。这群暴徒现在只是敢动手了,但他们还没想好要干什么。要让这个群体真正动起来,要让他们像病毒一样扩散,还需要第二道诅咒。这道诅咒,能绕过你的大脑,直接控制你的神经。
有没有过这种经历?你一个人坐在家里看一部电影。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的理智在告诉你:这是假的,这是演员演的,背景是绿幕合成的,血浆是番茄酱。但是,当悲情的BGM响起来,当主角声嘶力竭地哭喊时。你的鼻子酸了,你的喉咙哽咽了,你的眼泪下来了。或者,你去过演唱会吗?去过球赛现场吗?哪怕你平时是个极度社恐、说话轻声细语的程序员。当周围几万人一起跺脚、一起嘶吼、一起挥舞荧光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控制不住自己。你的心跳在加速,你的头皮在发麻,一种莫名的电流从你的脊椎直冲天灵盖。你想跟着喊,你想跟着跳,如果你不照做,你会感到生理上的痛苦。
这是为什么?勒庞冷冷地告诉你:你病了。你被感染了。勒庞在书里用了一个非常医学化、非常不客气的词汇:传染(Contagion)。他认为,在群体中,情绪的传播方式,跟瘟疫、跟细菌没有任何区别。它不需要经过你的大脑皮层(理智区)审核。它直接绕过防火墙,击穿你的边缘系统(情绪区)。让我们看看勒庞的原话,这是他对人类独立性的死刑判决:
“在群体中,每一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让个人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In a crowd every sentiment and act is contagious, and contagious to such a degree that an individual readily sacrifices his personal interest to the collective interest.)
这是一种催眠。在传染的作用下,那个理性的“你”下线了。你变成了群体的一个共振器。别人哭,你也哭;别人怒,你也怒。你以为那是你自己的真实情感?别傻了。那只是病毒在你体内复制的结果。为什么勒庞对群体这么绝望?甚至到了鄙视的地步?因为他通过观察发现了一个可悲的定律:在群体之间,只有低级的情绪能传染,高级的逻辑是绝缘体。你可以试一试。你试图跟一个狂热的人群讲道理?“哎,大家冷静一下,根据《刑法》第几条,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件事的证据链……”有人听你的吗?根本没人听。甚至,你会被视为异类,被视为病毒的抗体,然后被群体当作敌人消灭掉。但是,如果你大喊一声:“是他们害了我们!弄死他们!不转不是中国人!”轰!全场沸腾。为什么?因为逻辑是冷的,情绪是热的。逻辑需要动脑子(高能耗),需要前置知识,需要冷静的各种条件。而情绪只需要动本能(低能耗),只需要你有杏仁核。病毒只会选择最容易传播的路径。所以,在乌合之众的乐园里:愤怒传播得最快;恐惧传播得第二快;仇恨传播得第三快。而理智?理智根本出不了门,它在门口就被踩死了。
勒庞写这本书的时候,传染还需要靠“在场”。大家必须挤在同一个广场上,闻着彼此的汗味,听着彼此的呼吸,看着彼此扭曲的脸,病毒才能跳跃。但是今天,2026年。互联网发明了“远程传染”。而且,我们还发明了一个上帝级别的病毒加速器——推荐算法。你打开手机,点开那些短视频软件。算法知道你喜欢看什么吗?不,算法其实不在乎你“喜欢”什么,也不在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真”的。算法只在乎一件事:什么东西能让你留下来。而什么东西最能留住人?情绪。极端的情绪。于是,你刷到了什么?背景音乐:要么是激昂的战歌,让你热血沸腾;要么是悲惨凄凉的二胡,让你泪流满面。音乐是情绪的第一催化剂。文案:震惊!气抖冷!男人看了沉默!女人看了流泪!如果不转就是不爱国!剪辑:快节奏,高冲突。不给你留下一秒钟思考的时间。
你以为你在看新闻?你以为你在了解世界?不,朋友们。你在嗑药。你在接受情绪病毒的定点投放。当你看到一条“某地发生打人事件”的视频,配上那种让人血脉卹张的音乐。你的第一反应不是“真相是什么?前因后果是什么?是不是断章取义?”你的第一反应是“怒”。手指比脑子快,你点赞了,你转发了,你在评论区骂娘了。恭喜你,你成为了传染链条上的下一个宿主。更可怕的是,这种传染会形成“回音室”。算法发现你喜欢“愤怒”,它就会给你推更多让你“愤怒”的东西。你关注的人,都是跟你一样愤怒的人。你所在的群,都是每天在骂街的群。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情绪病毒不断地折射、放大、变异。最后,你会产生一种幻觉:“全世界都是坏人。”“所有人都跟我想的一样。”“必须要来一场战争了。”这就是勒庞预言的“群体极化”。在传染的作用下,任何温和的、中立的观点都会消失。群体只会向着最极端的方向狂奔。要么是圣人,要么是恶魔。要么是神,要么是狗。没有中间地带。朋友们,看着你的手机屏幕。那个红色的点赞心形,那个转发按钮。在勒庞眼里,那不是社交工具。那是细菌的培养皿。每一次点击,都是一次病毒的复制。
04
群体的第三道诅咒:易受暗示性
现在,你有了胆量(匿名),你有了情绪(传染)。你已经是一头蓄势待发的野兽了,浑身充满了破坏的能量。但是,野兽往哪里冲呢?这需要一个指令。这就是群体的第三道诅咒——易受暗示性。为什么群体不需要证据?为什么谣言能杀人?
朋友们,我们来做一个残酷的思想实验。如果现在,有一个满脸横肉的陌生人跑到你面前,指着街对面一个正在买菜的老太太,对你说:“那个老太婆是个人贩子!她拐卖了三个孩子,还把孩子弄残疾了去乞讨!”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现代人,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的大脑会立刻启动一个程序:“真的吗?证据呢?”“报警了吗?警察怎么说?”“这人是谁?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和老太太有仇吗?”这是正常的思维流程:刺激 -> 接收 -> 判断 -> 反应。在这个链条里,“判断”是最关键的刹车片。它负责过滤谎言,负责核实真相,负责让你不变成一个傻子。
但是,勒庞告诉我们:一旦你进入了群体,或者你正处于那种狂热的“传染”状态中。这个“判断”的环节,被物理切除 了。你的思维链条瞬间退化成了爬行动物模式:刺激 -> 反应。这就是第三道诅咒:易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勒庞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心寒的描述:
“群体中的个人,就像沙堆里的一粒沙子,风可以随意把他吹向任何方向。”
(An individual in a crowd is a grain of sand amid other grains of sand, which the wind stirs up at will.)
他不再是自己行动的主人,他变成了自动木偶。这时候,如果有人喊一句:“那是人贩子!打死她!”群体会怎么样?群体立刻就会冲上去。没有一个人会问:“证据呢?”大家会直接拿起石头,拿起雨伞,甚至用牙齿,去攻击那个老太太。因为在那个瞬间,那个暗示(她是人贩子)直接绕过了大脑皮层,变成了绝对的真理,变成了不可抗拒的行动指令。
这解释了一个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为什么谣言在群体中跑得比真相快一万倍?为什么辟谣这么难?难到让人绝望?因为群体处于一种“集体催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群体失去了“检错能力”。他们分不清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想象。只要那个暗示足够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就会把幻觉当成现实。勒庞在书里举了一个极其经典的例子,我们可以称之为“海上幻觉”:一艘船上的船员,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天,绝望、饥渴,所有人都渴望看到陆地,或者看到救援船。突然,瞭望员喊了一声:“有船!那是救援船!”所有人——包括最老练的水手,甚至船长——都看到了那艘船。他们甚至看到了船上的国旗,看到了船员在挥手,听到了汽笛声。但实际上呢?哪怕那只是一块漂浮的烂木头,或者是海市蜃楼。因为“暗示”(太想看到船了)太强烈了,它直接修改了所有人的视觉神经。这就是集体幻觉。
映射到今天。为什么一个毫无根据的网贴,只要写得够煽动,就能让几千万人深信不疑?“某某明星吸毒!”“某某企业卖国!”群体不需要证据链。群体只需要一个鲜明的形象。只要这个暗示符合群体此刻的情绪(比如仇富、仇官、或者某种廉价的正义感),群体就会立刻吞下这个诱饵。哪怕第二天警察蓝底白字的通报出来了,说那是造谣。群体会道歉吗?绝不。群体会说:“那是洗地!”或者干脆假装没看见,一哄而散,去寻找下一个可以撕咬的猎物。在暗示的驱动下,群体永远是“正确”的,因为群体活在自己编织的幻觉里。
回想一下,这几年我们在互联网上经历过多少次“反转”?上午:全网疯传一段掐头去尾的视频,一个老师在打学生。暗示:“老师是坏蛋,学生是弱者。”反应:全网暴怒,人肉老师,打电话骚扰学校,高喊“师德败坏”。下午:完整视频出来了,是学生先拿刀捅老师,老师在自卫。新的暗示:“现在的孩子太坏了,老师太难了。”新的反应:全网立刻倒戈,同情老师,转头去骂那个学生和家长,甚至骂得比上午更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像什么?我们就勒庞笔下的那个“提线木偶”。那个发视频的人(操纵者),只要稍微拉动一下线(给出一个暗示),我们就往左跳;再拉一下线,我们就往右跳。我们自以为在主持正义。其实,我们只是在表演。我们在表演愤怒,表演同情,表演审判。而真正的真相,根本没人关心。因为对于被暗示控制的群体来说,真相不重要,爽才重要。
既然群体这么容易受暗示,那谁是那个下指令的人?勒庞冷冷地指向了那个站在高处的人——领袖。或者在今天,是那些大V、营销号、媒体操盘手。他们不需要懂逻辑,他们只需要懂“断言”。他们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他们只需要不断地重复一句简单、有力、煽动性的话。“他们是敌人!”“买它!不买就亏了!”“这就是真相!”当这句话重复一千遍,它就变成了真理。它就变成了植入你大脑的一段代码。当你下次看到相关的事物时,这段代码就会自动运行,你会不假思索地做出他们想要的反应。朋友们,这就是勒庞揭示的三重诅咒:匿名给了你作恶的胆量;传染给了你狂热的动力;暗示给了你盲目的方向。在这三股力量的夹击下,理性的“人”死了,疯狂的“乌合之众”诞生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既然群体这么蠢,为什么它还能存在?为什么它甚至能推动历史?我们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难道群体就没有一点智慧吗?勒庞笑了。他要用一个更残酷的物理学定律,粉碎你的这个幻想。
05
群体的“智力减法定律”
朋友们,我们中国有一句流传了千年的老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话听起来很励志,很民主,很符合我们对“集体智慧”的向往。我们总觉得:一个人的脑子不够用,那就十个人想;十个人不够,那就一万个人想。把大家的智慧加在一起,取长补短,总能得出最优解吧?勒庞如果听懂了这句中文,他会直接把桌子掀了。他会指着你的鼻子说:“放屁。”“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不仅顶不了诸葛亮,他们连三个臭皮匠都顶不了。他们会变成三个只会扔烂泥的疯子。”在《乌合之众》里,勒庞提出了一个残酷的“智力减法定律”:
“在群体中,累加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
(In crowds it is stupidity and not mother-wit that is accumulated.)
这意味着,群体的数学公式不是 1+1=2,而是 1+1 < 1。如果你把一万个平庸的人聚在一起,你得到的不是一个“超级大脑”,而是一个巨大的、蠕动的单细胞生物。
为什么?难道大家聚在一起,脑细胞就集体自杀了吗?不是脑细胞死了,是标准降了。让我给你们讲一个通俗的“最大公约数”原理。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个微信群。群里有爱因斯坦(智商160),有毕加索(艺术天才),有你的中学班主任(普通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没上过学、满口脏话的流氓(智商80)。如果这个群要“团结”,要达成“共识”,要一起行动。他们能聊什么?爱因斯坦发一条:“我觉得引力波的方程还需要修正。”流氓说:“啥玩意儿?听不懂。滚。”毕加索发一条:“我觉得立体主义解构了空间。”中学老师说:“这也叫画?乱七八糟的。”为了不让群解散,为了让流氓也能听懂,也能跟着点赞,也能参与讨论。爱因斯坦闭嘴了,毕加索闭嘴了。大家只能聊什么?只能聊:“隔壁村那个寡妇真骚。”或者:“那家店太黑了,咱们去砸了它!”看明白了吗?在群体里,智商必须“向下兼容”。为了照顾那个最笨、最情绪化、最没有逻辑的人,所有的高智商者都必须自我阉割,把自己的思维拉低到地板的水平。
所以,勒庞告诉我们:群体不求平均分。群体的智商,永远等于那个“下限”的智商。这就是为什么一群教授开会讨论出来的结果,往往比不过一个普通人拍脑门的决定。因为在那个会议室里,他们不是教授,他们是“群体”。为了达成一致,他们牺牲了智慧,选择了平庸。勒庞甚至把这个矛头,直接对准了“投票”。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但勒庞不在乎。他写道:
“四十个院士的投票结果,并不比四十个挑水工的高明多少。”
( The decisions of general interest come to by an assembly of men of distinction, but specialists in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are not sensibly superior to the decisions that would be adopted by a gathering of imbeciles.)
为什么?因为当面对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通货膨胀、外交政策、税收改革)时。院士和挑水工一样,都是无知的。他们都被情绪左右,都被媒体的暗示控制,都只看得到眼前的利益。在群体决策中,专业知识是无效的。因为专业知识太枯燥、太复杂、太反直觉。群体听不进去。群体只听得进去口号。你讲“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导致长期通胀”,没人投你,因为听不懂。你讲“给每个人发一万块钱!把富人的钱分了!”,全场欢呼,票全是你的。所以,勒庞得出了那个让精英阶层绝望的结论:“文明是由少数智力超群的个人创造的。而群体,只负责把这些文明拉平,甚至摧毁。”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因为某个人(牛顿、达芬奇、拿破仑)跳出了群体,独自思考的结果。而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倒退,往往都是因为群体发了疯,把这些异类给烧死了。
现在,把这个定律放到互联网上。互联网是不是让我们的智慧增加了?理论上是,因为知识获取变容易了。但在社交媒体的层面上,它让“降智”变得更彻底了。为什么现在的短视频越来越弱智?为什么现在的文章越来越情绪化?因为流量就是群体的投票。而群体喜欢什么?群体喜欢简单,喜欢粗暴,喜欢不动脑子。如果你想火,你就不能讲逻辑。你必须把世界简化成“好人 vs 坏人”。你必须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成“男人 vs 女人”或者“穷人 vs 富人”。这是一种“智力逆淘汰”。在互联网这个巨大的“降智乐园”里:理性的声音被淹没,因为它不够刺激,大家直接划走;深刻的思考被无视,因为它太费脑子,大家看不下去;只有最愚蠢、最极端、最煽情的垃圾,才能飘在水面上,被几千万人传阅。勒庞要是看到今天的抖音和推特,他一定会冷笑一声:“看,我早就说了。给他们自由,他们只会选择平庸。”
06
群体的“图像思维”与生存法则
我们是匿名的暴徒(第一道诅咒)。我们是情绪的宿主(第二道诅咒)。我们是暗示的傀儡(第三道诅咒)。我们的智商已经被拉到了地板上(降智物理学)。这听起来很绝望,对吧?在这个疯人院里,我们还有救吗?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浑浊的泥潭里,保留哪怕一丝丝的清醒?勒庞虽然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密码。
朋友们,如果你想说服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会列数据,讲道理,摆事实,用严密的三段论推导出一个无懈可击的结论。但是,如果你想说服一群人呢?勒庞告诉你:把你的逻辑扔进垃圾桶吧。在群体面前,逻辑不仅是无用的,甚至,它是有害的。因为群体听不懂。群体的大脑构造,决定了它们只能处理一种东西:形象(Images)。勒庞写道:
“群体只通过形象思维思考。一个形象会唤起另一个形象,二者之间没有任何逻辑联系。”
(A crowd thinks in images, and the image itself immediately calls up a series of other images, having no log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first.)
什么意思?就是说,群体的脑子是一台幻灯机。你给他放一张片子(暗示),他就看到一张片子。你不能跟他说:“因为A,所以B,虽然C,但是D。”群体没有内存处理这么复杂的链条。你得直接把B拍在他脸上。举个例子:如果你想告诉大家“通货膨胀很严重”。理性的做法:拿出CPI指数图表,分析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曲线,引用经济学家的论文。群体的反应:划走,无聊,看不懂,你在装什么?勒庞的做法:拍一张照片——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大爷,在冬天的风雪里,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对着空荡荡的米缸流泪。群体的反应:炸了!“万恶的资本!” “政府在干什么!” “我们要活不下去了!” “抢米去!”看到了吗?那张照片可能是个案,甚至是摆拍。那个大爷可能根本就不是因为通胀哭。但对于群体来说,那就是真理。画面产生的幻觉,比一百万份详实的数据报告都要真实,都要有力。
所以,在这个时代,谁掌握了“制造画面”的能力,谁就是群体的上帝。看看那些顶级的营销号,看看那些带货的主播,看看那些煽动民粹的政客。他们从来不跟你讲逻辑。他们只做一件事:造梦(或者造噩梦)。卖课的:不会告诉你成功的概率只有0.01%。他会直接给你看一张图——他在迪拜开豪车,他在海边喝香槟,他在数钱。哪怕那车是租的,但那个画面直接击穿了你的贪婪。搞对立的:不会跟你分析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他会给你讲一个故事——“我的闺蜜被渣男骗得倾家荡产跳楼了”。哪怕那是编的,但那个惨烈的形象直接点燃了你的愤怒。勒庞说了一句极其深刻的话:
“谁能给群体提供幻觉,谁就能轻易成为他们的主人;谁试图打破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Whoever can supply them with illusions is easily their master; whoever attempts to destroy their illusions is always their victim.)
你试图做一个清醒的人?你试图跑过去说:“嘿,大家冷静点,那个豪车是租的,那个故事是编的,数据不支持你们的结论……”你会是什么下场?你会成为公敌。因为你打破了群体的美梦,你破坏了他们情绪发泄的快感。他们不会感谢你的真相,他们会把你撕碎。
好了,朋友们。第一集讲到这里,我们的“尸检报告”已经做完了。我们看清了那个名叫“群体”的怪兽:它由数量堆积而成,赋予你虚假的力量(匿名)。它靠情绪像病毒一样传播(传染)。它被暗示像木偶一样操控(易受暗示)。它的智商只有地板水平(降智)。它只相信画面,不相信逻辑(图像思维)。承认吧。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巨大的、喧嚣的、没有脑子的“降智乐园”里。只要我们还拿着手机,只要我们还活在社会中,我们就无法彻底逃离。
那么,还有救吗?作为一个不想变成丧尸的个体,我们该怎么办?在此,我送给大家三条“勒庞式生存法则”。这是我在无数次被网暴、被情绪裹挟后,总结出的防身术。
法则一:让子弹飞一会儿(Delay)。当你在网上看到任何让你瞬间热血沸腾、或者瞬间气炸了肺的信息时。切断你的手指。(这是比喻,别真切)千万不要点赞,千万不要转发,千万不要评论。告诉自己:“我有病。我现在被感染了。我的大脑皮层正在被情绪强奸。”给自己24小时。勒庞说了,群体是冲动的。对抗冲动唯一的办法,就是时间。你会发现,99%的热点新闻,在24小时后都会反转,或者变得索然无味。延迟反应,是你智商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法则二:警惕“爽感”(Skepticism)。如果一个观点、一篇文章、一个视频,让你看得特别爽。它完美地印证了你的偏见,它帮你骂了你想骂的人,它让你觉得“对!就是这样!我是正义的!”警惕!这时候,你大概率已经吞下了别人喂给你的幻觉胶囊。真相通常是复杂的、灰色的、让人不舒服的。爽,是因为你的智商被降维打击了。当你感到爽的时候,问自己一句:“是不是有人在试图操控我?”
法则三:精神上的“离线”(Solitude)。勒庞悲观地认为,只要在群体里,人就没救了。所以,唯一的解药是——孤独。不是让你去深山老林里当野人。而是要在精神上建立一个“隔离区”。每天留出一段时间,关掉手机,断开网络。去读书,去发呆,去跟一个具体的人面对面聊天。在这个“离线”的时刻,那个被群体熔断的“自觉人格”,那个理性的“你”,才会慢慢复活。在乌合之众的时代,孤独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特权。那是强者独享的清醒。
但是,朋友们。知道自己是怎么疯的,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问题是:是谁在让我们发疯?是谁在制造那些暗示?是谁在编写那些病毒?是谁站在高处,看着我们在泥潭里厮杀,然后数着手里的钞票和选票?勒庞把那些人称为——领袖。在下一集,我们将进入《乌合之众》最黑暗、也是最实用的篇章。我们将揭秘那些大独裁者、大教主、大网红手中的“洗脑手册”。你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把你变成信徒的吗?你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把一句谎言变成真理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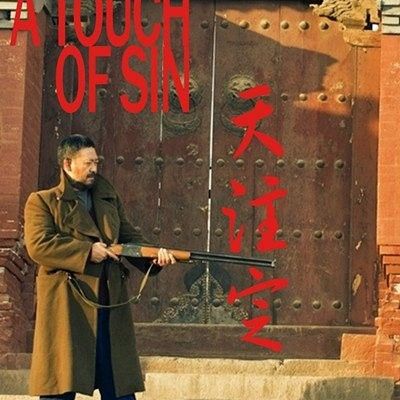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