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模拟生活月:放弃智能手机会让我更健康、更快乐,还是压力更大?
当我用诺基亚手机、随身听、胶片相机和纸质地图替换掉我的iPhone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的生活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艾玛·罗素
2026年1月21日

最近,两个蒙面男子骑着摩托车冲上人行道想抢劫我,我却浑然不觉。我的目光紧紧盯着手机上的短信,双手也攥得紧紧的,他们甚至都没来得及抢。直到一位老妇人尖叫一声,我才感觉到摩托车冲回马路上的呼啸声,这才抬起头来。他们或许没得逞,但这却让我开始思考:我究竟错过了周围真实世界的哪些方面?
早上还没来得及倒第一杯咖啡,我已经浏览了Instagram上陌生人的生活动态,看了新闻头条,回复了短信,在约会软件上滑动浏览了一些匹配对象,还刷新了两次邮件。我用苹果地图查看上班最快的路线。通常我都错过了公交车,所以就用Lime app租了一辆共享单车。白天,我哥给我发了一些表情包,我拍了一张运河船的照片,然后用Apple Pay付了午饭钱。我一边听着Spotify上的音乐,一边听着朋友发来的长语音留言,然后一边看一部不知名的电视剧,一边在Depop和Vinted上浏览服。
我随时都能联系到,没有个人界限,而且我的注意力早已消失殆尽。自2007年第一代iPhone问世以来,智能手机已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国人平均每天上网4小时20分钟。“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让我们得以接触到一个几乎免费的、无限延伸的数字毒品世界,”《多巴胺国度》的作者安娜·伦布克说道。“算法会根据每个人的独特大脑定制体验,使其具有很强的强化作用,同时在无限滚动中注入足够的新鲜感,以克服厌倦和耐受性。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让我们在不想继续浏览的时候,仍然忍不住点击和滑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产生耐受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更强效的刺激才能获得同样效果果。”
屏幕使用时间的增加与抑郁、焦虑和睡眠质量下降有关。但在高科技时代,我们真的可以过上低科技的生活吗?我尝试了一个月:用诺基亚手机代替我的iPhone,诺基亚只能用来发短信、打电话和玩贪吃蛇;我还用随身听和胶片相机。我开始阅读纸质书籍、报纸和杂志;我用伦敦地图册导航;我翻找我的实体银行卡,或者尽量使用现金。唯一例外的是工作时间,朝九晚五我用笔记本电脑回复邮件写作。
第一天
“你看起来就像个装腔作势的潮人,”我的室友本在我摆弄新设备时说道。他说得没错。我把随身听留在了家里,但包里装着书、记事本、AZ(可能是指某种电子设备或软件)和钱包,还是比平时重了些。我还没从新家坐过公交车上班,所以就跟着手绘的地图找到车站,然后跑去赶公交车。我傻乎乎地没记下公交车号,但这个号码听起来很耳熟。两个友好的陌生人告诉我,这不是我要坐的那趟车,不过我可以在Angel换乘另一趟。“我们已经把记忆外包给了手机,”《数字疯狂》的作者、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前心理学助理临床教授尼古拉斯·卡达拉斯说道,“不幸的是,科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感,恰恰意味着我们的人类技能正在退化。不用则废。”
公交车开得很慢。平时我肯定会改走别的路线。我试着回复朋友的信息,但要按好几次才能输入想要的字母,实在太麻烦了。“真累,”我结结巴巴地说。剩下的路程我都在看书。
第3天
午休时,我和姐姐去公园散步。她离开去再走一圈后,我突然很想看看Instagram和邮件,但只收到零星的短信。我渴望和朋友们在WhatsApp上聊天,听他们分享一天中的趣事。我感觉有点心神不宁,但还是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树叶的变色上。一些平时根本没时间浮现的念头涌上心头。真是令人焦虑。
下班后,我去ICA看萨克斯演奏家cktrl的演出。我有点担心没法用Dice app取票,但最后还是出示了护照。平时我肯定会加入人群,拍一两首歌,然后上传一些模糊不清、音质很差的视频到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玩得很开心。但这次不行,所以我只能心无旁骛地欣赏他的演奏。突然,身后一束手电筒的光束照过来,原来有人在拍一整首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做那种烦人的人了。
第6天
我的数码戒断开始让我的朋友们感到焦虑了。妮可终于联系上我了,她说:“我讨厌你那破手机。”她一直在发短信,但没意识到要按两次才能以短信而不是iMessage的形式发送。另一个朋友想分享她的约会故事,发短信说:“天哪,现在不能用语音留言真是太糟糕了。”还有,当房东发信息让我们用WhatsApp发送新地毯的照片时,我却发不了,本发短信说:“你这个月肯定会给我添麻烦。”
晚上,我的约会对象发给我一个酒吧地址,约我“在那儿见面”。我预留了充足的时间来辨认那小小的字体,并找到路。他迟到了,所以我坐在酒吧的壁炉旁看书。我看起来像是在等着别人来搭讪。他到了之后,教我怎么打开预测文本功能,这真是让我疲惫的拇指松了一口气。
第8天
午饭时分,我打开电视,看了《逃离都市》这档节目,了解了赫里福德郡的房地产市场。我想给自己做顿丰盛的晚餐——既当晚餐,也当消遣。但到了超市,我才想起手机上查不到菜谱,只好买了番茄意面。

第9天
我的室友在慈善商店给我淘到了一张妮娜·西蒙的CD。我试着用随身听播放,却发现没电了。午休时我去买了几节电池(谁知道电池居然有这么多尺寸?),然后一边听着CD一边从办公室走回家。Spotify上数以亿计的歌曲让人眼花缭乱,所以摆脱选择的束缚,专注于专辑本身,而不是被随机播放模式打乱节奏,感觉真好。罗莎娜·欧文在爱尔兰经营着一家名为Samsú的“数字排毒小屋”连锁店,她深知模拟聆听的重要性:她会给客人留下她和父亲一起录制的磁带。在科技行业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导致身心俱疲之后——先是在Meta公司,后来又在一家气候科技公司——她于2023年和丈夫一起去了丹麦的萨姆索岛,在信号不太好的岛上和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我的精神状态很差,”她说。“我花了很多时间上网,这次在岛上意外地进行了一次数字排毒,回来后感觉精神焕发。”她推荐为期三天的静修。“大量科学研究表明,在大自然中待上大约72小时,真正的奇迹就开始发生了。”
第12天
我在沃克斯豪尔车站和朋友碰面,然后我们一起去咖啡馆吃早餐,之后去了泰特英国美术馆。卡米拉很少上网:她是一名医生,没有社交媒体账号。她很少回复短信,可能是我认识的最快乐的人之一。但她说她总是因为没有早点回复而感到内疚,她讨厌手机就像房间里永远存在的一个人,让你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与身边朋友的相处中。这种感受引起了我的共鸣;我们都渴望更加随性自在。
受我们谈话的启发,我给住在不远的阿克里蒂打了电话。我见到了她和她的两个朋友,我们一起吃了馅饼。回家的路上,我不得不向站台上唯一的男士求助。地上铁还有24分钟才到,所以我琢磨着有没有更快的路线。结果没有,我只好在露天车站瑟瑟发抖,真希望当时能叫辆优步。
第13天
我到达加拿大水镇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我不想弄脏我的AZ导航仪去找罗瑟希德街。我知道五月花酒吧就在河边,于是问了便利店里的一个男人该怎么走。我到得早,便眯着眼睛在烛光摇曳的酒吧里看书,感觉自己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酒吧里有个很搞笑的服务员,正在讲他在Grindr上的约会故事,比我的书有趣多了。这种不用科技的感觉让我变得有点爱管闲事。我用现金付了烤肉的钱,现在感觉有点假,好像在玩游戏一样。然后我和朋友去了电影院——伦敦市中心的Picturehouse,因为它正好在我们俩住的地方中间。他们收了我们20英镑的票价,如果出发前知道要这么贵,我肯定不会买。我气得直冒烟,不过还好电影不错。
第14天
我得给银行打电话。我的室友把房租转到了我的Monzo账户,这个账户只能通过App访问。结果我收到一条短信,说我的账户透支了。早上到地铁站的时候,我的Oyster卡余额不足,只好充值,结果错过了火车——平时我都会用Apple Pay支付。我只好等了八分钟才坐上下一班。等我到了办公室,已经慌乱不堪,而且因为没法查看账户余额或者在账户之间转账而感到焦虑。
第18天
我的火车上有一群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旅行。老师为了让他们不觉得无聊,让他们玩起了词语联想游戏。“我说‘面包’,”她说,“你可以说‘三明治’。我们来试试。”“学校,”老师又说。“监狱!”一个孩子大声回应。到达诺丁山后,我在车站仔细研究了地图,确保从正确的出口出来。我记住了几个重要的地标,这样就知道该往哪走——盖特电影院就在我要去的那条路旁边,那就是阿克斯布里奇街。我迟到了,没时间犯错,于是开始快速地沿着街道走,仔细查看每一家餐馆,直到找到我要找的那家巴勒斯坦咖啡馆。
第21天
实验开始时,我担心迷路,也担心无法和朋友联系,但现在这些担忧似乎都减轻了。我更平静了,和别人在一起时也更专注。早上通勤时,我环顾四周,发现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人都低头盯着手机。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既没戴耳机,也没带手机或书。我尽量不去看他,因为我担心自己刚才一直在盯着他看。下班后,我和朋友纳维德约好见面,气氛就没那么轻松了。我们没能约好见面地点,他很沮丧,因为他发不了链接给我:“你这个原始人,赶紧用回WhatsApp!”他迟到了,所以我在车站外等了45分钟。他来了,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知道我有点不耐烦,但我还是报复了他,让他听了两个小时的实验爵士乐。

艾玛用她的iPhone换了一台胶片相机。
第23天
下班后,我去看望我的朋友斯嘉丽,她被一只柯基幼犬“囚禁”了。我到达伦敦东南部时,天色已黑,空气潮湿,但我已经尽可能仔细地写下了去她家的路线。我的包太重,所以没带导航仪,但我确信这十分钟的路程我肯定不会走错。我给妈妈打电话,我们闲聊了二十分钟,我才意识到我没看到路口。情急之下,我让她用谷歌地图帮我定位,这显然是作弊,但我现在迟到了,而且身处一片墓地之中。我完全走错了路,她只好给我描述路线。
第27天
这个周末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只想好好放松一下。我步行去上瑜伽课,然后出去散散步。一边走一边听着我唯一的那张CD,这时我约会的对象打来电话,他刚下班。我们想找个桌游玩,但附近的慈善商店都没找到,于是就买了些报纸杂志和烤鸡的食材。然后我们像老古董一样,窝在沙发上听音乐、看书。感觉就像退休了一样。
第30天
我终于抽出时间给银行打电话交房租了,这还是我第一次逾期。我一直拖着没打这通不可避免的20分钟电话,因为这意味着我要念一大堆银行代码、账号,还要拼写房东的名字,以及我欠钱的那些朋友的名字。在没亲眼核对信息的情况下转账,感觉很不自在,而且电话那头的女人一直跟我说网上操作会方便得多。
第31天
尽管这个月令人沮丧,但实验结束还是让我感到难过。我感觉离线生活会给别人带来不便:如果我们想找地方吃饭或去酒吧,都得靠他们,他们得负责地图,而我却没法叫优步。但我更快乐、更平静了——摆脱了无休止的刷手机、等待回复短信以及时刻与人交流的需要。大约一周后,我不再会去拿手机,而且有耐心阅读。晚上不用查看工作邮件的感觉真好。我决心删除那些让我分心的主要平台:Depop、Hinge 和 Instagram。在慈善商店淘衣服更有成就感;没有干扰的约会也轻松多了;而且我可以不用看那些失败的肉毒杆菌注射和人工智能动物的视频了。“大型科技平台并非偶然让人上瘾,而是有意为之,”卡达拉斯说道。 “他们通过瞄准弱势群体来推销产品:如果算法检测到某个年轻人有身材焦虑、自残或抑郁倾向,就会向他们推送大量相关内容,加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在我离开的最后一天,我收到斯嘉丽的邮件:“我在浴缸里听莉莉·艾伦的专辑时,不小心把手机溅到水里了,现在手机没了,我真想学你。” 看来,渴望断网的不止我一个。
My analogue month: would ditching my smartphone make me healthier, happier – or more stressed?
When I swapped my iPhone for a Nokia, Walkman, film camera and physical map, I wasn’t sure what to expect. But my life soon started to change
Emma Russell
Wed 21 Jan 2026 00.00 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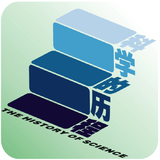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