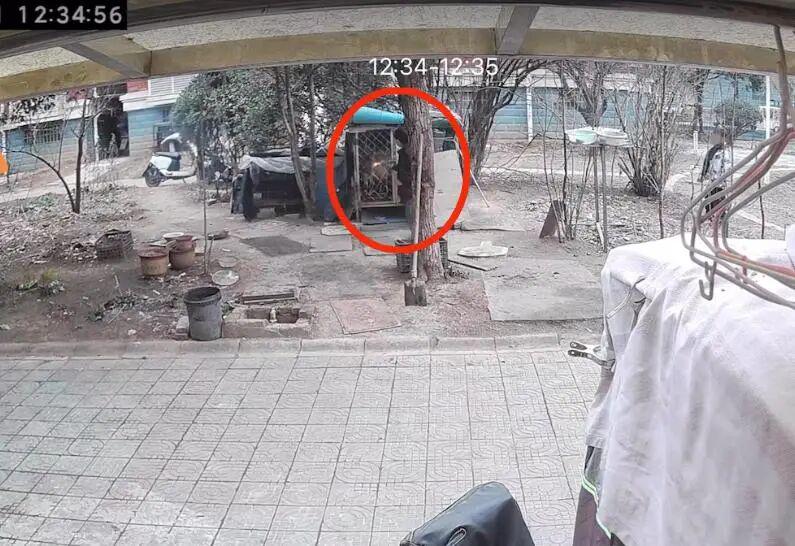我一直以为,儿子结婚,只是家里多了一张碗,多一个人说话。后来才明白,是我被悄悄挪出了原来的位置。
他结婚那天,我坐在酒席最角落的一桌。不是没人安排,是我自己坐过去的。新娘那边亲戚多,热闹,笑声一阵一阵。我不想显得多余。有人来敬酒,叫我“阿姨”,我纠正了一次,说我是他妈妈。对方愣了一下,笑着说,不好意思。我也笑,说没事。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从那天起,我的身份要靠自己提醒。

婚后他们很快搬走,说是离单位近。我理解,年轻人要空间。我没拦,也没多问。只是逢年过节,他们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以前他下班会给我打电话,问吃什么,现在多半是我打过去,电话那头总有人声,锅碗瓢盆,或者他压低声音,说在忙,晚点再说。后来连“晚点”也省了。
我开始学会不打电话。
有一次,我去他们家送点自家腌的菜。敲门,等了很久。门开了,是儿媳,穿着睡衣,看见我,明显愣了一下。她很快笑,说怎么不提前说。我说顺路。屋里很整洁,像样板间,沙发上没有我的位置。我站了一会儿,把菜放下,说不打扰了。她送我到门口,客气而疏远。
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也是这样对待婆婆的。不是刻意冷淡,只是忙,只是觉得她不懂我的生活。那时我心安理得。
真正让我醒过来的,是那次住院。
那天早上我起床,觉得胸口闷,像压了块石头。我以为是没睡好,洗了把脸,还是不对。等我意识到不对劲时,人已经站不稳了。我给儿子打电话,响了很久才接。他说在开会,让我先去医院。我说我一个人。他沉默了一下,说那你先打车。
我坐在急诊走廊,灯白得刺眼。医生问有没有家属,我摇头。填表的时候,联系人那一栏空着,护士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我突然觉得羞愧,好像这空白是我的失职。
下午他来了,穿着衬衫,脸上是赶路的疲惫。他站在床边,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他点头,说那就好。我们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沉默。后来他说,晚上可能来不了,孩子那边没人看。我说理解。
他说“孩子”,指的是他的孩子。
住院的三天里,他来过两次,每次不超过二十分钟。儿媳一次都没来。我不怪她。她没这个义务。我怪的是我自己,还在等一个不存在的角色。
第三天晚上,我一个人输液,旁边床位的老太太儿女轮流守着。她吃不完的水果分给我,问我孩子怎么不来。我说忙。她叹气,说现在都这样。我笑了笑,没有接话。
出院那天,我自己办的手续。医生交代注意事项,我点头,全记在心里。走出医院,阳光很亮,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轻松感。像是终于不用再假装期待。
回家后,我把他们给我买的钥匙放进抽屉,没有再用过。我开始安排自己的生活,体检、旅行、报班,日子被填满,反而踏实。儿子偶尔打电话,我也不再追问生活细节,只说我很好。
有一次他在电话那头说,妈,你怎么最近都不找我。我愣了一下,说,你忙,我不想打扰。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等我有空带孩子回来看你。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窗前,心里很平静。我突然明白,亲情不是消失了,而是换了一种形态。它不再以我为中心,也不再需要我随时待命。
我不再把他当作唯一的依靠。他有他的家庭,我有我的余生。那次住院让我看清的,不是他的薄情,而是现实的边界。母子一场,不是终身捆绑,而是陪走一段。
这样想的时候,我反而不再怨了。人到这个年纪,能看清位置,是一种迟到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