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人生大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婚姻又往往是很现实的事情,它不可避免地与地位、财富沾边挂钩。
朱俊芳,1957年9月出生在河南商丘,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兄弟四人,家里太贫穷了,作为长子的朱俊芳才读了两年的小学,就被迫辍学回到家里帮助父亲务农。
“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地打一辈子交道,这是几千年来原生农民家庭子弟的宿命,他们的人生轨迹往往是“到了年龄娶妻生子,拉扯孩子长大,再繁衍下一代”。
16岁那一年,朱俊芳也到了订婚的年纪,村里的热心老大妈给他介绍了一位邻村的姑娘,父母见过后感觉很好,就咬着牙四处借钱,凑了份彩礼,连同不少新衣服,一并送到了姑娘家里。
这婚事就算是订了下来,只不过从始至终,两个年轻人也没有见过面,更别提互相窜门了。
转眼之间,三年过去了,朱俊芳要正式迎娶那位姑娘了。这个时候,对方说是要到朱家瞧瞧,看看这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那位未过门的姑娘来到老朱家,看到了令她十分胆寒的景象:破败的院墙,四间土坯小房,看上去都摇摇欲坠,屋里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就连床都是用砖头木板搭起来的。
朱俊芳的父母显得特别苍老,而那三个弟弟,竟然还未成年,流着鼻涕,穿得也是破破烂烂。
姑娘越看心越凉,礼貌地应付了几句,头也不回地逃回家,很快就让娘家把彩礼退了回来。
这门婚事儿啊,告吹了。
眼瞅着儿媳妇儿即将过门了,忽然之间又跑了,这种事情令朱父感觉异常耻辱,气血郁积,难以开解,竟撒手人寰,随后,朱母也病倒了。
怎么办呢?朱俊芳知道如果还是守着这份“一亩三分地”的庄稼,他们还是没有啥出路,他只好忍痛把母亲交给三个弟弟暂时照顾着,自己则出门找生路。
长这么大,朱俊芳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他走走停停,啃着干粮、喝着凉水,一路打听哪里有活计,在500里之外的济源,他找到了一个煤矿,毫不犹豫地加入招工队伍,成为一名矿工,在这里他干了六年。
1982年,朱俊芳又来到焦作矿务局冯营矿,继续当矿工。
出身贫寒的朱俊芳,特别珍惜当矿工的工作机会,不管是在哪个煤矿工作,他都踏踏实实吃苦耐劳,还特别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说“朱俊芳这个小伙儿真不错”。
1984年3月,班长王好义对朱俊芳说:
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媳妇了,如果实在找不到,咱们可以在杂志上征婚啊。
27岁的朱俊芳听了这番话,十分羞涩,他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王好义二话不说,拉着朱俊芳就来到照相馆,拍了照片,在咨询杂志社同意后,又提笔帮助他写了征婚启事内容,并附上100元钱,一块寄给了杂志。
这份征婚启事很快就被杂志发表出来,内容如下:
我是一个煤矿工人,今年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有房数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

这则征婚启事在今天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37年前,征婚可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儿,彼时改革开放还没有几年,中国大地人们的思想还相对保守。
“朱俊芳到杂志上征婚”这件事儿,在煤矿上也引起轰动,大家都很好奇是什么促使朱俊芳这么大胆,而作为当事人的朱俊芳在征婚启事发出去之后,还是平静地生活,下井干活、吃饭睡觉,似乎这件事儿没有发生过,因为他认为征婚这事儿不会有啥效果。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才过了几天,他就陆陆续续地收到应征的来信,这些信来自四面八方,有陕西的,有东北的,有湖南的,有四川的,更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姑娘回信。
一封封的信逐渐累加起来,装了两个黑色提包那么多,朱俊芳感到手足无措,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信,也不知道究竟与哪位姑娘交往。
正当他犹豫不决之时,有一位来自东北的姑娘李萍,竟然登门前来找他。
1984年6月的一个午后,也就是征婚启事发出去1个多月的时候,有工友转给朱俊芳一封信,班长王好义给他念完,朱俊芳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朱俊芳,你好!你的征婚启事我已看到,我现在已从东北来到焦作,住在某某招待所302房间。你如有空,请明天上午到招待所,咱俩面谈。
这姑娘可真是够大胆的,别说在当时,就是现在来说,也是吓人一跳。
朱俊芳犹豫再三,还是叫上班长陪他一起去。两人见面后,李萍有些失望,征婚启事上的朱俊芳还挺年轻英俊的,可面前这位个头不高,长相还老气,这是同一个人嘛?
见面后,朱俊芳才知道李萍并非是直接奔着他来的,这位黑龙江克山师专毕业的大学生,比朱俊芳小6岁,她的父亲是传统的老观念,不允许她自由恋爱,而是自己出面给女儿张罗找对象。
李萍不同意父亲的做法,被父亲扇了一巴掌,一气之下,她带上60多块钱,离开泰康县老家,离家出走了。
她先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工作也没处找,又不愿意回家被强迫相亲。
忽然李萍想起杂志上的那则征婚启事,她想自己既然想自由恋爱,那么就要胆子大一些,勇敢地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于是她按照地址来到焦作冯营矿,但毕竟是姑娘家,还是很害羞,她就写了一封短信,托工友带给朱俊芳。
两个人见面后,李萍有些失望,朱俊芳却心跳如兔,眼前这位姑娘如此俊俏,还有文化,自己能配上人家吗?
你如果愿意就留下,不愿意就送你回家。
沉默了好长时间,朱俊芳才憋出这一句话。李萍在失望之后,转念一想,“人不可貌相”,也许这个小伙儿是个好人呢,不如交往几天再说。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李萍对朱俊芳的印象彻底转变,她认定这个小伙子就是自己托付终身的人。她看到朱俊芳自己啃着凉馒头,就着咸菜,而把食堂买来的鸡腿、鱼省下来,留给她吃,在公园游玩的时候,也总是关心照顾着她。
李萍的母亲、堂姐得到她的消息后,连夜从东北赶来,痛哭之后,劝李萍回家,可是她却流着泪拒绝了,把母亲、堂姐送走。
同年10月1日国庆节,朱俊芳与李萍参加了矿上的集体婚礼,他们给自己的小屋置办了简单的家具,还有一套锅碗瓢勺。

冯营矿作为国有企业,比较注重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李萍是外地人,矿上出面安排她去矿职工子弟学校当音乐教师,两个人相濡以沫地生活着,第二年,儿子朱强出生了,给朱俊芳更大的生活动力,工作也更加积极。
煤矿工作,总有一些意外事故出现,每一次上班之前,李萍都要不厌其烦地叮嘱丈夫要注意安全,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她独自承担了照看儿子和打理家务的重担。
朱家被评为矿、集团公司的“五好家庭”,李萍个人还被评为“女工家属安全先进个人”,多次参加表彰大会。1999年,北京多家媒体在进行评选后,认为朱俊芳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征婚第一人”。
2003年,18岁的儿子朱强考上大学,立志做一名电脑工程师,可是天降厄运,大三时,他身体突感不适,被确诊为“肾病综合征”。
朱俊芳是合同制矿工,每月全部收入1000元左右,李萍的工资也是1000元左右。为了筹措医药费,他们两口子东挪西借,更是把房子卖掉凑钱给儿子治病。
短短几年的功夫,家庭就欠债数十万元,好在换肾之后,朱强的病情还比较稳定。
回顾过去的岁月,朱俊芳总是觉得对不起妻子,跟着自己太委屈了,自己是小学二年级文化,为人又内向,不善于与人沟通,而妻子是大学生,还能歌善舞,两个人缺少共同语言。
李萍呢,有时候也在想自己当初是有些任性和冲动,年轻不懂事,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情绪去做事儿,在他们结婚的最初几年,她倒没有后悔的想法,但经过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面对儿子的病情,她的情绪出现波动。
不过这种波动也只是暂时的,既然当初自己选择了这个男人,选择与他组建这个家庭,这辈子就要相亲相爱,共度人生,无论贫贱灾祸,都要共同去面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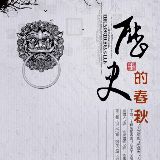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