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一鸣
近日有关清拆旧霓虹灯广告的新闻引起关注,有网民强烈反对清拆霓虹灯广告牌,声称此举等于拆“香港的招牌”。潮流兴怀旧重视保育,但维度要如何设定才合适?城市要发展,部分旧广告牌有安全隐患,确有必要清拆,政府应尽量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不过,说到霓虹灯广告是“香港的招牌”,老一辈上海人未必同意,可能会觉得霓虹灯广告最早应该是“上海的招牌”。
一九六八年白先勇在台湾发表短篇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讲述他记忆中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世界,著名的百乐门舞厅的头牌舞女嫁作商人妇。六年后导演白景瑞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片中由蔡琴演唱的主题曲《最后一夜》有一句“红灯将灭酒也醒,此刻该向它告别”,曲中的“红灯”,就是指霓虹灯。也许很多人还记得八十年代上海《街上流行红裙子》(内地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却不知道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街上流行霓虹灯。当年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市区时,命令所有官兵睡在街头,不准打扰市民,这个故事后来拍成电影《南京路上好八连》,但也有个别农村出身的战士觉得“上海的风也是香的”,后来果然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没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反而倒在南京路的霓虹灯下。这是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其中一个情节,故事的背景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之后,这是当年上海流行霓虹灯的另一个证据。
三四十年代是上海的霓虹灯辉煌时代,到了五十年代之后开始暗淡,当中部分霓虹灯跟随主人到了香港之后重新亮起来。在一九六○年代,随着香港工业发展蓬勃,许多企业、店铺、夜总会,食肆等,纷纷使用霓虹灯招牌来宣传自家品牌,五彩缤纷、鲜艳夺目的霓虹灯广告逐渐成为香港最具标志性、独具魅力的夜景。那些年不少港产片以港九商业区为拍摄背景,将香港到处霓虹灯这种独特的景观传播到海外和内地,成为世界各地观众认识香港、对香港记忆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保育这种老香港的人文景观,确有必要,亦有价值。
但是,不少无主广告牌年久失修,不仅有碍观瞻影响市容,更俨如一个个空中炸弹,途人随时会“中头奖”,出了事谁负责?因此,政府以公众和游客安全为首要考虑,亦是无可厚非。据统计,过去五年,根据港府屋宇署修订建筑物条例,不少旧区店家户外霓虹灯招牌因有“安全疑虑”,而遭到大量拆卸或重新维修,总数达一点六万个。位于香港油麻地庙街的老字号美都餐室,其招牌于本月八日最后一次亮灯,并于翌日拆卸结束五十八年历史,有媒体形容这是“代表香港又有一块历史招牌不敌时代洪流而熄灯”,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如何在保育和安全、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政府固然首要考虑保障公众和游客安全,但采取一刀切清拆的做法,肯定不会符合社会期望,亦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因此,政府不妨邀请专家成立专责小组,一是考虑划出特定区域保育区内霓虹灯广告,二是评估全港有哪些霓虹灯广告具有保育价值,一些无主霓虹灯如确有保育价值,可交有兴趣的团体保育,和其他保护文物项目一样,费用由政府支持或资助。至于众多旧霓虹灯的命运,只能逐渐走进历史。
笔者曾听金庸亲口说,当年他从上海来到香港,感觉像是从大都市来到乡下地方。的确,当年香港没有上海滩。八十年代上海走出封闭,九十年代开始重新找回“东方大都市”的感觉,在短短十多二十年间,外滩对岸的浦东神奇般出现一个高楼林立、美轮美奂、彩灯璀璨的现代化新上海。与此同时,老上海被好好保育,“百乐门舞厅”依旧屹立在华山路口,但今非昔比,舞池内外的霓虹灯也已随金大班们消失于历史的长河,换上了五彩的LED射灯。保育不是把旧时代的一切都保留起来。
版权声明:本文系作者原创文章,图片资料来源于网络,本文文字内容未经授权严禁非法转载,如需转载或引用必须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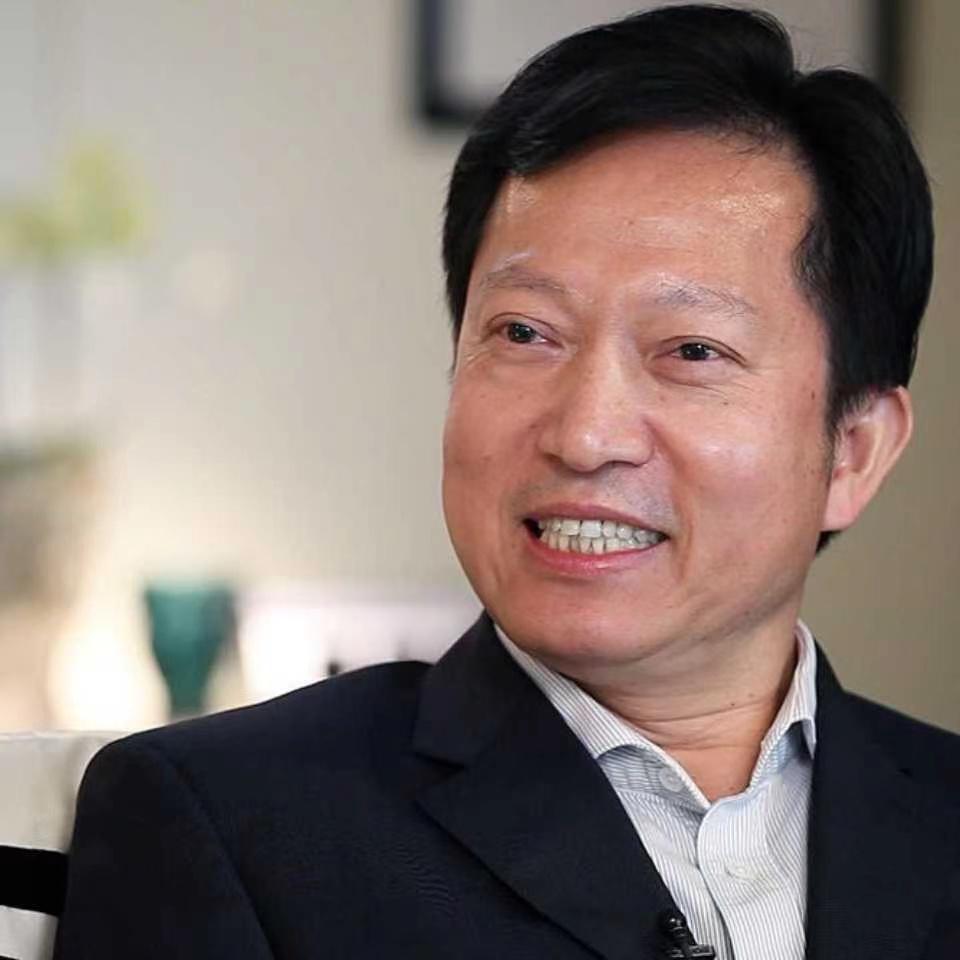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