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蒙像,图片源自网络)
□卢江良
作为“元四家”之一的画家王蒙,与同样位列其中的画家黄公望一样,在艺术生涯中有一座山脉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前者为“黄鹤山”,后者是“富春山”。倘若说,富春山对黄公望“晚变其法,自成一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黄鹤山几乎贯穿了王蒙的整个艺术人生。
黄鹤山,地处杭州市临平区星桥街道一带,旧属仁和县,系天目山余脉,山高百余丈,关于其名称的由来,南朝梁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黄鹤山者,仙人王子安乘鹤过此,因名。”北宋乐史则在《太平寰宇记》中云:“黄鹤山旧有黄鹤楼,黄鹤权乘鹤至此修道,故名黄鹤山。”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古人谓之“虽不甚深,而古树苍莽,幽涧石径,自隔风尘”。
或许鉴于黄鹤山“灵秀神奇,林泉幽野”,至正元年(1341),当过小官、刚过而立之年的王蒙,可能为避时代之动乱,携妻赴此隐居,将居处取名“白莲精舍”,并在山巅筑“呼鹤庵”,自号“黄鹤山樵”“黄鹤山樵者”“黄鹤山人”等,过起了樵耕、读书、会友、作画的闲适生活,直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受张士诚政权招引,才下山出任长史一职。之后,由于张士诚被俘,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重归黄鹤山,至洪武元年(1368)离开为止。
这也就是说,从1341年到1368年,在这漫长的二十七年里,王蒙除却为张士诚政权服务过四年,基本上都隐居于黄鹤山。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状态,王蒙在《谷口春耕图》中以图文结合的形式,有过生动的描绘:远处群山叠起,山势峥嶙,幽泉悬瀑,林木丛布;近处溪水淙淙,杂树乔林,茅庐数楹掩映其间;谷口,稻畦数亩,有人躬耕。在画的左上部自题:“山中旧是读书处,谷口亲耕种秫田。写向画图君貌取,只疑黄鹤草堂前”。

(王蒙《谷口春耕图》,图片源自网络)
众所周知,山水画与文人隐居自古紧密相连,作者生活的地域往往与其创作息息有关。可以这么认为,王蒙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山石皴法”,创造出生动繁茂的江南山水意境,显然是黄鹤山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和精神的滋养。而王蒙这种独特画风的形成,不仅与元代文人画的审美趣味相契合,同时反映了当时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可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山水画艺术的审美形态和精神内涵。于此,清孙琮评价道:“至今尺幅上,古法人独宗。”
然而,王蒙终究不像黄公望那般钟情于富春山,最后还是选择离开了黄鹤山,《浙江通志》载:“洪武初,为泰安州知州。”据说,他的这次离开,是半夜从杨维桢家逃走的,杨基《黄鹤生歌赠王录事叔明》曰:“龙君(杨维桢)劝不止,竟触龙君怒。手挽黄鹤衣,醉叱黄鹤住。黄鹤不敢去,飞绕三花树。夜深铁龙醉不醒,黄鹤高飞不知处。”之后,黄公望、倪瓒等好友屡次写信劝他归隐,倪瓒还寄诗:“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烟波一钓徒!”但王蒙始终没有回应。
可正因为这次入仕,为王蒙日后死于非命埋下了伏笔。据《明史·文苑传》记载:“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尝谒胡惟庸于私第。与会稽郭传、僧知聪观画。惟庸伏法,蒙坐事被逮,庾死狱中。”洪武十八年(1385),王蒙因牵扯胡惟庸案,难堪折磨惨死于狱中。尽管他当时的画艺已被倪瓒盛赞:“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但作为反贼党羽,时人怕受牵连,将收藏的他的作品尽数烧毁,好不容易留存下来的,也大都被刨去了他的姓名和图章。
应该说,在“元四家”中,王蒙年纪最小,却最具才华。本来,他可在黄鹤山悠哉度日,完美走完自己的艺术人生,可入仕之心一直未曾泯灭,甚至于不介意做“叁臣”,以致名节不保,未能善终。为此,清张庚在《浦山论画·论心情》中对其人品作出了这样的评语:“未免贪荣附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仍不失为中国山水画史上极富创造性的一代宗师,其传世作品在元以后常被奉为范本,广为传模,影响至今不绝。而这一切,不能不说是黄鹤山成就了他,难怪他死后选择归葬于黄鹤山,永久地与这片热土融为了一体。
2024.5.4于杭州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http://blog.sina.com.cn/lujiangliang
微信公众号:lujiangliang-1972
新浪微博:weibo.com/lujiangliang
腾讯微博: t.qq.com/lujiangliang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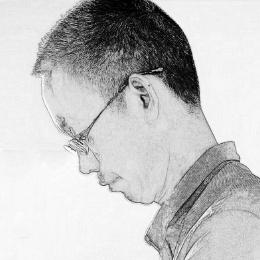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