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20世纪初,法国化学家(兼艺术家和设计师)爱德华·本尼迪克特(Edouard Benedictus)某天在实验室里工作,中途不慎让一个烧瓶掉到地上——但事故中的烧瓶并未破碎飞散,虽然裂了,各部分却仍粘在一起。
本尼迪克特对此很感兴趣,深入研究后发现,烧瓶内有一种火棉胶溶液,溶剂蒸发后,留下一层薄膜沉积于玻璃表面,因此碎片能粘一起。化学家把东西放入柜子,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发明了防碎玻璃。后来汽车市场创造了一个已经找到答案的问题,这东西才又被拿出来。由此而言,似乎是先有发明再有需求,而非先求再做。
此类偶然发现让我们看到了创新的不可预测性,也引出了更大的话题:新发现、新发明是偶然所得、运气使然,还是以某种必然性的形式,等待着对的人让它发生?
回望历史,好像所有重大发现都有其必然性。只要理论和技术方面时机成熟,迟早会有人开创新天。
麻醉剂无论如何都要被发现,便利贴的发明人也可以是张三李四。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R.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各自独立地、几乎同时地(后者比前者晚15年)提出了自然选择进化论。他们都依靠了类似的数据,例如阅读托马斯·R.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的作品以及观察岛屿上物种的分布等;双方理论有许多细微差别,但二人思想上的巧合着实令人惊叹。
这种现象在生物进化中也存在,被称为趋同:两个并不密切相关的物种演化发展出相似的功能适应性,例如蝙蝠和某些鸟类的回声定位。出现趋同进化的原因是环境对不同物种提出了相似的生存问题,或者说选择压力,例如在黑暗中飞行时怎样确定方向。
类似机制或可解释为什么科学研究也有趋同发展——不同研究团队面对相似选择压力,即相似的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所需的观测手段,并彼此竞争,提出解决方案。
如果具体分析达尔文和华莱士构建相似理论的过程,可以看到,实际上有些相当偶然性的因素促成了趋同结果,例如前文提到的,两人都在正确时间阅读了马尔萨斯的学说。同样的偶然性也促成了沃森和克里克的工作,曾与他们在同一实验室工作的晶体学家杰瑞·多诺霍(Jerry Donohue)用他对氢键的专业见解直接帮助两人修正了核苷酸碱基对模型并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这类“意外”并不少见,但总的来说,科学发现并非意外。
运气只是加速了必然的发生。所有科学家都站在前人肩膀上,客观上来说,科学需要累积。当然,在某些时刻,在特定情况下,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能够看得更远些。当一项科学发现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比其他工作更加可预测、可预期,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力量在其中不重要了,并不意味着那些天才、大师的杰出工作不值得“经典咏流传”。某些研究自带更大的必然性,会更加“包实现的”,但它们的实现仍取决于科学家个体或群体的知识,仍受偶然性的助力。(若没有旅行中出现的偶然机会,达尔文和华莱士最终能发现什么?)
没人知道,本尼迪克特意外收获的防碎玻璃——如果换到其他平行宇宙,可能以多少种不同方式出现。人总有事后做诸葛的倾向,容易把事前看似不紧要的因素拿到事后评价为意义重大,进而将偶然性认作已注定。当我们用自己灵巧的头脑把一系列巧合排列组合,并发现这些巧合使一个惊人结果成为可能,往往会立刻得出结论: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原因。它不可能纯属巧合!
我们需要承认的一个现实是,一些籍籍无名的科学家能比巨人看得更远,更能开辟新的知识领域——这绝非巧合。可以这么说,巨人的思想更容易被既有知识束缚,局限于既有的习惯、研究问题和方法的框架中。
因此,老派学者更可能做出可预测的、通过积累与深思得来的发现——有时这些发现同样至关重要,但它们停留于已知事物的附近,因为发现者更不愿接纳意料之外。
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之所以能看更远,是因为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摆脱,甚至略微背叛既有知识的束缚(或许是有意识的,更多则出于偶然)。他们有可能想象出另一片天地。
资料来源:
Is discovery inevitable or serendipitous?
本文作者:特尔莫·皮耶瓦尼(Telmo Pievani),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生物系的全职教授,意大利首位生物科学哲学教授。他著有《不完美》(Imperfection)和《意外发现》(Serendipity)等多部著作。本文即改编自这两本书中的部分内容。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 ◆ ◆
编辑邮箱:sciencepie@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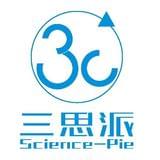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