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希腊别传》中,哲学家陈嘉映以平易的语言带我们快速领略了古希腊的风光,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时代漫谈至战乱频仍的希腊化时代,内容涉及神话与史实,征服和反叛,在宏大叙述之外细致描摹了一位普通雅典人的一天。如何才能达乎更高的生存,希腊人的哲学、德性、自由精神都叫人心向往之。

12月15日下午,哲学家陈嘉映,历史学者张新刚,编辑胡晓镜齐聚方所北京店,与我们围绕古希腊展开一场精彩的对话。想知道希腊人如何对待朋友,怎样的精神生活才算是好生活,AI给今天的历史研究提出哪些困难……尽在本篇活动回顾中。

-本文约8000字,阅读时长约25min-
用一本“小书”去认识古希腊
主持人:我很好奇,您为何会写《希腊别传》这本书,它不管在内容还是风格上都与您以往的写作有些不同,以及您在整个构思上又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陈嘉映:新刚老师是当然的希腊史专家,写过很多古希腊的书,那么我也想要为自己解释一下。我在书的序言里提到,我一直在读希腊,喜爱希腊,经常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朋友分享,有好些朋友觉得我的想法还不错,挺有意思的,就建议我把它写出来。而我还有一个初衷是,能不能有那么一本“小书”,适合那些想要读希腊却又没有太多时间的人去读,我不反对读大部头的著作,可是今天的知识面是如此广大,单单讲历史,就有中国史、西方史和各个国家的国别史等等,其他领域也都有繁多的书籍。相对而言,我也特别盼望能有人为我写几本小书,让我多少知道一点我感兴趣的领域的知识。
张新刚: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历经2500年它还能像神一样伫立在那里,召唤出众多的精神古希腊人。在我的印象中,陈老师始终是一位哲学家的形象,我以为哲学家谈论起古希腊首要关心的应该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他们留下的重要文本,而历史学者可能会更关心一个个普通的人。但是当我翻开陈老师这本小书的时候真的是眼前一亮,从目录就能看到由古风时代、古典时代一直写到希腊化时代,其中有一章叫“城邦人”,描绘了一位普通城邦居民的一天。这让我们知道希腊除在哲学、戏剧、史诗、建筑、医学、数学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个普通的雅典人或斯巴达人他在过怎样的生活,这一点是令我非常感动的。陈老师作为一个哲学家不只让我见识到天上的事物。
陈嘉映:我们从前谈到历史常会说“英雄造就历史”,尤其是中国史,非常丰富的记载着一个个伟大人物的事迹,但当我们去问一位历史学家,一个普通的唐朝人或宋朝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也需要爬梳大量的史料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漫长的历史记叙中,普通人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往往是不受关注的,但这和我们当代人看历史的方式不同,当代人依然会崇拜大人物,但是不会再发出项羽“彼可取而代之”的慨叹,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当然更愿意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看待历史。
过一天雅典人的生活
主持人:陈老师曾经说希望过像古希腊人一样的生活,那么您想象中的古希腊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新刚老师又是如何对古希腊发生兴趣的?

陈嘉映:非要让我去概括一个希腊人该是什么样子的话,我只能从一个有限的角度谈谈,对我来说,希腊人所展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充沛的活力,它不仅仅体现在运动场上,还体现在希腊人的艺术和哲学探讨上,今天的哲学论文不管多么精妙,总也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但希腊人的哲学则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灵性,希腊人之间的对话是生动的,是喷发式的智慧。可以说希腊人把他们的活力充盈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跟他们的自由精神有关。
在我所了解的各个时代中,希腊是最富独特吸引力的,我甚至无法想象自己不会爱上希腊,可是让我说愿意成为希腊的哪一种人,实际又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比方说你想成为一个唐朝人,你是想做一个战士、一个诗人还是一个宦官呢,这需要各种各样细致的琢磨比较。对我而言,我希望我是一个古希腊人,更多的是一种感叹,而不是一个statement。
张新刚:我最初对古希腊产生兴趣是因为大学时读到一本书叫《政治的历史与边界》,作者是伦敦政经学院的肯尼思·米诺格教授,书的第一章叫“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作为一个刚步入政治学的学生我还无法理解什么是“政治”,在米诺格口中,专制和政治都是一种统治方式,那么又为何说“政治中没有专制者的位置”呢。他随后解释到,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是古希腊发明的,而古希腊的政治是平等的、自有的、公民的自我统治。英文中专制这个词的词根来自于古希腊语的主人“despotes”,主人对应的则是奴隶“doulos”,在当时的希腊人眼中,主人与奴隶间的统治是埃及、波斯这些东方帝国的统治方式,他们把这种外国制度称作“专制主义”,而希腊人使用的则是“政治”的统治方式,不管政体是哪一种,它都是公民集团的一个自我统治。于是我开始对发端于希腊或说地中海区域的政治文明产生浓厚的兴趣,它们所构建的政治秩序形态都令我感到陌生。去做希腊的政治思想史,柏拉图是一个绕不开的原点人物,《理想国》为我们贡献了一个他心目中最佳的政体,但随着我对古希腊了解的更多,便发现原来古希腊也深受两河流域的文明影响,世界文明本就是一个互相交流的文明型态。但希腊政治文明的显著成就还是在他的改造力上,他当然吸收了许多产自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果实,可是他最终所呈现出的那个模样,就像刚刚陈老师所提到的“活力”,才是奠定西方主流文明的一个东西。
我认为若想进入古希腊人的日常有两条道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是荷马史诗,另一个是古希腊悲剧。每个城邦的孩子不是都有机会去柏拉图学园聆听哲学,但是他们都可以坐在剧场里观赏悲剧和听荷马史诗。所以在此意义上,你只要打开荷马史诗,去读这些剧本,你都能秒变雅典人,知道当时的人内心在想些什么。希腊神话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许许多多的英雄故事,英雄是神和人的后代,但他们的命运通常充满悲剧性,一生下来就要沥血,要去完成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还必须要死掉。奥德修斯也好,忒休斯也好,他们受到人的传颂,是因为他们并非拥有神的不朽(肉身),却也实现了一些传奇的功业。我觉得这是非常人文主义的,即我可以选择在我有朽的生命长度里去把我的活力彻底迸发出来。古希腊悲剧讲述的也是相同的内容,面对一些两难的选择,我们如何把自己活成一种典范。即使身死也要追求死得伟大而不是寿终正寝。所以古希腊孩童从小听这些英雄故事是能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滋养的,今天很多年轻人选择gap一年到世界各地去旅行,这个传统其实从奥德修斯就开始了。
“天上没有阿喀琉斯”
主持人:希腊人是此世的,希腊人认识自我首先是认识到自己是个“有死者”,关于这点陈老师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陈嘉映:希腊人处在人和神之间,他们的英雄在血统上和神有联系,但是在生死上是两隔的,神是不死的,可英雄是有死的,透过这种基本的区别,我们还能看到更深刻的内容,正如新刚所讲,希腊人作为一个有死的凡人,梦想在有限的时间里迸发他的活力,去达到一种功业,达成不朽。神当然比人更强大,因为他们不死,他们所能拥有的快乐也要比人多的多,荷马笔下的神明永远是欢乐的神明,人则是悲苦的人。但在此之外,有些东西却是人所独有的,比如勇敢、慷慨、忠诚,此类卓越的品质都建立在一个有限的基础上,因为神的生命和财富是无穷的,也就无所谓勇敢或慷慨。这个道理我们或许比较陌生,但是希腊人不陌生,从荷马时代起这几乎就是个常识。
主持人:谢谢陈老师的解答,您书中有一段话令我记忆深刻,“凡人终有一死,这是件憾事,但也正因为身为有死者,人才可能拥有复杂而深刻的感情。实际上,一切卓越都单单属于人,永远不死无比强大的神明谈不上勇敢、不屈、慷慨、笃爱、忠诚。亚里士多德一句话把这说完了‘天上没有阿喀琉斯。’”刚刚我们围绕古希腊人谈了很多,两位老师认为古希腊还有什么珍贵的东西是今天已经失落的?
张新刚:我先自我反省一下,今天很多做古希腊研究的学者特别不注意锻炼身体,我们每天开会热烈地讨论着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而德性的核心是“arete”(卓越),其本义是“男子气概”、“雄风”,这在今天听起来很政治不正确,许多女性都比男性更符合德性(卓越)的标准,但在古希腊人眼里身体的健美是卓越的必要条件。所以我才说今天的很多学者都没能做到知行合一。身体是一切自主性的来源,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比灵魂还重要,如果苏格拉底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无法在七十岁时还能站在广场上侃侃而谈灵魂的不朽。
陈嘉映:希腊人让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他们的质朴,或者说朴直。这种品格体现在他们的建筑上,希腊建筑看起来非常恢宏,但是不像哥特式建筑有那么多的附件,那么多的装饰,希腊人的雕塑也是如此,干净利落的感觉。在写作上,谁人敢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没有深度,可他们的深度又是大家都看得懂,体会得到的。希腊史诗中的英雄角色在各种境遇下也会出现矛盾挣扎,但是它不像现代小说作品的主人公,纠缠不休,可能一辈子都绕不出来。史诗中的英雄无论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总有光线会打进去,质朴的一面总会被照亮。
希腊人的“朋友圈”与我们有何不同
主持人:还想请问两位老师,如果让你们选择和一个希腊人交朋友,你们会选择谁?

张新刚:我首先不会选苏格拉底,因为他太烦人了,每天跑到你耳边劝你省察自己,质问你生活值不值得过?!我还是喜欢怪一点,好玩一点的人,就选希罗多德吧,一个说书人,走过那么多的地方,见识过那么些有趣的风景。
陈嘉映:我和新刚一样,我也不会选苏格拉底,他太怪了,很难靠近他。其实我很乐意选柏拉图,柏拉图是一个智性极高的人,他的思想中充满了空灵高扬的东西,看起来也很难让人接近,但历史上那些灵性极高的人就不会和庸人做朋友嘛,或许柏拉图也需要我这样一个平庸的朋友来帮他认识世界。
主持人:两位老师平常会看朋友圈嘛,陈老师书里写希腊人热衷于展现自己的荣耀,那么这和今天的人爱发朋友圈有什么区别?
陈嘉映:今天的人和希腊人的生活环境大不相同,希腊人生活在城邦里面,一个小共同体,相互之间都很了解,没必要躲躲藏藏,他们乐于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而今天的中国有十几亿人,你要接触不同的人群,你面对你的老板同事是一个样子,面对你的亲人朋友又是另一个样子,不能说朋友圈不真实,只是朋友圈是一种更立体的展现。所以我觉得二者无法比较,我们能够从古人那里发现自己的不足,但绝对不会是想回到古人那种状态。
张新刚:我觉得“朋友圈”这个名字起的太好了,朋友圈里其实是没朋友的,你不可能有5000个朋友,亚里士多德说朋友就是愿意和你一起吃盐巴的人,经历过考验的才能算朋友,那真正的朋友可能就两三个。我在课堂上见到一些孩子正在受我认为不好的东西毒害,我也会忍不住发朋友圈来表示关怀,我还特爱看晒做饭、晒健身的,我珍视这样的朋友,时刻想着和他们发展成典范之交。
哲学是求真的
主持人:刚才新刚老师讲到对青年人的毒害,哲学史上有“苏格拉底之死”这个著名事件,那么哲学是否毒害青年,哲学应以哪种方式言说为宜呢?

陈嘉映:我觉得源自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传统的一个目的就是求真,今天我们认为科学是求真的,但是科学追求的真实和哲学不同,哲学的求真是追求一个更丰满的东西,柏拉图讲究“真善美”,如果没有真,美和善便也不复价值,今天你们可以夸赞我是一个一流作家,把我捧得很高,我感觉特别幸福,但是我的幸福在苏格拉底眼里一文不值,因为它不真实。若不承受真实的痛苦幸福又从何而来?但是苏格拉底的求真行为与他的政治活动是分开的,虽然里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比较复杂。
论政治与自由
主持人:希腊人所理解的“自由”与我们的有何不同,对今天是否还存在启示?

陈嘉映:我们今天反过去看几千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政治模式、共同体形式,希腊这种极其高度自治的公民政体都是非常少见的,在绝大多数时代是由一个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去统治其他人。可politics这个词虽源于古希腊,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希腊人把他们管理自己的手段叫做政治,那其他地方的人使用的就不是政治了嘛?政治具有广泛的含义,如果只从希腊人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的话那一定是带有偏见的。
张新刚:我认为希腊人在“自由”上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有两个。众所周知希腊人的自由一般是指政治自由,但政治自由仅限于城邦成年男性公民,这里需要纠正的一点是,希腊的部分女性也有参与城邦宗教事务的权利,宗教事务和政治事务都属于公共事务,而直到19世纪,尤其在一战后,世界范围内女性参政议政的权利才逐步扩大,今天的社会也不再有奴隶的存在,只要你是一个合法公民就有投票权和被选举权,从此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原则被推广至所有人,我们都算是希腊人自由精神的后裔。
另一方面,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希腊绝大多数城邦面积极小,大概只需两三个小时就能横穿城邦,居民清晨出城劳动,傍晚而归,狭小的城市空间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即各项公共事务都能得到城邦居民的有效参与。这和今天的情形不同,今天的城市太阔了,人口也太巨了,我们必须选出一些代表来替我们进行常规的政治活动,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等等。同时,希腊人的政治活动多聚集在战争的讨论上,而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战争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国家行为,但商业世界我们更关注自己的私人权利,渴求的是不被干涉的自由(法律层面上),对于国家和社会,共同体与个人,希腊人并不如现代人善于区分。
与希腊人精神生活的远近
主持人:制度和履行制度的人哪个更重要?希腊的三个时代,希腊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我们和哪一时期更接近呢?

陈嘉映:去比较雅典和斯巴达城邦制度孰佳孰坏是一件无解的事,虽然我们很容易就能指出他们各自的优劣。制度设计当然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一个主要的地位,但关键是我们能否去爱护这个制度,因为世界上本不存在完美的制度,爱护者所要做的是尽量发挥制度的优点,并从其他方式上弥补它的缺点。如果所有人都变成机会主义者,开始利用制度的缺陷,那么制度将会越来越糟糕。正如我们早年在学习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时也将其视作典范,但随时间推移,我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加深,它旧有的和新的缺陷都暴露出来,这背后当然也跟一些西方政客对待他们制度的态度变化有关。
从前古典时代(荷马时代)到古典时代再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精神生活当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我们不可能再靠近荷马时代,那是一个摆放在天上需要我们抬头仰视的“英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不存在联结。硬要说和哪个时代更接近,我觉得是和希腊化时代吧,一个个小的城邦被吞并,庞大的共同体(帝国)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人就像一粒沙子,他为了寻求更高的生存,需要找到一个凌驾在共同体之上却又便于他靠近的信仰,基督教因此而诞生。我觉得这和我们今天许多人的心灵状态接近。不过我个人还是更向往古典时代,柏拉图和埃斯库罗斯的时代,他们把全部的情感渗透进对世界的观照中。
张新刚:希腊后期,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犬儒主义等逐渐成为显学,在这个时段城邦生活不再使内心感到安宁,尤其是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希腊人变得和他们口中的蛮族一样野蛮,开始屠杀敌对方的成年男人,把老人、小孩、妇女卖为奴隶。这时候你只能寻求自我的安慰,像第欧根尼一样躲进木桶里,享受肉体的无痛苦,灵魂的无纷扰。《刺客信条:奥德赛》中有一个主线任务是雅典人的金库,它被雅典人献予诗歌之神阿波罗,以纪念希波战争期间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但你要清楚,这样的辉煌灿烂是靠极端的血腥塑造的。古典时期的伯里克利说,如果你丝毫不关心城邦的公共事务,你将不仅是一个无用的人,还是一个无趣的人,这意味着成为人的前提是成为一个“政治人”,那么是否说明我们的人生都必须和城邦捆绑在一起,也不是,你当然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吟游诗人,一个说书人,游走在各个城邦间,但是无论做何种选择都脱不开城邦的兴衰。
陈嘉映: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上:我们如何看古人?方才新刚讲到了希腊人的暴行,这些暴行在当今是难以想象的,即使俄乌战争打得如此激烈也不会出现把对方城市的男性公民全部杀掉的事情,这违反了战争伦理,那是否能说我们比希腊人更文明更先进呢?我觉得看待古人的行为还是要回到他所处的历史阶段,同一时期的秦国也发生了白起坑杀四十万降卒的事。不论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还是历史学家,都没必要去美化历史,当然也不应该用后来者的眼光去挑古人的错。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我当然想和更好的古人交朋友。
读者提问

读者提问1:想请教两位老师,西方哲学和东方思想的异同点在哪里?
陈嘉映:从我个人的理解上讲,和希腊同时期的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与法家,主要是围绕“治国”来展开他们的思想的,不管是使用宽厚的治理方式还是使用严酷的手段。当然在佛学传入中国后思想的锚点起了很大的变化。希腊则不同,希腊哲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自然”展开,从早期的伊奥尼亚哲学家到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论述许多是在讲自然世界的物质基础,今天看来充满了科学精神。希腊哲学当然也谈了很多政治,但极少谈治理术,谈如何参与公共事务(公共生活)比较多。
读者提问2:AI技术的发展和跨学科方法的成熟给今天的历史学研究造成了很大冲击,对某段历史可能会出现全新的认知,面对随时更新的历史观,我们该如何自洽呢?
陈嘉映:你提到的是一个在历史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中非常突出的问题,它可以反映到一切学科上,无论我们怎么做都不可能穷尽某个学科的知识。那在此意义上大可走入一个彻底虚无主义的结果,对待一切都选择缄口不言。但我认为更实事求是的做法是尽可能多的占有资料,即使这些资料明天就会被证伪,即使我们所做的推导明天就会被人推翻。我们还是得保留一些求知欲。
张新刚:今天的科技手段,比如AI,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识读一些过去读不了的东西,但有一点很关键,历史材料的总量是有限的,关于希腊史95%以上的材料都被人使用过了,且使用了无数遍,那我们还怎么去做研究呢。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平稳的心态,应当清楚任何的历史研究都是建立在已有的材料基础上,你并不知道古人留给你的材料是什么样子的,像柏拉图他写了很多论文,但留下来的都是他的对话录,亚里士多德有很多对话录,留下来的却全是课堂笔记,如果他们的东西能够全部留存下来,那今天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但很抱歉,我们今天只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很难知晓手里的材料在古代是个什么位置,它是主流还是非主流,但既然你去研究古代,每一份材料都应当成至宝,即使它存在偏见,那也可能会反映出许多东西。
读者提问3:我们在做历史评价时是否存在一些基本的评判纬度,比如物质发展情况、道德要求或者人民拥有的自由度等等?
陈嘉映: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有主导的一套标准,可能包含GDP,也可能包含人民的道德水平,甚至可能包含对上帝的虔诚性等等,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何为良好的国家形态,何为良好的社会生活。
张新刚:希罗多德在他的书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波斯帝国的每个人选出最好的生活方式,人人都认为自己民族的习俗和生活方式才是最好的。粽子有甜咸之争,这不是一件有所谓的事,可如若让你必须选一个国家生活,你愿意在朝鲜、叙利亚还是瑞典,这就是一件很值得思考的事了。社会学家涂尔干写过一本书叫《教育思想的演进》,考察了十几个世纪的教育观念和制度史,涂尔干在最后告诫我们应该学文法,还应该学历史,只有学了历史你才能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习俗及不同的秩序构建方式。台湾中研院的王汎森先生有一本《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王先生说我们应借着读史不断地贮存内心中的资粮,这样你再去思考时才会有更多的凭借,即以史来扩充“心量”。
游学墨西哥(3.21-31),解开失落文明的密码
春节·日本旅行(1.29-2.3),国家地理认证的亚洲最佳旅行城市
春节·古埃及文明深度游学(1.28-2.6)+尼罗河五星游轮
查看更多游学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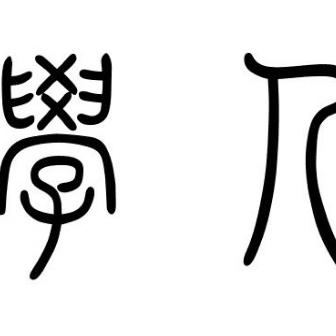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