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被公认为“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本人对此有所保留)。桑德尔在牛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 1980 年开始就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目前是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 Anne T. 及 Robert M. Bass 讲席教授。2007 年 5 月底,桑德尔到上海访问演讲,我们曾有过愉快的交谈。12 月我到哈佛大学拜访他,现场观摩了他讲授的本科生课程“正义”(这是哈佛有史以来注册学生最多的课程),还得到他惠赠的两本著作《民主的不满》和《公共哲学》。《民主的不满》中译本出版后 , 在我的提议下桑德尔教授接受了这次访谈。
刘擎:中国学术界和读者对你是有所了解的。你的著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2001 年在中国翻译出版,2007 年你又到中国进行了学术访问,最近《民主的不满》又出版中译本。我们仍然想更多地了解你的思想历程。作为政治哲学家,你的学术生涯开始于第一部著作的巨大成功,这本书是在你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在这个学科领域中,很少有博士论文产生过如此显著的影响,不仅罗尔斯本人予以高度重视,甚至还引起了欧克肖特的关注(他几乎不读当代学者的作品),而当时你还不到 30岁。在你看来,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样不同寻常的成就?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故事吗?而在哪些方面,你受到了你当时的导师查尔斯 · 泰勒的影响?
桑德尔:我对政治哲学的兴趣是由对政治的兴趣而萌发的。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格外关注媒体对总统竞选活动的报道。读大学的时候, 我学的是政治、历史和经济,当时我以为我会成为一名报道政治问题的记者,或者可能会去参选公职。在大学最后一学年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在华盛顿特区打工,做一名政治记者。那是 1974 年的夏天,当时“水门事件”丑闻败露,美国国会正在展开辩论,是否因为尼克松总统的滥用权力而弹劾他。我报道了弹劾案的听证过程,也报道了最高法院的决议案,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他与幕僚之间关于水门事件的对话录音带作为证据。这是一段引人入胜的经历,让我能近距离地观察一个令人兴奋的政治时刻。大学毕业之后,我得到一笔奖学金,使我有机会到英国牛津大学就读研究生。我当时以为,我只是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学习政治哲学,然后就会重新回到对政治和经济更为经验性的研究方向上去。
但是, 政治哲学把我给迷住了。在第一个假期,记得那是 1975 年 12 月,我和几个朋友去西班牙南部旅行,随身带了四本我要读的书 :约翰 · 罗尔斯的《正义论》、罗伯特 · 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这本书对放任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做了一个哲学上的辩护)、汉娜 · 阿伦特的《人的境况》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回到牛津的第二学期,我选了有关康德的指导课(tutorial)。后来我继续学习其他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包括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早期马克思、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宾诺莎。
特别幸运的是,我能在查尔斯 · 泰勒的指导下学习,那时候他对我有很大影响,而我对他始终是极为钦佩的。我最终在牛津度过了四年时间,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有关罗尔斯和康德所发展的那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对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展开了批判,这后来成为我的第一部著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刘擎:在《民主的不满》一书中,我感到你有两个重要的变化进展。首先,你仍然继续对康德派的自由主义展开批判,在哲学上针对其关于自我的不恰当观念,在政治上反对其国家道德中立的政治原则,但与此同时, 你试图提出更为正面的或者说更有建设性的另类方案,在此你汲取了公民共和主义的传统。其次,当代大多数与古典共和主义复兴有关的论述(比如斯金纳和佩迪特的作品)主要是纯粹学院派的写作,而你的这本书似乎有意识地要超出“纯粹学术”的限制,面对更广泛的读者(包括普通公民)。在我看来,这两个方面的进展实际上使你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 :你成为一个倡导新的(基于共和主义的)公共哲学的重要公共知识分子。那么,两个进展背后的主要意图是什么?这与你对“何为民主” 以及“政治哲学在公共生活中有何作用”等问题的理解是否有所关联?
桑德尔:是的,你的观察是准确的。《民主的不满》试图针对两种读者──学者和公民。对于学者而言,这本书继续展开关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争论,提出一种借鉴了公民共和主义的另类方案。但这本书也面向学术界之外的公民。因为我感到,人们虽然获得了更大的物质繁荣,但却体验到一种共同体的失落,体验到一种越来越严重的无力感,这时候就会产生不满,而这本书试图对这种不满予以诊断。在我看来,政治哲学不只是去研究过去的思想家和各种思想传统,它也与当下相关。政治哲学的目的是对那些影响我们公共生活的各种前提作出批判性的反思,并且去促进这种反思。在民主社会中,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要介入这种反思。民主社会的公民必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涉猎政治哲学。
Sandel 哈佛讲座《公正:该如何做是好?》,非常受学生们欢迎。
刘擎:这部著作最初发表在 1996 年,至今已经十多年了。但随着全球性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它所关切的主要问题在今天甚至更为突出,与公共生活(不只是在美国)具有更为紧密的相关意义。在许多方面,不同国家的人们都有某种无力感,都体验到共同体的溃散以及道德的衰落, 或者说都有相似的不满。对于寻求新的公共哲学的人们来说,公民共和主义的确具有某种吸引力。但是,论及复兴共和主义的传统,我们也面对许多问题和困难。首先,有一种看法认为,复兴公民共和主义的努力可能是一种“时代错误”(anachronism)。人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公民共和主义当初会被抛弃?《民主的不满》用了相当大的篇幅给出了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解释,阐述“公民的政治经济”何以逐渐被“消费的政治经济”所压倒。但是,这一历史变迁不仅是政治话语的转换,而且伴随着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背景的转变(大公司时代的来临,国民经济的兴起,以及国际市场的扩张,等等)。
因此,有人会争辩说,除非我们愿意并且能够改变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和背景(这似乎要求某种革命),否则,共和主义政治的复兴是不可能的。毕竟,共和主义政治根植于一种相对较小的、同质性的共同体,也只能在这种共同体中得以存活。你会如何回应这种怀疑论?你也曾提到共和主义传统不能在现代条件下直接运用, 那么需要改良的是什么?
桑德尔:我同意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不能直接运用于当代社会。在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中,城市的所有公民聚集在一起来审议公共问题,但这种思想假定了“城邦”(polis)是政治联合体的主要形式,还假定了“城邦”在经济上或多或少是自给自足的。而今天,从政治上说,“民族国家”取代了“城邦”成为政治联合体的主要形式;从经济上说,在全球化的时代, 甚至最强大的国家也会受到超出自身控制的经济力量的制约。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公民共和传统提供了两方面值得我们借鉴的重要洞见,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仍然具有相关意义。首先,如果要让公民参与来塑造那种支配他们集体生活的力量,那么经济权力就必须受到政治权力的问责约束。而全球性的市场就要求全球性的治理形式。其次, 如果要让公民来商议“共善”(common good,或译作“公益”)的问题,他们必须分享某种共同的生活,分享某种对自己公民同胞的责任感。民主公民的这两个要求,突出了全球化对于民主所造成的困境或者(至少是) 挑战。
全球市场的兴起以及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都要求我们发展一种全球性的公民品质──某种共享的政治伦理和相互责任,超越国家疆界的限制。然而,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要培养一种强有力的社群感与公民义务感是困难的。因为大家最容易认同的是那些与自己分享共同经验和传统的人们。而全球政治伦理,需要我们培养一种多元交叠的公民身份认同──某些要比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更宽泛,有些则更特殊。
刘擎: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较大而且异质性的共同体之中,在道德观念和“良善生活”(good life)的观念方面,存在深刻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有这样一种论点 :对于道德、价值、善以及生活的意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谈论得越多,我们就越可能发生分歧, 哪怕我们都是理性的人。用拉莫尔(Charles Larmore)的术语来说,就是所谓“合理的分歧”(reasonable disagreement)。在现代社会中,似乎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但同样正当、同样合理的善的观念,这构成了现代性的特征性条件,也常常被用来证成(justify)政治自由主义。
如果“合理的分歧” 是一个事实,那么共和主义复兴所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更为深刻,或者说在哲学上更为困难。问题不在于我们存在分歧(分歧本身是任何民主社会的特征),而在于它可能威胁到“自治”(self-government)这一理念(这是共和主义对自由的理解)。如果我们不能形成那个基于“共善”的“集体自我”,而只有形形色色不同的自我,那么我们究竟在谈论谁的“自”治?如果我们的公民德性(诸如道德推论和商议)以及积极参与无法建构那个集体的“大我”,如果我们能有的就只是许许多多彼此竞争的“小我”,那么,任何一个基于实质性价值立场的政治决定,是否就必定意味着,要在各种竞争性的善的观念中有所抉择、有所褒贬或者说“区别对待”?
桑德尔:的确,现代社会的公民对于良善生活的意见常常会发生分歧。我们生活在多元的社会中,人们有不同的道德与宗教信念。而民主的公共话语必须尊重这些差异与分歧。但问题在于,如果对各种良善生活的观念完全没有厚此薄彼的臧否,是否还有可能制定公正的法律、界定人的权利,或者贯彻实施公共政策?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而且, 试图将公共政策同法律与道德理想相隔离,可能会导致用一种技术官僚式的、经营管理式的方式来对待对公共生活,这种方式剥夺了公民对那些体现在政策和法律中的价值予以批判性反省的机会。对于道德和公民理想展开公共商议并不要求意见相同,也不能保证会达成一致。强劲的公共讨论与争辩──甚至是关于深信不疑的道德理想的辩论──并不一定是虚弱与不和谐的征兆,实际上反而可能是民主社会的力量源泉。
刘擎:你或许知道,许多中国人曾有过那样一种经历 :生活在某种单一价值与道德的政治垄断之中,这套价值与道德是由“大立法家”所强加的。有过这种经历自然会对“强制的危险”格外敏感。你对于共和主义政治潜在的强制性也相当敏感,似乎试图“驯服”这种强制性,这特别体现在你对卢梭与托克维尔(还有阿伦特)在公民教育问题上的看法所作的区别。为了防止所谓“灵魂工艺”(soulcraft)变得过分强制,我们应该首先注意什么?就此而言,在共和主义政治与自由主义政治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共同之处?
桑德尔:在任何时候,只要当政府自己关注“公民德性”或者“政治教育”,就会有演变为强制的风险。这里的危险在于,国家权力被用来将某种单一的美德观念强加给整个社会。自由主义就是在回应这种危险之中兴起的。但是,自由社会也需要公民拥有某种公民品格,例如宽容以及尊重他人权利的意愿等。任何一个关切“共善”的社会,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提升和促进公民的一种精神意愿──为了整个共同体的益处而超越自身利益的意愿。
没有任何社会可以无视公民教育的事业,但公民教育不是灌输教化(indoctrination),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加某些价值观或信念。最好的公民教育来自参与从事自治,来自自己的公民同胞商议要做什么样的集体选择。通过参与某种实践活动来开展公民教育,这是一种在行动中学习的方式。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曾讨论过民主所要求的“心灵的习惯”,他认为这些习惯(至少在最初)是“习得”的,是在新英格兰地区通过镇的公民参与活动而习得的(那是在 1830 年代,当时托克维尔访问和周游了美国)。
本文节选自刘擎经典著作《纷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寻踪》
综述西方思想界十年图景,勾勒一代知识分子立体群像,西方思想界源流与发展入门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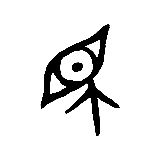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