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国家档案局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档案馆举办的“刘松龄与玑衡抚辰仪档案文献展”在皇史宬举行。
刘松龄来自斯洛文尼亚,是一位传奇般的人物。18世纪上半叶,他完成学业后,立志到中国以科学传教,在1739年得偿所愿,跨越中亚大陆来到中国,进入钦天监,工作了35年,直至去世。
刘松龄将自己的半生奉献给了中国,是中国连接欧洲的重要科学家。他的名字和他主持的工作,多次出现在乾隆皇帝的实录里,这些实录也曾经存放在皇史宬的金匮石室里。

▲中斯友好纪念碑——玑衡抚辰仪复制品落成仪式现场。玑衡抚辰仪原件现位于北京古观象台。新华社发
远渡重洋赴中国
刘松龄,本名费尔迪南德·奥古斯丁·哈勒施泰因(Ferdinand Augustin von Hallerstein),1703年8月27日出生在今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近郊门盖什镇的一个贵族家庭。
哈勒施泰因家境优越,从小喜欢读书,爱好科学,尤其喜爱天文学。因自幼受到家庭宗教信仰的影响,在卢布尔雅那的耶稣会学院完成学业之后,他决定加入耶稣会,并立志以科学传教。为此,他又先后到维也纳、格拉茨学习了数学、天文学和神学。1727年,哈勒施泰因请求去中国传教,但直到八年以后,他的请求才获得耶稣会的批准。
1735年,哈勒施泰因出发前往中国。他从今天意大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海港出发,先后途经了葡萄牙里斯本、非洲莫桑比克、印度果阿,经过两年多漫长的海上旅程,历经艰辛,终于在1738年到达澳门。
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哈勒施泰因就开始学习中国的文字、书法和礼仪,并且给自己取了一个好听又颇有含义的中文名字——“刘松龄”。“刘”是中国的大姓,而“松龄”则有健康长寿的美好寓意。当时的乾隆帝对西洋学术文化和奇器物品有浓厚的兴趣,来自西方知识渊博的传教士,会被召入宫廷委以重任。当时,担任钦天监监正的德国传教士戴进贤向乾隆帝介绍了从国外乘船而来的“能知天文历法”的刘松龄、鲍友管,“能知律吕之学”的魏继晋,“画喜容人物”的王之臣和“能于钟表”的杨自新,并建议将五人“交与广东督抚,令其派人伴送进京”。得到乾隆帝应允后,刘松龄于乾隆四年(1739年)四月来到北京。
刘松龄从欧洲带来了最新的天文观测技术和数学知识。乾隆帝对此深为赏识,将他安排在钦天监工作,辅佐德国传教士、钦天监监正戴进贤。乾隆八年(1743年),补授钦天监监副。乾隆十一年(1746年),戴进贤去世后,刘松龄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官至五品。刘松龄负责掌管钦天监事务一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是担任此职务时间最长的西方人,清宫档案记录了他在钦天监的履职情况。

▲刘松龄墓碑。资料图
玑衡抚辰夺天工
观测天象是钦天监最主要的职责,刘松龄任职期间,一旦遇到重要天象,会及时呈报观测结果,并据此判断当年的气候,以指导农耕。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刘松龄根据测得打雷的时辰、次数、声响,结合占书,得出“雷初发,声和缓,其岁善”的判断。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根据观测的春分时节风向,推测“春分之日风从巽来,有虫,四月多暴寒”。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根据月食的时刻及方位,推测“甲日月食,年多雨,禾麦伤”,但又提到“三日内有雨则解”。
刘松龄还参与修订了《灵台仪象志》,更新了书中天文知识。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了6座天文观测仪器置于观象台,并纂成《灵台仪象志》一书,阐释仪器所用之法。由于时间久远,该书与实际情况已有不符,如书中所载黄道赤道相距已不准确,且二十八宿诸星也多有不同。
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下令钦天监修订和补充康熙朝编撰的天文学专著《灵台仪象志》。在戴进贤和刘松龄主持下,中外天文学家经过8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修订本。全书共35卷,包含了当时中西方天文学家观测的最新成果。乾隆帝认为,该书可“步天定时之道,益为精密”,将其命名为《仪象考成》,并亲自撰写了一篇序言。《灵台仪象志》记载了1876颗恒星,而《仪象考成》中则记载了多达3083颗星。
此外,刘松龄的突出贡献之一,便是监制了玑衡抚辰仪。这一复杂而精美的仪器,由乾隆皇帝赐名,如今位于在北京古观象台青砖搭建的角楼上。
乾隆九年九月二十二日(1744年10月27日),乾隆帝亲临观象台视察,看到台上的观测仪器构造和刻度都已经陈旧,无法达到所需精度,遂下令钦天监按照中国传统浑仪形制,再制造一架新仪器,用来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和纬度。此仪器由传教士戴进贤和刘松龄负责监制,中外能工巧匠花费了10年时间完成,使中国天文观测精度达到空前水平。
玑衡抚辰仪由青铜浇铸,使用了欧洲天文度量制,在结构上则采用中国传统的浑仪形式,中西合璧,工艺精美。它主要用于测定天体的赤经差和赤纬、真太阳时,采用360度分尺,大大提高了测量精度。仪器两边有两根游龙盘旋的柱子,支撑着天常赤道圈,在十字交梁底座的中心处立有精美的云座,托着双环子午圈的底部。仪器上除了有十条龙盘旋,还有狮子、云海、山水纹装饰其中,可谓巧夺天工。
刘松龄亦擅长地理舆图之学。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下令绘制一幅清代塞外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地图。为此,刘松龄受命与同在清廷供职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等人一起,来到野兽出没的木兰围场,他们绘制出了新的木兰围场地图。清朝平定准噶尔以后,刘松龄在西北地区舆图绘制中也发挥出一定作用。
外交事务亦胜任
刘松龄不仅是学识渊博的科学家,还经常协调处理清廷的外交事务。这得益于他精通汉语、葡萄牙语等六种语言的才华,以及在欧洲、中国的丰富生活经历。
刘松龄极有语言天赋,他在里斯本等待船只赴中国的过程中,学会了葡萄牙语。在离开里斯本前,他与出生在奥地利的葡萄牙王后玛丽亚·安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此后,刘松龄一直与玛丽亚一世和葡萄牙宫廷保持联系。乾隆十七年(1752年),刘松龄向乾隆帝转达了葡萄牙国王派使臣巴哲格率团访华的意向。乾隆帝十分重视,在北京做好了准备,特派遣刘松龄去澳门迎接,并护送进京。巴哲格所带领的葡萄牙代表团受到乾隆帝的隆重接待,在中国待了一年多,回国时,仍由刘松龄送至澳门。刘松龄圆满完成了外交使命,乾隆帝十分满意,下谕“此次西洋贡使来京,刘松龄前往接引,沿途办理一切,甚属黾勉,著加恩赏给三品职衔食俸”,晋升刘松龄为三品官职。除此之外,又加赏白银2000两。
刘松龄能够圆满完成外交任务,得益于他出众的社交能力。在北京时,他与当朝官员结下了友谊,搭建起中西交流的桥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夏日的一天,乾隆朝进士、历史学家赵翼等官员造访北京城里的宣武门天主堂,受到了刘松龄等人的热情款待。刘松龄邀请赵翼等人观赏了教堂里的油画、试看了千里镜(即望远镜),并且用管风琴演奏了西方的乐曲,使客人们大开眼界。这次参观后,赵翼有感而发,写文赞美令人惊叹的望远镜和美妙的西洋音乐。赵翼的文章既是刘松龄与中国官员友好交往的例证,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佐证。
当然,哪怕有同事朋友相伴,身在遥远异国,刘松龄也难免有思乡的时刻。他一直与耶稣会同仁以及远在欧洲的弟弟、妹妹们保持着书信往来,尽管那时候一封信件的往来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在想念故乡的时候,他还会阅读从斯洛文尼亚带到中国的唱诗本,这成了他最大的精神慰藉。如今,这本1729年出版的唱诗本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鞠躬尽瘁身后荣
刘松龄在中国工作30多年,把毕生的精力与才华都奉献给了中国。晚年,在身体条件越来越差的情况下,刘松龄仍勤勉本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已经70岁的刘松龄精神渐消,步履艰难,奏请休致。乾隆帝希望他继续留在钦天监的同时,给予了极大的关照,传谕:“刘松龄不必乞休,听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艰,即不随班,亦从其便。”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1774年10月31日),刘松龄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为褒奖刘松龄的事迹,乾隆帝下令将其安葬在北京西郊耶稣会墓地,丧葬所需费用全部由宫廷支付。刘松龄墓的汉白玉石碑上盘绕着象征皇家威仪的双龙,碑身正中刻有“耶稣会士刘公之墓”和清廷给予他的赞誉,墓碑全文如下:
耶稣会士刘先生,讳松龄,号乔年,泰西热尔玛尼亚国人,自幼入会精修。大清乾隆四年,来京传教;乾隆八年,奉旨补授钦天监监副;乾隆十一年,特授监正;乾隆十八年,因接送波尔都噶俚国使臣有功,赏给三品职衔食俸。共在监三十一载,勤敏监务,敬寅恕属,德业兼着。卒于乾隆三十九年,享寿七十有二。蒙恩旨赐内库银二百两为安葬之资。
刘松龄的一生是中西交流的写照。刘松龄和他的事迹长期不为大众所知晓,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流沙中。近年,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中斯两国档案学者、历史学者的努力,对刘松龄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024年2月6日,中国驻斯洛文尼亚使馆、卢布尔雅那市政府联合举办中斯友好纪念碑——玑衡抚辰仪等比例复制品落成仪式。纪念碑位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档案馆门前。该纪念碑的落成,是中斯之间交往的新里程碑,象征着两国的深厚友谊,是当代中斯友好的一条纽带。(完)(原标题:刘松龄:从斯洛文尼亚到紫禁城)
作者/高伟强
来源:北京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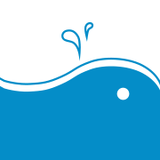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