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坚持带饭上班,我在同事眼中就树立起了一个很会做饭的形象。
川味辣子鸡、豆腐焖火腩、花雕冷泡虾、酱油皇炒面… 我的饭盒365 天不重样,色香味摆盘样样俱全。从小包邮区长大的我,自以为天南地北的食材和烹饪手法都能轻松拿捏,再加上网上各式教学视频,各种高科技厨房小家电,我甚至夸下过海口:随便点餐,我几乎都能做出来。
“溪姐明天能蒸屉包子吗?好怀念妈妈亲手发面的包子啊。”隔壁山东籍00后小姑娘向我投来期待的眼神。
啊!这,这就是我死穴了!
虽然十八般厨艺样样精通,偏偏发面一直是我难以攻克的技艺。南方人是不是生来就不带发面这个基因?至少就我看来,无论北方博主们如何“保姆级教程”,“有手就会”,臣妾做出来的,终究是一箩筐的热粮食冷兵器,咬是咬不动,打还是能打得过。至于“暄软”“白胖”?对不起,我们普通南方人的手作面点里真没这个词!

为什么我的南方妈妈,什么都传授了给我,却从来没教过我包包子?

“发面?这都是要功夫的呀,自己在家哪能搞得好呀?”
电话那头,我妈差点总结了“不能在家做面食的一百个理由”,简而言之就是:经过年轻时无数次失败以后,发面这件事,就再没出现在她的厨房了。
确实,记忆中面粉在家里的唯一出场就只有疙瘩汤。

但我不是我妈!为了00后的小妹妹,也为了我自己,在北上十多年后,我再次尝试告诉自己,这事还有余地。于是,又一次未知旅程开始了:
“你就急着,100克面粉1克酵母,再加点小苏打,确保出锅的时候不会塌陷,再搁一点白糖,酵母喜欢吃白糖,这样发出来的面就会香甜。”视频那头的北方阿姨不紧不慢,游刃有余地操作着一桌子各种粉末。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精准教学”的北方阿姨了。努力跟着屏幕里展现她的比例进行模仿,室温偏热的温水,开始蓬松的酵母水,蓦地,心中升腾起一种叫做希望的情感。
右手一双筷子,因为视频里的阿姨说,一开始面的确会黏手。伴随着节奏将黏手的面粉倒入洒满面粉的平面,搓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等等,为什么我的面团手感很疙瘩?不祥的预感开始在胃底环绕。盖上湿抹布放1个小时,等再次回来,视频里的阿姨已经拥有一个胀开膨大的面团,而我的,几乎只有她的1/2大。

不管了,再次对面团进行捶打,进入揉剂子环节。当我盘着面皮准备起码捏出一个像样的包子褶时,那面皮被我的小心谨慎越扯越大,越扯越薄,上面是收了口,下面却开起了天窗。再一次,厨房变成了一个大型作死现场,信心被灭掉大半,事情也就开始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
所以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象中明明是一笼包子,最后却变成了一锅肉龙。至少肉是一定熟了,而且吃起来绝对顶饱。可不么?宣软二字跟眼前的这笼几乎毫无干系,扎扎实实的实心面,砸身上都疼。
第二天在办公室,我自然是只字没提前一天的尝试,只是拐着小妹妹,去了我熟悉的一家北方包子馆,带小妹妹吃了个痛快。我仿佛走进了南方女人一生中无法穿越的大山,再次证明了即便是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想发面成功也是不一定能的。


我选用了一个格局比较大的视角来进行自我安慰。
30 岁不到的我,只是一个跨过秦岭淮河北上不过区区十年的小兵。人家小麦,已经在祖国黄河流域待了整整一部中国历史那么长的时间。这种背景巨大差异,造成我们在短时间内相互不理解的状态似乎变得可以理解了。
老家在西亚和中亚的小麦,五千多年前跟着有史以来第一批游牧民“北漂”进了中国境内,在黄河流域雨水稀少的广袤旱地,这些古老的种子遇到了惺惺相惜的地理环境,从此在这开枝散叶……

如此浩浩荡荡的历史并不需去翻看什么文献资料,在北方任何一个生活区里的主食厨房档口,那高强度白炽灯光下并排摆开的馒头、窝头、烙饼、火烧,都足以向人展示小麦在这片土地上,身为“地头蛇”的实力,照料了一代又一代北方人成长,他们在餐桌上相互融合相互扶持,是数千年累积出来的底蕴和手艺。
对于初来乍到,和小麦完全不熟的南方仔,只能乖乖当个局外人。一双迷妹眼睛看着厨房里白衣白帽的大娘,惊叹她们都懂得用面粉变魔法,只凭面粉和酵母和水,就能做出形态各异,入口绵软、蓬松、弹牙、筋道的面,面粉的可能性都被一双双北方人的巧手出神入化地展现出来。在这一点上,我认输,无论是吃菜饭,还是嗦米粉长大的南方人,关于面食的知识盲区,都比北方茫茫的小麦田还要广袤。更何况除了小麦磨出的面粉,还有粟米面、豆面、荞面、莜面。而一种面又可以被蒸、烤、煎、炸、烩……

再把他们组合起来,北方面食的战斗力,可以说是复仇者联盟级别的几何增长。
北方人能够如此坦荡地享受“面”真叫人羡慕。这让我想起过去有老上海人下馆子点不起浇头面,但大庭广众下讲出“光面”两字又扫面子,于是光面改叫了阳春面的故事。要是换在北方,好像就大可不必扭捏,有馅儿则锦上添花,没馅儿的馒头花卷,单单吃它的暄软蓬松也是一种享受,还有馍的脆口,火烧的咬劲儿,窝头的谷香……

更有登峰造极的“银丝卷”,传承自鲁菜,光亮白嫩的包子皮,卷着油润的“甜丝”,第一口是馒头的松软,第二口是花卷的香甜。说白了就是面条馅包子,和帝都地铁口第一名产“大饼夹土豆丝”有得一瓶。令人不禁感叹,山东大汉做起精细面点,就是这么实在。
面食面前人人平等,虎妞给祥子做的是“馏的馒头,熬白菜加肉丸子,一碟虎皮冻,一碟酱萝卜”,坐车的贵族老爷吃的兴许也不过就是这一口。

落魄的老克勒在一碗光面前的难堪,让人不得不承认,菜才是南方人的面子,面不是。
江南的面馆里是铁打的面条,流水的浇头;香港茶餐厅里,人们关心猪肝够不够爽滑,云吞馅料够不够鲜,叉烧够不够肥瘦均衡,但对“面”的要求却会降低,甚至是在塑料装袋的”预制”的出前一丁,也足够成为老港面碗里的定番。
所以也有人说,在南方别人问你今天吃什么饭,其实是在问吃什么菜。在种满水稻温热湿润的土地上,下饭比吃饭更重要。也无可厚非,毕竟在这片物产丰饶的土地上,菜的发挥空间,确实比面多多了。所以这里的人,就算做面,拿出的也是做菜的天赋和觉悟。

春天野菜上市的季节,苏州人把还沾着泥土的野荠菜切细碎,和上猪肉和香菇、木耳、干冬笋,再加若干海米包进包子,几组分别来自山河湖海的鲜货汇集一堂,互补又不抢风头,鲜得叫一个掉眉毛。秋天蟹脚痒的季节,拆一只蟹,将黄、膏、肉分开炒制,加一点点姜丝和醋调味,再配一点时令的鸡头米做装饰,就是一碗无可匹敌的秋之精华。还有扬州三丁包子,鸡丁是由煮好整鸡拆骨后切下的,猪肉也得肥瘦肉分开切,分开炒,完全是正经烹一道淮扬菜的架势。
这些,都跟面怎么样,干系不大。在整个长江以南的世界里,能把面发出来,折出18个褶子,已经是登峰造极的手艺。当年跟着中原政权南下的北方移民们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口袋里的小麦干粮,在扎根鱼米之乡到几个世纪后,竟然会以这样的形式,融入此地的下饭文化。

好在流浪了几千年的面团,早已练就了包容万千的肚量,能够走到哪,就把哪里的风物收入囊中,也由着那儿的气候、湿度、土壤,随意改变自己的形态,滋养那儿的人们。唯一不变的,是作为主食带来的实实在在的饱腹感,始终是那样叫人安心笃定。
往南走,人生和口味就随了稻谷;往北走,余生的好好吃饭就交付给小麦;炒菜和包子是平行宇宙里两条赛道,懂发面的不需要再研究浇头,人生已经足够富足;讲究数秒就要起锅的精细火候的,不用太在意酵母下次要放多少。厨艺有专攻,米饭和馒头,我们不能既要又要。
本期作者|Alka 梅姗姗
编辑|斯小乐视觉/创意|BOEN
摄影|《风味人间》、小红书@Aimaimai、游水过珠江女士、瞭望角的厨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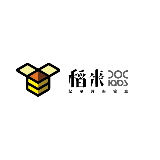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