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童年起就走在一根钢丝绳上,你在两个世界之间摸索道路,你对两个世界都没有完全的归属感。而一旦你歪向某一边,比如说现在你一下子损失了15分贝的听力,这条绳子就不见了。
在又一次听力下降后,露易丝的言语治疗师如此对她说。露易丝自小左耳失聪,右耳只能隐约听到一些声音。一直以来,她靠嘴形才能辨认别人的话语。只有光线才能让她“听”懂,让她将词语如珍珠般串起来,构成对话。有时线断了,便产生了误解,荒诞画面进入脑海,化身为奇妙的人物。
露易丝的故事,是一个面临失聪的年轻女孩与周遭世界之间的奇特关系的展现。在法国作家阿黛勒· 罗森菲尔德笔下,露易丝找工作、在水族馆散步,爱,她掉进词语的深渊,又在奇思妙想里飞升直上。水族馆里,她发现水母和其他的鱼不一样,它没有耳朵,却不妨碍感受世界。
水母的听觉器官位于其触手中间的细柄上,有一个含有听石的小球,它能够感受到海浪和空气磨擦产生的次声波,从而感知风暴的来临。因此,水母尽管没有陆地生物那样的专门听觉器官,却能够通过特殊结构对周围环境中的振动或声波有所感知。

每年九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国际聋人日。从罗森菲尔德笔下的失聪女孩自白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散落诗意与阴影的世界,并努力回答一些问题,比如语言能否描绘静默、静默如何带来偏见。
《水母没有耳朵》(节选)
撰文 | 阿黛勒·罗森菲尔德翻译 | 何润哲
工作
我重新掌控了自己的存在,开始找工作。当我以标有“残疾人士认证”的简历在求职市场海投的时候,士兵在阳光下抽烟。
我收到的第一份肯定答复是市政厅的合同岗。岗位说明含糊其辞,可谓完美匹配我的个人资料和求职动机。
几封电邮,我约上了一个大概是部门领导的人。日子到了,我开始严重怯场,想到自己可能会听不懂,我又复习了一遍自我介绍要怎么说。我要怎么才能回答关于开会还有接打电话的问题呢?我已经不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了。
市政厅离我家有三十分钟巴士车程。那是一座附属建筑,嵌在两栋奥斯曼式的大楼之间,入口是玻璃门,外立面是石膏加偏光玻璃的幕墙,显得格格不入。通过安检闸门,我来到一个小厅,里面有交错布置的蓝色塑料椅和一棵假香蕉树,看起来仿佛一个乡间小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个高个子、肤色苍白、有点驼背的女人过来找到我,软绵绵地和我握了握手,请我跟她走。
跟着她的步子往前走时,她的鼻音消散于两壁的回音之间,我推测出她在和我说话。我没法向她解释情况,只好摆出一个愚蠢的微笑,让她在回头确认我没有跟丢的时候瞥见。我不知道她是在等待我回答她之前说的话,还是已经对我有了判断,或者什么都没注意到。不管怎样,等到我走进她的办公室的时候,局势的紧张已经显而易见了。
我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安置好自己,一叠叠文件成了我们二人之间的护城河。对我来说很不幸的是,电脑遮住了她的脑袋,而且排风扇还对着我的脸吹热风,加重了我的麻烦。
“所以说,您(我在座位上扭动,好读取她的嘴唇,可那苍白的脸避开了我的视野)夏季。”
或许她是在说暑期工?概率很大。
或许她已经在询问我的暑期安排了?不可能。
或许她是在想问我有没有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可这说不通。
也有可能是“简历”,而不是“夏季”。这样的话,她可能是在面试的开头讲到我投了简历。
不论如何,我回答:“是的。”
她的棕发从屏幕后冒出来,惊讶地打量着我,又缩回自己的城堡主楼。
接下来,在一阵清嗓子和咕哝声之中,我好像听到了“做作”两个字——我听到的音节没法将我导向别的词。是我显得太做作了吗?我说了什么会这么令人讨厌?她想说什么?
愤怒将我淹没。咕哝声又开始了,越来越响。
“您知道的(叽里咕噜)我们(嘟囔)。”电脑后面的声音说。
我却只能听见狂吠、呻吟和尖叫,四周只剩下狗被虐待的惨叫。
一阵铃声突兀地响起,是火灾警报器吗?我每一个器官都开始惊恐。部门负责人在材料堆里一通摸索,从一摞乱七八糟的文件里掏出一个电话听筒。
原来只是电话呀!
我向露出四分之三的脸嘟囔了一句“您请便”以表示我不会偷听她和别人的通话,面试随时都可以继续;以上,再加上一个轻松的微笑,作为点缀。
我用眼角余光看着她的键盘,同时试图抑制住自己为失败的一天狠狠敲下撤销键的欲望。
就在这时,我感觉到小腿上一阵热气。那不是电脑排风扇。趁着对面的注意力不在我这里,我往座位下方看去,但突然一阵疼痛,让我叫出了声。一条狗——或许是德国牧羊犬,或许是捷克狼犬,或许是牛头梗——咬到了我的小腿。它用仅剩的一只眼睛看着我——另一只坏了——大口掀开,准备好再次攻击。我吓得动弹不得,只能放低目光,尽可能动作轻柔地把双脚往椅子上提,直到膝盖紧紧靠在胸口上,这时部门负责人挂了电话。
她像是被惹毛了,瞪着我。我回到得体的姿势,心里祈祷不要再被那条正用尾巴拍打地面的狗咬到。显然,部门负责人完全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
“(叽里咕噜)残疾人。”听上去像是一个问题。我能回答些什么呢?向她解释耳聋是什么感受、无助是什么体验?我可以声音不发颤地谈论这些吗?我担心的那一刻已经到来,她即将提出一连串尴尬的问题。不假思索,为了岔开话题,我说:
“‘残疾’(handicap)最初是一个马术词汇,起源于18世纪英国的赛马。当时,投注在一匹马身上的钱会被收集在一个帽子里,英文叫‘cap’。到了法国,‘handicap’这个词被用来指一种特殊的比赛,它会通过合理分摊不利因素来保证参赛者的机会均等。”
面对她的不解,我开始总结陈词:“押注在我身上,您就可以填满残疾人士就业的配额,赢得比赛!对谁都有好处!”
她站起来,向我伸出柔软的手,示意这场不伦不类的面试宣告结束。我搭上汗津津的右手,她将我推向出口。

不用上班的时候,我就渴望把自己关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比较解剖学艺廊,是我心目中结束一天愁人工作后的好去处。入口处,史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的骨架群落在风中驰骋,重新组装的骨骼会让人以为它们真的在动。这里总让我联想起某个濒临灭绝的文明,我不禁将其与我的双耳做比,就像骨传导的声音,在我的大脑皮层穿行。俗称“大海牛”的巨儒艮已经因为过度捕杀而彻底灭绝,小牌子上写着这样的话。
我转向沿着墙壁延伸的展示柜。午夜蓝的背景上,一排钟形罩里的老鼠头骨吸引了我的注意。孤独的空腔中,交错的光影让我不忍离去。
我全神贯注,都忘了身边的呼噜声:狗在秘鲁河狐的骨架前喘着粗气,发出尖锐可怖的吠叫。
在入口的正对面,是畸形陈列区。福尔马林罐子里泡着形形色色的怪物:独眼的猪、兔唇的狗、无头鲤鱼、连体羊羔。我看到旁边的说明上写着,畸形学研究的是发育异常所引起的畸形。这些异常通常是由胚胎分裂过迟或不完全,先天(染色体异常)或意外(接触有毒或放射性物质、感染)的遗传变异所导致的。
我算什么怪物呢?我想象自己被封存在福尔马林里,鼻子皱起来,耳朵朝两边打开,嘴巴微张,像是要说“什么?”(展示柜里的标准形象)。不过说到底,并没有人知道我算不算真正的怪物:我从来没有做过基因检测,我的家族成员里也没有一个是聋子。
我从脑海中赶走这幅画面,接着读说明:“在19世纪以前,此类畸形被视为偶然事件(那为什么落到我头上?)或鬼斧神工,激发了丰富的想象。美人鱼、三头犬以及荷马《奥德赛》中的独眼巨人等古老的怪物形象都是这类想象的产物。怪物们也频频出现在中世纪艺术对地狱的描绘中,例如耶罗尼米斯·博斯的画作以及教堂的三角楣饰。
在集体想象的疆域,聋子是被遗忘的。没有哪一个金光闪闪的传说是关于残破的耳朵的。人类的创世神话里,没有聋子的位置。人性中的同理心都留给盲人了。在古代中国,聋子会被扔进海里;在高卢,聋子会被献祭给天神;在斯巴达,聋子会被从悬崖上推下去;在罗马和雅典,聋子得在公共场所示众,或是丢到农村里。
俄狄浦斯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何苦呢?他本该刺穿自己的耳朵才是。这故事原本就关乎听觉:俄狄浦斯听错了神谕的意思,换言之,他是听障人士,没有听懂警告的能力。但聋子既没有盲人的辉煌,也没有盲人那哲学家般的沉静。这样的误解还在因精神分析的风靡而延续。不,说真的,这没道理,精神分析师不是眼睛也不是嘴巴,他们是耳朵。
最后一面墙通向出口,向游客展示了我觉得可以统一归于声音系统的各种器官。首先是肺——呼吸器官,然后是各种尺寸的心脏。这二者的功能是持续泵送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是它们让我们坚持活着。
羊驼的舌头、鬣狗的舌头——不知它们可会有是非口舌?——舔着自己的展室。(“再试试,你听不到‘th’这个音吗?”英语老师说,她的舌尖卡在上下两排牙之间保持不动。“再试试,你听不到‘r’这个舌尖颤音吗?这一点也不难呀!”西班牙语老师说,张开嘴巴向我展示她的舌背。)
下一个展示柜里是一组编号牌,上面钉着一个个中央有黑孔的灰色方块。我看了看说明文字,原来这些都是鱼的耳朵。旁边放了一个按钮,我按了上去,一阵剧烈的振动传来,直达我的小臂。发光板亮起,补全了说明:刚刚的感官体验展现的是鱼类感知声音的方式,即振动。
接下来,我走向下一个完全透明的方块,那里呈现的是水母的听力,与代表鱼类和人类的耳朵的黑孔截然不同。
这里没有按钮,代之以一团黏糊糊的东西。把手指伸进去,可以感觉到它像外阴一样,不时抽动。小小的发光板指出,水母没有耳朵,它们的感觉器官是负责视觉和平衡感的。我感觉自己就像水母,漂浮在团块中,什么都看不见。
牡蛎则代表了向人耳的过渡。再次滑动手指,会感觉到刺痛。发光板解释说,有一组研究人员对牡蛎放录音带,牡蛎的反应是猛地闭合,尤其是在播放低频音段时。对声波振动的感知使得它们可以听到激浪、鲷鱼和船只。
说明文字最后写道,人类的船运已影响到牡蛎的健康,因为这会让它们的开合过于频繁。
我感同身受。
相比图文并茂的鱼类、刺胞动物和双壳纲动物听觉器官展示柜,人类耳朵的展示要简单许多。只有几个内耳的取样、几片骨骼碎块和残骸,看起来就像是一艘因退潮而搁浅在博物馆的沉船,已经被高盐分侵蚀得只剩几片遗骸。
我的双耳从未能出海航行,去往其他语言。我至多只能算是水母、鱼和牡蛎的混合体。

我们第二次见面的一个月之后,托马在和安娜一起来我家喝一杯时,看到了门口摊放的听力图。
过了长到足够让我忘记这件事的时间,到了四月——那时我们刚开始“常常见面”没多久——有天晚上,他把我拖进了一个那种昏暗的角落。“我不喜欢惊喜。”可他却用一连串雄赳赳气昂昂的拟声词回答我,大概是想要激励我迈出最后一步。“我不喜欢黑洞洞的酒吧。”我又说。他拉起我的手,让我顺着楼梯下到地窖——一个空荡荡的、有拱顶的房间。石头之间的光照出了墙壁的潮湿,房间尽头有一个调音台。
一道没有一丝模糊的声响划破空气,电吉他奏出一个悬停许久的音符,圆润、饱满,声音的温度让我的喉头颤动。倏尔,声音全部消失,一片寂静中,余音回响。如此重复了几轮。我的喉咙和食道与低音共振,头骨被通电般的声膜罩住——寂静扯住记忆中残留的音符——那个最敏感的音爆燃开来,每次都是那个音,我等待许久、期盼许久的音——天鹅绒般的沉默——托马的微笑——等待中的沉默。
萨克斯管的乐声在地窖中铺展开来,填满我两肺之间的空域,高音的渐强让我口干舌燥。情感像河水一样流过我。我听见起音,听见呼吸进入乐器的吹嘴。附点音符淡褪后再起,变得更加高亢,冻结我湿润的心,为我发烧的耳朵带来凉意。尖峰林立的景象穿过灯火通明的夜,和黑白的巴黎夜景图像混溶在一起,被声音染上颜色。(托马是怎么知道《通往绞刑架的电梯》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的?)
有时,糟糕的听力会让我有超忆的症状。在最后那清晰、有力、前所未闻的独奏中,我看到托马的嘴唇翕动,为我翻译电影的对白:“我明白存在着私人生活,但私人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稳固的。电影比生活更和谐,阿方斯。”——我又看见让娜·莫罗那美丽的等待、甜蜜的恐惧,咖啡馆里的黑白画面,这等待与恐惧在我的眼中是多么光滑,那交叉的双腿和铅笔裙包裹的倦怠又是多么美呀——“电影里不会有堵车,也不会有冷场。电影像列车一样滚滚向前,你明白吗?就像夜行列车那样。”
我很喜爱《蓝色列车》。
过了一会儿,我认出了专辑中第一支乐曲开头的旋律。那些音符流入我,仿佛从未抵达过我一样。
我之前曾和托马说,萨克斯管的乐声是最接近人声的东西,有时我甚至会混淆两者。
于是他给我写了迈尔斯·戴维斯的这句话:“真正的音乐是沉默,所有的音符都只是沉默的框架。”他以此劝诱我接受:沉默先于声音。
最后,当低音穿透过来,钢琴接续上时,我一定是高兴得哭了出来。我听到了每一件乐器。
这怎么可能?“你还记得那张听力图吗?”托马把它交给了他的一位做舞台监督的朋友,他根据我的听力曲线调整了所有的频率,让每一个音都可以抵达我。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水母没有耳朵》,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按语写作:徐鲁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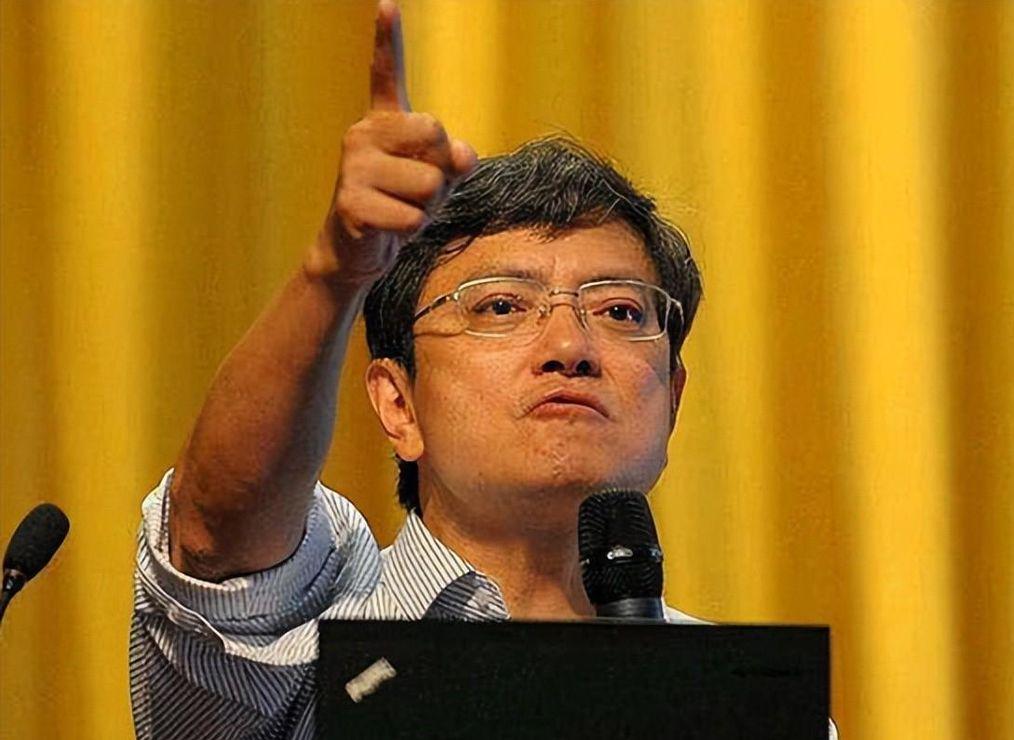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