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首发于豆瓣(ID:Surnager),标题系《我们还可以如何向历史发问?告别“天真的野蛮人”和“创世纪神话”,重提社会实验与政治自觉》。

01
如何向历史发问?
告别“天真的野蛮人”和“创世纪神话”,重提社会实验与政治自觉
“在卖弄学问与老于世故之人的鼓励下,我们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习惯于将幸福看成是愚蠢的。”
格雷伯和温格罗在《人类新史》的一开篇就表达了对历史进化论的不满,这种陈旧的历史叙事在他们看来不仅有误,而且十分无聊。人类原本生活在平等但匮乏的狩猎采集社会,但因为农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人口增长、私有财产、阶级分化、城市革命和国家起源,使人类不可挽回地奔向文明的锁链,这几乎是《创世纪》中关于人类偷食禁果最终招来永久堕落的翻版。虽然包含着对现代文明的悲观与不满,但这样的叙事通过将人类历史的复杂性捏合在一条直线上,最终使得现代人将当下视为不可改变的历史进程中的一环,认为历史上存在的关于平等和自由启示以及人类幸福的可能都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从而哪怕不认可也不得不接受如今一切制度安排,这就是进化论暗含的政治影响。出于对以上简化的、僵化的和说教性的历史的不满,格雷伯和温格罗利用新发现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材料,进行了一次改写历史的尝试,他们不再徒劳地追问一切关于“起源”的问题,放弃了目的论的历史观之后,他们提出的新问题是:“如果我们看重的是谷物驯化没有导致产生养尊处优的贵族、常备军或债务奴役的5000年,而不是导致了这一切的5000年,将会怎么样?”换言之,他们发问的不再是究竟是人类命运之环的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最终一路导致今天的困局,而是在那些拒斥今日困局的同样漫长的历史中,我们能不能学会想象不同的生活方式?
虽然在这样的表达中事情变得非常简单,但进化论及其变体在现代社会的根深蒂固,使得拆解其中的一系列预设并提出新发问成为一个庞杂的工程,这不仅涉及重新解读农耕、城市和国家,还需要审视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欧洲中心论和殖民权力,重建一个关于交流的空间。

▲逐出伊甸园,米开朗基罗,梵蒂冈西斯廷教堂
02
漫长却无聊的“进化”:世界历史中被排斥的“他者”与“她”
进化论讲述的狩猎——采集、园耕、农耕、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以及相对应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的政治发展阶段,在启蒙时期的欧洲存在着两个神话变体——霍布斯的利维坦和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两个版本的故事分别宣告着文明的胜利和文明的危机,使得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理论不过是在二者之间摇摆或取舍。霍布斯讲述的是一个早期一切人以一切人为敌的故事,这使得割让个人权利建立国家变得必要;卢梭则讲了一个早期人类生活在无忧无虑但离群索居的孤独的童话,但随着私人财产的诞生人类从此永远告别童年。这虽然是极其不同的故事,但都指向启蒙时代欧洲关于国家、等级制的重大争辩。在以往的讲述里,这种争辩是欧洲意识理性化发展的结果,但在一个等级制拥有长期历史的社会里(如法国),人们为什么能够开始频繁想象一种平等状态?如果认为这是欧洲社会新出现的资产阶级要求等级制的变革,那么想象一种新等级制显得要比想象一种完全的平等要更有说服力。这意味着如果坚持启蒙精神产生于理性的自我发展,那么社会之外的“平等”就只能说成是从天而降的神启,格雷伯和温格罗显然不能只满足于此,他们选择走出理性内部,发现启蒙时代同时是欧洲殖民扩张的时代,而在与美洲新大陆接触的过程中,殖民者带回的原住民故事和批判,成为启发欧洲进行自我反思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现代自由、平等、民主之精神,是由与被贬斥为“原始人”、“野蛮人”进行接触和交流所带来的。
格雷伯和温格罗在书中引用了美洲原住民政治家坎迪亚洪克对欧洲社会的批评,他无法理解欧洲人为什么彼此争吵、缺乏互助、盲目服从权威,而且能够把财富直接转化为对其他人的权力。以坎迪亚洪克为代表的原住民批判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很大的波澜,几乎所有闻名的启蒙思想家都曾承认其所带来的反思。讽刺地是,原住民批判对欧洲文明优越性的动摇刺激了欧洲的回应,社会进化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进化论者杜尔哥看来,野蛮人的平等与自由恰恰是他们的劣势,因为只有在一个家家户户都自给自足且人人同样贫困的社会里,这样的平等和自由才能存在,而欧洲技术的进步、劳动分工的发展才是社会繁荣的表现。就这样,平等主义被转换为社会进化阶序最底层的特征,而欧洲与原住民之间的地理区隔也由此被转换为时间区隔,活人被化石化了。同时,进化论也因此成为优越文明改造落后文明的殖民主义的辩护者,但这也制造了殖民帝国自己的短命,因为他们声称自己只是加速其统治对象走向文明的暂时工具。
至此,进化论的建构属性和知识生产背后的殖民权力都被提交出来,这首先动摇了它渴望宣称的科学性。同时,进化论的排斥性也被提交出来,这意味着被殖民者的历史、生活、思想没有被认真地纳入考虑,而只是作为自我尊严破裂后条件性反射的拒斥被划归到无足轻重的位置,从而进一步确认自己长满虱子的霸权。尽管格雷伯和温格罗没有非常明确地强调女权主义的立场,但在对进化论的批评和新发问中,他们同样强调了在进化论框架下发展出的世界历史对女性历史的贬低与排斥,通过将提出“母权制”的女性学者污名化,通过把很多女性实践和集体生产的生活经验和技术演变窃取为男性力量主导的技术变革,进化论最终确认的是白人男性的中心地位,并还在持续不断地生产着种族和性别的身份范畴。

▲ 加泰土丘出土的泥塑女性坐像,年代在公元前 6000 年前后。
这尊著名的塑像最初被解读为一位“母神”
03
依次挑战“农业—城市—国家”这一简单却令人满意的历史发展路径
在进化历史的框架里,农业的出现被视为文明的起源,这意味着人类开始驯服物种并定居,由此带来了剩余劳动产品和人口增长,最终导致复杂城市与等级化社会的出现,而要管理其中的分化则需要建立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国家。这个推论太顺理成章了,以至于听上去像一个逻辑演算而不是真实历史,格雷伯和温格罗正是从这一推论出发,以此拆解了其中的论证环节。
对进化论的拆解首先来自于对农业革命的质疑,即将农业视为从狩猎—采集状态发生的根本性的生产方式的突破与发展。第一部分的证据来自萨林斯所提出的“原初丰裕社会”,其反对将狩猎—采集者视为处于极度贫困依靠辛苦劳动只能勉强填报肚子的预设,而是指出在原初社会中人们花非常少的时间就能养活自己,因此休闲、游戏得到尊重和发展。相关的考古证据还有历史上农业总是发展于自然条件贫瘠的边缘地区,这否认了从狩猎—采集到农业是一种事实上的进化。其次,通过提出往往被忽略的关于季节性集散的材料,他们进一步否认了生产方式的变迁所带来的定居式的生活是一步到位的,即开弓没有回头箭。人类历史上纪念性建筑的冰期遗址,以及人类学关于南比夸拉人、因纽特人和夸扣特尔人的民族志材料都显示,历史上存在着季节性集散的社会生化方式,即按照一年中不同的时期,人们会不断地分离形成小游群从而保持无政府状态,也会从小游群聚集成大型社会并产生等级制甚至是集权,这意味着“随着一年中时间的变化,会变成另外的人”。而生活在大平原上的农民部族在过上游猎生活后,基本上也放弃了谷物农业,这也意味着历史上的大多数人并不像进化论假设的那样被困在单一的社会存在模式和生产方式之中,而是用于从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和灵活性,他们进行农耕但不成为辛苦农民,他们的农业活动更像一种在阿多尼斯的花园里“种着玩”,因此他们的社会里耕种活动和狩猎、采集并存,拥有多种事物源可以使自己不必受制于农业,这一切更像一种“自由生态”。所以,农耕并没有进化论所宣称的那样拥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性。再进一步,农业必然导致私有财产和不平等的出现也是站不住脚的推论,因为在很多社会里,财富的差异从来没有转化为发号施令或使人屈从的能力,农业与不平等并不存在必然关系。而农业与私有制的绑定关系更为致命的后果是其否定了原住民对土地的自然权利,因为他们没有在土地上耕种(劳动),所以这些被用于狩猎—采集的土地属于闲置土地,因此可以被殖民者占领。通过对农耕的重新梳理,格雷伯和温格罗想指出的是,农业革命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一场爆发后迅速蔓延以至于将世界进程推向牢笼的事件,相反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在有意识地拒绝彻底成为辛劳的农耕者,拒绝与物种的双向驯服,拒绝由此可能导致的不平等状态。农耕不是一场进化历史中的突破点,而只是早期人类进行的一项社会实验,当时人们依然保有退出、转变的自由,以及让尝试之后发现并不幸福的社会实验付之一炬的慨然。

▲夸扣特尔面具舞者(Edward S. Curtis 摄,1907)
接下来,格雷伯和温格罗着手拆解关于城市的进化假设。城市原本是接在农业 发展的后面,随着人口聚居和规模扩张而带来的结果,意味着大型社会和复杂分工、管理的出现。但亚欧大陆冲积平原的例子恰恰说明生态因素是城市产生的诱因,而粗放农业可能是城市产生的结果而非其原因。进一步,格雷伯和温格罗对城市概念的侧重点进行了从物质实体到观念想象的转换。正如卡蒂内所说的,“城市诞生于头脑中”,这是在说尽管人们认为自己生活在城市里,但其真正生活空间也许仍然只是小群体,超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实际上是“看不见的人群”,其只存在于想象之中。通过将城市从根本上看作是一种想象而不是拥有固定规模的实体,他们指出:“觅食者或许有时以小群体的形态出现,但他们并不,或者说从未,生活于小规模的社会之中。”这是因为在早期的共居群体中,人们并不是按照血缘亲属的关系构成的,亲属关系更像是一种隐喻,支撑着早期跨越远距离的迁徙,因为人们相信自己远离亲人也依然能找到招待之所,在他们的想象里,“看不见的人群”同样存在。因此“城市本身和早期绵延百里的氏族或半偶族聚落差不太多,它只是一个首先存在于人类想象中的结构,在其中未曾谋面之人也能和平共处”。同时,存在一定实际规模的聚居城市也不意味着对环境的极尽利用、对他人极尽剥削。乌克兰的超大遗址、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墨西哥谷底的特奥蒂坎城都在验证着大规模聚居下平等、民主、互助的可能性,特奥蒂坎城甚至启动了非凡的社会住房工程。相反,我们今天很熟悉的贵族制和彰显暴力的英雄社会恰恰出现在文明城市的边缘,他们对平等主义的城市“归根结底是充满敌视和怨恨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早期所有城市都是平等的,而是说我们可以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视为自觉的社会实验场:“在那里,对于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同见解可能会引发冲突,这种冲突有时的和平的,有时则爆发出惊人的暴力。”
最后一步我们进入政治的领域,格雷伯和温格罗像放弃不平等的起源一样放弃了对国家的起源的探索,相反通过对历史和当代不同政治实践的梳理,他们确认了社会权力的三个可能的基础:暴力控制、信息控制和个人魅力,分别对应主权、官僚制和竞争性政治场域。历史上的大多数政治体要么以其中一个作为主要基础,要么突出其中两个,因此被称为“一阶”和“二阶”的支配政权,而现代国家事实上是各种元素在人类历史某个时刻偶然汇聚的产物。而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权力形成过程,各有其独特的对暴力、知识和魅力这三种基本支配形式的组合。从主权来看,历史上存在很多没有“国家”的主权,当统治者以“大太阳”或神明等一类至高无上的权力出现时,也同时标志着主权的范围:在范围内是绝对的,在此之外则迅速减弱。暴虐的主权者令人恐惧、具有破坏力且是非常神圣的,尊严使得他们“不能触碰地面”、“不能直视太阳”,从而限制了行动自由,“神圣国王自己将面临仪式性死亡”。同样,官僚制也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社会发展超出一定规模和复杂度时作为解决信息管理问题的实用方案才出现的,而多诞生于仪式性情境中。三个基础的提出意味着在谈论历史上的政治实践时,我们无法谈论“国家”的起源,因为这只是一个自我论证的命题,我们谈论的只是广泛的区域系统,在实践中,整个区域系统碰巧被单一政权统一了,或统一只能存在于理论中,或区域性霸权很少能维持超过一两代人,或两个主要势力集团旷日持久地争斗不休却胜负难分,这意味着“事情总有调整的余地”,也意味着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都假定存在着三种原始自由:迁徙的自由、不服从的自由和创造或改变社会关系的自由。
04
重新发问,重新回答,重新想象: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
格雷伯和温格罗在《人类新史》中不仅挑战了进化论的抽象化、简化和背后的政治权力,同时还对其内部一环扣一环的推论以此进行了挑战。通过不只是将原住民视为“天真的野蛮人”或“高贵的野蛮人”,他们拒绝对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存在的人的简化和浪漫化(虽然本文中引述的例子还是有浪漫化的嫌疑,所以推荐大家读原文),而是致力于将他们视为和我们一样拥有同等反思能力的人,并进一步追问我们可以从和他们之间跨越时空的交流中学会些什么。因此,在这里,他们并不去追问关于不平等、国家的起源,好像真的存在一颗导致一切灾难的种子,相反,他们追问的是历史上人们努力保持自由、平等的实践是多么复杂、不稳定但也因此总是保有希望的。但也正如我们所知,大多数对人类历史的探究并不完全致力于复原历史,而经常是试图理解当下的努力尝试,所以既然拒绝了“不平等的起源”这样的追问,格雷伯和温格罗还是需要回应“我们的现在究竟怎么了”这一问题。通过放弃寻找一个必然导致一切的因,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灵活的实践在今天却仿佛僵化了?我们为什么失去了历史大多数时期人们都拥有的退出、重建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提问,因为其避开了历史目的论,将我们的当下也视作一种偶然性,只是这种偶然的结果呈现出可能前所未有的约束力。
格雷伯和温格罗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非常详细的回答,但通过使用文化区的概念,他们将文化视为“拒绝的结构”,即相邻的人们总是通过强调与邻居的不同来标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认为这种夸大差异、制造身份的实践需要为今天的困局负有一定责任。随后,他们也强调战争暴力的作用,即尽管早期的政治实践很可能是人们演着玩的过程,但当国王扮演者开始杀人的时候,他就不再是扮演的国王了。战争的暴力不仅维持了边界,还把另一团体的社会成员视为可被替代的,这种“社会的可替代性”是对具体的人的抽象暴力,与之相关的还有官僚化对承诺的去个人化和可转让化,在这种抽象化暴力和战争暴力中,人们玩乐、扮演的权力仪式中出现了永存的欲望。在对暴力的进一步描述中,格雷伯和温格罗还提到了暴力和照护的组合,在对史坦纳“一切都源于慈善”的引用中,他们非常迅速且隐晦地提出一个和《狗屁工作》结尾用SM(施虐/受虐)解释对工作的忍受一样大胆的可能,即早期社会中提供庇护的过程常常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这里可能在暗指父权制的强化),而外部暴力往往又与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地位变化有关,这也就是说有可能是慈善与仁爱之心在实践中偶然地变质将我们带到了不知是何处的地方。

▲《人类新史》书影
在重新追问历史、现在的过程中,格雷伯和温格罗提醒的是进化论不是一种事实而只是一种神话,努力重建的是一种偶然性,一种作为人的反思和政治自觉,以及社会作为一次实验的可能性,这种重建其实是将我们引向未来:如果我们从来都不只是被推着向前的人,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停下来想象一下过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我们是否依然握有改变未来的权力?
推荐书籍

《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
作者: [美] 大卫·格雷伯 / [英] 大卫·温格罗
译者: 张帆 / 张雨欣
定价: 128.00元
丛书:智慧宫
思索人类社会的命运时,我们总会借助大历史的广角镜头。可耳熟能详,甚至被默认为公理的人类发展叙事——从人人平等的狩猎采集小游群到现代民族国家,历经“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国家起源”等关键节点——真的反映了事实吗?《人类新史》向我们揭示出,这或许只是一个现代版本的起源神话。
两位作者追本溯源,发现上述理论其实源自18世纪美洲原住民对欧洲殖民者的批判,以及欧洲人做出的保守反击。随后,作者们综合考古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近年来涌现的突破性成果,展示了人类实际上有过怎样多元和流动的社会组织形态,历史的道路又有过多少分岔与并行。重新理解人类的过去,重新发现人类本就拥有的其他可能性,或许也能赋予我们新的思想资源,去想象一个更具希望的未来。
京东首发,下方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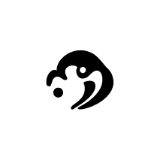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