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马克·C·威尔逊(《美国数学会通告》前主编)于2025年4月主持的Zoom线上会议内容编辑整理稿。受邀参与者均为知名获奖作家,长期致力于向大众普及数学知识,其讨论对数学之外的学科的科普工作一样会有启示。

左上KD:Keith Devlin 基思·德夫林,斯坦福大学名誉数学家
左下MdS:Marcus du Sautoy 马库斯·杜·索托伊,牛津大学公众科学理解西蒙尼教授
中上JE:Jordan Ellenberg 乔丹·艾伦伯格,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约翰·D·麦克阿瑟数学教授
中中SH:Sarah Hart 莎拉·哈特,伦敦大学伯贝克计算机与数学科学学院的名誉教授
中下JAP:John Allen Paulos 约翰·艾伦·保罗斯,天普大学数学教授
右上SS:Steven Strogatz 史蒂文·斯特罗加茨,康奈尔大学科学与数学公众理解Susan and Barton Winokur杰出教授
右下MW:Mark C. Wilson 马克·C·威尔逊,《美国数学会通告》前主编
作者:AMS(美国数学会)2025-12-20
译者:zzllrr小乐(数学科普公众号)2025-12-21
面向大众:六位作家谈公共数学科普

马克·C·威尔逊(MW):开展公共科普的重要意义何在?
基思·德夫林(KD):当然,从历史上看,人们认为良好的公众形象有助于争取国会拨款——不过现在这一点可能已经不成立了!
萨拉·哈特(SH):我们不能总是自嗨,对吧?关键是要让人们明白,数学是一门美丽、奇妙且令人兴奋的学科。它不只是用来报税、丈量房间之类的工具,更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探索。我们必须把这份乐趣分享给大众,否则怎么能吸引更多人投身数学呢?
KD:如果不是那些通俗数学读物,我可能根本不会走进数学领域。我来自一所小型学校,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没有任何学术背景,也从未接触过这类知识。但不知为何,我偶然读到了一些通俗数学书,书中的内容和学校里教的那些枯燥乏味的东西完全不同,让我深深着迷。
那时候科普形式很少,这类书籍也不多——兰斯洛特·霍根(Lancelot Hogben)的《大众数学》
Mathematics for the Million、W·W·索耶( Sawyer) 的几部作品,正是这些书点燃了我的热情,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相信有同样经历的绝不只我一个人。现在科普形式丰富多了,比如YouTube上的科普视频,肯定也在吸引着更多人关注数学。学校的教学往往以应试为导向,即便教学质量不错,也很难传递数学的趣味性。而这种乐趣,需要通过其他不同的场景来呈现。科普内容越丰富,就越有可能让更多人爱上数学。
SH:完全同意。雷蒙德·斯穆里安的《模仿一只知更鸟》
To Mock a Mockingbird和罗杰·彭罗斯的《皇帝新脑》
The Emperor’s New Mind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我正是在后者中了解到了图灵机。这些书让我重新认识了数学的可能性,但在学校里,我们只需要学习解题技巧(虽然有些技巧也挺有趣,但始终缺乏那种探索的喜悦)。部分原因在于,高中阶段的一些数学老师本身可能对数学并不自信。
在英国,数学教师缺口极大,很多被说服去教数学的人,自己未必热爱这门学科。所以教学中往往只是死记硬背——比如“这是解决这类问题的算法”,却不会告诉你“这太有趣了!用三角形的知识,仅凭一根棍子就能测量地球周长,这简直是天才的想法!”。正是这些通俗书籍,常常成为人们走进数学世界的敲门砖。
史蒂文·斯托加茨(SS):说到童年回忆,我想推荐纽曼的四卷本《数学的世界》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高中时,我常常在图书馆里花好几个小时读庞加莱的散文,还有哈代回忆收到拉马努金来信时的文章。
不过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除了为受众和学科带来的诸多益处,科普对我们自身也大有裨益。众所周知,通过教授或解释某个知识点,你能更深入地学习,思路也会变得更清晰。而且我们都热爱数学,这也是我们投身于此的原因。
当你为大众写作时,你可以尽情沉浸在自己热爱的事物中。虽然这算不上“官方认可”的理由——说“我做科普是因为它能让我快乐”听起来有些自私,但说实话,除了那些利他的原因,这确实是很多人坚持科普的重要动力。其实这两者并不冲突。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面向大众的科普,但数学家之间的沟通通常也并不顺畅,与相邻领域科学家的交流也是如此。我认为我们的书籍和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弥补这些沟通鸿沟。
科普不一定非要面向完全没有数学基础的读者。对于《美国数学会通告》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想“我能参与科普吗?如果我写得不如乔丹或萨拉怎么办?”其实你完全可以为其他数学家,或者像马丁·加德纳的读者那样本身就喜欢数学的人,写一些通俗易懂的内容。你不需要说服他们喜欢数学,他们只是希望得到清晰易懂的解读。
科普的受众是多层次的。我个人特别喜欢挑战那些“数学恐惧症”患者,那些看似最难打动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但从极度害怕数学的人,到原本可能成为数学家却选择了当医生等其他职业的人,科普的受众涵盖了各个群体。
科普书籍中完全可以包含大量公式。斯蒂芬·霍金曾说过,每增加一个公式,书籍销量就会减半。但如果你去问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出版的《虚数的故事》
An Imaginary Tale: the story of √-1或《常数e的故事》
e:
The Story of a Number这类包含大量数学内容的书籍,销量都高达数万册。撰写这类富含专业数学知识的书籍,完全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它们可能成不了《纽约时报》畅销书,但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都算得上非常成功的作品。
马库斯·杜·索托伊(MdS):一个令人意外的收获是,科普能帮助我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我原本以为科普是单向的付出——启发下一代、让政客认识到数学对社会的重要性等等。我从未想过自己能从中获得如此多的数学启发,尤其是在写我的第一本书《素数的音乐》
The Music of the Primes时。
我一直知道黎曼猜想是数学中最伟大的未解决问题,但直到撰写这本书时,我才真正明白其中的缘由——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我本身就是研究数论的。但确实,通过写这本书,我才真正理解了它的意义、起源以及为何如此重要。希尔伯特也曾说过(这句话的起源可追溯至更早——详见 https://quoteinvestigator.com/2021/09/30/street/ ),只有当你能向一个没有专业知识的人解释清楚某个领域时,你才算真正理解了它。所以对我而言,这是科普带来的意外收获,对我的学术研究也大有裨益。
此外,我们做科普也是为了回报那些曾激励我们走上数学道路的人。我读过基思的书,正是这些书以及伊恩·斯图尔特( Ian Stewart、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等人的作品,让我爱上了数学。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科普也是在说“基思,非常感谢你写的那些书”。
MW:当你们因公共科普而广为人知时,遇到的最大惊喜是什么?
乔丹·艾伦伯格(JE):受众的规模和公众的热情程度。我们这些大学教师,平时面对的学生中,很多人其实并不是自愿来学数学的。他们虽然态度认真、努力学习,但选择这门课并非出于自愿——是别人要求他们来上的。这是我们工作中很常见的情况。
但出版界的人都知道,有很多人会主动走进书店,自己花钱购买数学相关的书籍,还会发邮件向你提问,这真的非常令人振奋。多年来,作为公立大学的从业者,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使命不应仅限于教育18至22岁的在校学生。
KD:我为《卫报》写的第一篇文章(其实是第二篇,第一篇没被发表,但他们让我再试一次)大获成功。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档儿童新闻节目注意到了这篇文章,邀请我去伦敦录制了一个片段。我当时想:“我在向全英国的孩子传播数学知识,这太有意义了。
我是以一名真正数学家的身份和他们交流,即便我表现得有些笨拙,或者说有点古怪,这也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不过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自己当时表现得还不错。但从那以后,我突然成了一名数学科普作家。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能接触到大量受众。但这也招致了同事们的负面评价:“居然上儿童电视节目!”我当时显得格格不入。但大约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时候做科普的只有我和伊恩·斯图尔特。有趣的是,我从未见过他本人。我们曾合作撰写《千禧年七大数学难题》一书,但从未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SS:对我来说,最大的惊喜来自中小学教师。就像乔丹说的,很多人对数学科普有着强烈的需求。我们通常认为科普是为了吸引学生、培养年轻人对数学的兴趣,但萨拉提到,很多教师本身也是在应试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非常渴望获得我们能提供的那些生动有趣的数学内容。他们通常会主动给你发邮件。
同样,家长们也可以看作是广义上的教育者。所以科普的受众不只是孩子,还有那些与孩子打交道的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工作,同时也丰富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之前从未意识到,有如此多的人能从这类科普工作中受益。
MdS:上周我在布莱克韦尔书店买书时,收银员登记我的名字时被旁边一位男士听到了。他说:“天啊!真不敢相信能见到你。我10岁左右读了你的《数字奥秘》
The Number Mysteries,从此就爱上了宇宙形状以及用数学理解宇宙的想法。现在我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微分几何博士学位。”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还说:“没想到见到激励我的人会这么激动。”
我的一个博士生也曾告诉我:“我12岁时在新西兰听了你的演讲,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要和你一起工作。”后来他真的来到牛津,敲开了我的门,说:“我想跟着你读博士。”现在我们正在一起写论文。对我来说,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小时候曾受教于克里斯托弗·齐曼(Christopher Zeeman),他在1978年做过英国皇家科学院圣诞讲座(英国皇家科学院自1825年起每年举办的公共讲座——详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yal_Institution_Christmas_Lectures )。像他这样杰出的数学家,愿意花时间撰写讲座并向我们这些孩子传播知识,真的非常令人敬佩。
2006年,当我受邀做圣诞讲座时,我终于有机会向他致敬——告诉他我曾是1978年的听众。基思,我上六年级时(大致相当于美国的高中低年级或高年级学生),曾把你发表在《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贴在墙上,因为那篇文章让我深受启发。有趣的是,多年后我偶然找到了那篇文章,发现有一个人给你写了回信,而那个人后来成了我的博士生导师。所有这些看似偶然的联系交织在一起,正是这些个人故事,让科普工作变得意义非凡。
约翰·艾伦·保罗斯(JAP):这些年来,我收到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信件,有人说因为我才选择主修数学,也有人说非常喜欢我某一篇文章。有一次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当时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一个年轻人跑过来对我说:“我喜欢你的书,得知你要来,我太激动了。”这真的非常令人欣慰。
我总是会满怀感激地回复这些信件。我记得自己年轻时曾给马丁·加德纳写过信,当收到他的回复时,我欣喜若狂。信不信由你,我们后来还就荤段子展开了长时间的通信。所以,因恰当的原因而知名,这是科普带来的一个积极方面。
SH:我同意大家的看法。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对我产生了影响”,这真的非常令人满足。此外,由于我的书是关于文学与数学的,我有时会受邀参加文学节。那里有很多人原本认为自己不喜欢数学,但活动结束后,有人会过来对我说:“我上学时从来都不喜欢数学,但这个内容太有趣了,也许我以后会更愿意接触数学。”这对我来说是真正的积极反馈。
我们都曾受到过他人的影响,对我来说,这个人是大卫·辛马斯特。他碰巧是我父母的朋友。我母亲曾在现在的伦敦南岸大学上晚间计算机课程,大卫是她的老师。他曾给母亲展示过一种“柔变体”(flexagon)的玩具,母亲对此非常感兴趣,他们也因此成了朋友。他偶尔会来我们家做客。
我父母举办夏日派对时,他就像夏日圣诞老人一样——一个留着浓密大胡子的老人,口袋里装满了各种谜题和游戏,而且他会平等地和你交流,仿佛你是值得他认真对待的人。很多人在和教授交流时会感到拘谨,但我小时候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却截然不同——这位数学家会像对待平等的朋友一样,和我讨论谜题和游戏。
这种经历非常宝贵。所以对于所有参与科普的人来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你是权威,是专家,人们会为有机会和你交流而感到无比兴奋。这正是科普工作带来的真正乐趣。
MW:对于那些有意参与公共科普的人来说,需要注意哪些潜在问题?
SH:我觉得我们迟早得谈谈这个话题。我不知道你们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过,但作为女性,我有时会收到一些不受欢迎的关注。比如收到不友好的邮件,或者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不当言论。我不知道男性是否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也许会吧。另外,还有些人会非常急切地想要和你交流、见面,甚至会给你发他们所谓的“四色定理证明”——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遇到。
只要你是稍微有点知名度的数学科普工作者,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必须考虑是否以及如何回应。因为如果你回应了,告诉他们“你的第三个论点有误”,他们就会回复“我已经修正了”……所以你必须谨慎,尤其是女性,要考虑好自己的联系方式是否公开。我认为大家需要明白,如果你不想回复某人的邮件,完全可以不回复。我们都很有礼貌,但有时候不回复反而更好。
JAP:我偶尔会写一些与政治相关的内容,至少是涉及政治中的数学层面。经常会收到一些邮件说:“做好你自己的事,你这个书呆子数学家,你懂什么政治?”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支持者。但这并不会困扰我,事实上,他们不喜欢我,我反而觉得有点受宠若惊。
KD:我以前为《卫报》写稿时,曾和一个人有过长期交流。他是一名退休教师,给我的感觉是个聪明人——他问的问题很有意思,也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我们的书信往来持续了好几个月,后来突然中断了。不久后,他的遗孀给我寄来一封信,说:“在我丈夫生命的最后七八个月里,你一直陪伴着他,他当时正身患癌症,是你给了他慰藉。”
我非常震惊,没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竟然成了他重要的精神支柱。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的情况,本来我完全可以敷衍了事,但我一直耐心地回复他的信件。现在想来,我很庆幸自己当时这么做了。
JE:我觉得萨拉说得非常对。作为男性,我在公众视野中几乎不会遇到什么风险,但女性可能就不一样了。萨拉,你觉得写作和公开露面这两种形式,所面临的情况有区别吗?
SH:单纯写作可能会好一些。我曾做过格雷沙姆学院的讲座,这些讲座会被上传到YouTube上,获得了很多观看量。众所周知,女性演讲者在YouTube视频下收到的评论,和男性是完全不同的。我从中学到的经验是:永远不要看评论。这让我开心多了——这也是我的建议。
书面形式的互动肯定会少很多,而如果是做视频、电视或广播节目,可能会收到一些负面反馈,但你完全可以选择不回应。当然,如果有人真诚地发邮件问我问题,我还是很乐意回复的,我喜欢这种交流。
JE:我也要抱怨一下,和萨拉一样,可能在座的每个人都经常收到所谓的“黎曼猜想证明”。但就在过去一年左右,有人开始给我发ChatGPT生成的“黎曼猜想证明”。拜托,能不能尊重一下数学!以前人们还会自己动手做错误的证明,现在的人怎么这么懒?
MdS:我也建议大家不要看评论区,因为如果有人真的有有价值的想法,他们肯定会直接联系你。但我在做科普相关的演讲时,总是会告诉大家:你必须脸皮厚一点。你既然站出来做科普,就难免会受到批评。
我为《泰晤士报》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收到了两封信,我本来还很兴奋,结果两封信都是攻击性的——我很快就学会了适应。那天我去学院吃午饭时,一位也为《泰晤士报》撰稿的历史学家对我说:“我很喜欢你昨天的文章,收到奎克小姐的信了吗?”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每次写文章她都会给我写信,你慢慢就习惯了。”
我记得还有一次,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后看了评论区,里面全是反犹主义的谩骂:“你为什么嫁给犹太人?为什么让你的孩子以犹太人的身份长大?”我当时就想:“这和我的文章有什么关系?”所以你必须脸皮厚,总有人会想方设法攻击你。
MW: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写作方式需要做哪些调整?
SS:我们这个行业非常注重严谨性,要求不能有任何错误。但面向大众写作、演讲或制作YouTube视频时,完全不犯错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我想引用伟大的概率论专家马克·卡克(Mark Kac)的话:“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但不必说出全部真相。”这句话非常有用。不要撒谎,但可以省略一些内容,把它们放在文末的注释里。
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学术训练让我们在面向大众写作时过于拘谨,因为确实需要做出一些小小的妥协。有些人把这称为“降维”,但我不这么认为——这需要技巧。如果把学术写作中那些繁琐的细节和警告都写进去,只会让文章变得晦涩难懂。要做好科普写作,真的非常不容易。
JE:我一直在尝试研究如何培养学者的外向型写作能力。我曾为研究生开设过相关研讨会,现在还在教一门大一课程。这些学生还不是学者,但他们所学的写作方式,都是为了完成课程论文,是典型的学术写作风格。
我逐渐意识到,要做好科普写作,不仅需要学习新的技巧,还需要“忘掉”一些旧习惯。像我们这样的科学家,有些写作习惯本身并没有问题——它们在专业写作中非常有效且正确,但在面向大众写作时就不再适用了。
另外,学术数学写作非常看重创新性,但这也是我必须学会放弃的一点。如果我只写那些从未有人科普过的内容,那我可能永远也写不出任何东西——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很多基础内容已经被反复科普过了。
我必须学会的是,如果我有新的视角,或者觉得某种表达方式更有吸引力,就不必纠结于“马丁·加德纳是不是已经写过了”。有些内容可能确实已经有人写过,但我们的受众可能从未读过。每天都有新的人想要了解数学,总有新的受众群体。我们不会去重复发表已经发表过的学术论文——即使有人没读过,他们也可以去读原始论文。但科普写作则完全不同。
SS:我更愿意把科普写作比作音乐。埃拉·菲茨杰拉德有她的演绎版本,萨拉·沃恩也有她的风格,而我两个版本都想听。如果萨拉·哈特还没写过关于《白鲸》
Moby Dick的数学科普,我非常期待读到它。
SH:严谨性这个点非常关键。你可以明确告诉读者,你不会深入讲解细节——如果是数学家读者,他们自然会知道定理存在一些适用条件或限制。你只需说明“该定理存在一定的适用条件”,而不必详细列出这些条件。
我写《昔日盛世——数学与文学之间的奇妙联系》
Once Upon a Prime——
The Wondrous Connections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Literature时,第一次有了编辑。我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先写很多细节,然后编辑会说“这个可以放在注释里”,我同意了。大约两个月后,她又会说“这个注释可能也不需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参阅)
MW:如何避免自己成为故事的焦点,从而掩盖了内容本身?是否应该避免这种情况?
SS:我的第一本书《同步》
Sync中就加入了自己的经历。这本书主要讲述世界上各种事物如何自发同步的科学和数学原理,以及相关的数学描述。因为这是我一直在研究的领域,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的经历写进去是合适的。
我并没有把自己和诺伯特·维纳相提并论——我明确表示自己只是这个领域的一名普通数学家,或许读者会想了解,作为一名不必成为罗杰·彭罗斯或斯蒂芬·霍金那样的顶尖学者,普通数学家的工作日常是怎样的。
所以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写成的。我确实担心这会显得自我吹嘘,所以在书中加入个人经历是一件需要谨慎处理的事情。但事实上,适当的个人经历可以让故事更生动,有时候也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我曾给一位刚进入数学科普领域的人提供建议。她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第一位密码学负责人,作为如此有影响力的女性密码学家,她的个人经历本身就应该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密码学的数学原理。
她一开始非常不愿意把自己写进去,但我说:“我真的觉得这会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故事,让它更有趣。如果你觉得合适,而且有一位好编辑,你完全可以做到不显得尴尬。”我不知道她最后有没有采纳我的建议。
我喜欢带有个人风格的科普作品。比如约翰,你写的东西辨识度很高,因为你有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我很喜欢。我知道这是约翰·艾伦·保罗斯的作品,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犀利的评论,但这种独特的风格非常有趣。我觉得你不应该收敛这种风格,当然你也不会收敛——因为这就是你,这就是你的写作方式。
JAP:非常感谢你的赞美。总的来说,在文章中适当展现自己的个性是有帮助的。我并不是刻意为之,但效果确实不错。如果你写一篇全是引理、定理、推论的文章,肯定没人会读。但也要把握好度。我很喜欢尼尔·德格拉斯·泰森,但我觉得他有时候有点过于突出自己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总的来说,展现自己的真实一面,用个人化的方式谈论数学或相关话题,是很有帮助的,就像视频比文字更有吸引力一样。但同时也要避免成为令人难以忍受的自恋者、自我吹嘘者或偏执狂。
SS:基思,能谈谈你的《斐波那契》一书吗?
KD:那是我第一次在书中加入自己的经历,这是普林斯顿出版社的维基·基恩(Vickie Kearn)提出的想法。我之前写过一本《数字之人》
T
he Man of Numbers,是纯粹以第三人称讲述斐波那契以及《计算之书》
Liber Abaci的引入历程。我在书中聊起我写这本书时的经历——去意大利和学者交流、在档案馆查找资料、阅读拉丁文文献,甚至有点像一名历史学家。
她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故事,你是在追寻一位你敬佩的人。”把自己写进书里对我来说非常困难,维基帮了我很多。结果这本书的读者比《数字之人》多得多,成了我最受欢迎的书之一,至今仍然畅销。所以加入个人经历确实极大地提升了销量。不过写的时候我真的很尴尬。
SS:除了销量上的成功,现在回头看,你还会觉得尴尬吗?
KD:不会了,因为我已经克服了那种感觉。这和我为美国数学协会(MAA)写的长期专栏《德夫林的视角》
Devlin’s Angle(现在是博客)也有关系。这个专栏始于1996年,最初很多年都是第三人称写作,但后来逐渐变成了我和读者之间的对话。
最近几年的专栏,完全就是我在和读者聊天。我觉得大家并不会觉得这是自我吹嘘,而只是把它当作一场对话。人们似乎很喜欢这种形式,有些学校还会把专栏文章贴在公告栏上。所以我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个人经历,确实能让科普作品更有吸引力。如果要利用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进行科普,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必要的。
SS:马库斯,我觉得你在BBC的纪录片《数学的故事》
The Story of Maths中也是这么做的。
MdS: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如果你是主持人,那么“旅程”(这个词虽然被过度使用)是构建叙事的重要部分。我认为,科普的一大挑战就是为这些数学主题构建一条清晰的叙事线索——历史线索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我在《素数的音乐》
Music of the Primes中就采用了这种方式。
而《数学的故事》
The Story of Maths则采用了地理旅程的形式,通过讲述不同地区的数学故事,构建了一条强有力的叙事主线。我当然知道,编辑们都很喜欢在书中加入一些个人元素,因为这能让读者更有代入感——我完全同意基思的看法。对我们来说,这种写作方式并不自然,因为我们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是第三人称的。
所以关键在于平衡,不能过多地突出自己。我的第二本书《寻找月光》
Finding Moonshine中,我想通过对称的故事,让读者了解数学家的工作日常。我非常谨慎地只加入了一些片段,重点还是放在核心故事上。我觉得把握好这个平衡非常困难,而编辑在这方面确实能提供很大的帮助。
KD:我以前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和斯科特·西蒙一起主持《数学小子》
The Math Guy节目时,最常见的反馈是“我喜欢你的口音”。我很清楚,这个节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美国电台里,有一个带着约克郡口音的人在讲数学。我和斯科特之间的默契也很重要,虽然我们身处数千英里外的不同演播室,从未见过面(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但节目听起来就像两个朋友在聊天。
当然,节目都是录播的,他们会把斯科特那些过于出格的笑话剪掉——如果听众听到那些未删减的内容,斯科特可能就再也不能在NPR工作了。这个节目的成功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聊天风格,二是我的约克郡口音。如果我只有标准的美国或英国口音,这个节目可能不会这么成功。
SS:我想到了塞德里克·维拉尼(Cedric Villani)的《一个定理的诞生》
Birth of a Theorem。作为一名顶尖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他在书中就像马库斯说的那样,带读者走进了“幕后”。他和他的合作者在书中占据了很大篇幅,但我觉得这对于那个故事来说是合适的。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品味问题。如果一个人有良好的品味,就能在书、电影或系列节目中恰当地展现自己。
MdS:我还想提一下爱德华·弗伦克尔(Ed Frenkel)的书。在阅读关于朗兰兹纲领的内容时,了解他的一些个人经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KD:《双螺旋》
The Double Helix是一本非常棒的书,书中展现了克里克和沃森之间的竞争、野心,以及整个发现过程。
SS:这本书的优点在于,沃森在书中毫不掩饰自己的缺点,没有假装自己是完美的,但这却让故事变得非常精彩。
MW:如何根据不同的媒体形式调整科普方式?
MdS:我最初是为报纸写文章,当时的编辑非常有耐心。她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为报纸写稿——我总是把最精彩的内容放在最后一段,但没人会读到那里。她教我采用“金字塔结构”写作。
后来我开始写书,我的编辑又说:“天啊,你每一页都在大喊大叫。读者是来读长篇内容的,请冷静一点。”为不同的媒体写作,确实需要学习不同的技巧。
广播和电视也有很大区别。广播的环境更丰富,因为它更抽象——在某种程度上,这非常适合数学科普,因为你可以谈论那些无法可视化的概念。
而电视是一项团队工作,你必须更愿意接受多方面的意见。这既令人兴奋,也充满挑战。你必须学会“重复三遍”原则:“我即将告诉你……我正在告诉你……我刚刚告诉你……”我觉得电视是一种非常枯燥的媒体,但它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能触达大量受众。
现场表演则有不同的特点。有人说过,数学不是一项观赏性运动。所以要想办法让观众参与进来,而不是被动接受。我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在英国皇家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关于《魔笛》
Magic Flute的互动歌剧活动。
我们向观众解释了《魔笛》背后隐藏的数学知识,还邀请观众上台参与互动,通过一个充满趣味性的动态游戏来讲解奇偶性。多年后,还有人对我说:“我参加过那场《魔笛》活动,现在还记忆犹新,因为观众能亲身参与其中。”
JAP:我还没提到蓝蝴蝶(BlueSky)和推特(X)这两个平台。在这些平台上,科普内容必须简洁有力,或许可以链接到更详细的内容,但开头部分一定要简洁、有冲击力,能够吸引读者或引发讨论。
MW:《标题党数学家》The Clickbait Mathematician——这可以作为你的下一本书名。
SS: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书名。
KD:我也觉得这个书名很棒。谁会先抢走这个书名呢?
MW:你们都提到了编辑的重要性,能详细说说吗?
SS:这可能是我们的同事们不太熟悉的领域,因为期刊编辑通常只是根据审稿人的意见做出决定。但科普书籍的编辑,甚至是优质媒体上的科普文章编辑,会真正地塑造作品。你之前问过潜在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如果你想写一本面向大众的数学书,不要写完再拿给编辑看——这是非常外行的做法。
正确的做法是先提交选题提案,编辑认可你的想法并买下版权后,你再开始写作。他们会在很多方面给出建议,比如“这个内容应该放在这里”“这个太冗长了,删掉吧”。或许这其中有编辑的私心,但更多的是他们真的知道什么内容会受欢迎。至少根据我的经验,他们的建议都非常有价值。
KD:我把所有的编辑都视为合著者。我和大卫·特拉纳合作撰写《逻辑与信息》时,曾对他说:“大卫,我们干脆把你列为合著者吧?”他说:“不行,我是编辑。”但那本书实际上是我们共同完成的。我觉得这非常令人兴奋,因为他们能带来完全不同的视角。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我的编辑是一位历史学家。这会很有挑战性,因为我知道他会提出很多重要的意见,而我需要花时间去理解和吸收。
MdS:我的所有编辑也都是历史学家。写《素数的音乐》时,我提交了第一稿,编辑说:“你可能觉得这很有条理,但你采用的是科学叙事方式,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一会儿跳到20世纪,一会儿又回到18世纪,读得我头晕目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历史叙事结构。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以历史为线索,让数学知识自然地融入其中?”
这个建议彻底改变了这本书。我之前是按照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写作,而不是为普通读者或数学读者写作。和史蒂夫一样,我的目标读者是那些害怕数学、对数学感到恐惧的人。我的编辑说得非常对,采用人们熟悉的历史叙事结构,再将他们不熟悉的数学知识融入其中,是最有效的方式。
SS:我很好奇,现在这本书看起来浑然天成,仿佛只能这样写。那你最初的版本是怎样的?
MdS:我当时觉得最初的版本非常合理。科学叙事通常不需要遵循历史顺序,数学家也常常从结论开始讲起。但我认为科学的教学往往是按照历史顺序进行的——你能看到理论的提出和推翻过程,这对于学习科学非常有帮助。
SS:我记得我学量子力学时,前几周全是历史背景介绍,我当时想:“直接告诉我量子力学是什么就行了!我不想听这些混乱的历史!”
SH:我的编辑帮我解决的最大问题,是我作为学者那种追求“完整性”的倾向——比如“这里有所有相关的例子”。我总觉得需要列出所有实例,才能让我的学术论点更有说服力。
但我的编辑说:“读这本书的人知道你很专业,你不需要向他们证明自己的知识储备。你要做的是给他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只保留那些与其他例子有明显区别、能展现新视角的实例就够了。你不需要列出俄罗斯文学中所有将四维空间用作隐喻的例子,一个就足够了。”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我有很多详尽的笔记,如果需要可以随时查阅,但在书中,只有那些对故事有帮助的内容才会被保留下来。
JAP:伯特兰·罗素曾说过一句话——其实很多人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清晰性和严谨性之间存在权衡。如果是为大众写作,清晰性可能比严谨性更重要。至于编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固执,或者像史蒂夫说的那样喜欢“说教”,我其实不太愿意听编辑的建议,而且一直都是这样。也许这是个问题,但我不确定。
SS:听到你这么说很有趣,但并不意外。你对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有非常清晰的愿景,可能不需要编辑的过多干预。而我则更愿意接受他人的建议。
MW:对于那些担心在面向大众科普时偏离自己专业领域的数学家,你有什么建议?
MdS:我认为可以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开始,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果想长期从事科普工作,就必须走出舒适区——事实上,这往往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对概率论一窍不通。我记得伊恩·斯图尔特曾在电台上解释蒙提霍尔(Monty Hall)问题(即三门问题),但显然他解释得不够清楚,因为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收到了很多质疑信件。而当时伊恩去了东南亚的一个岛屿参加会议,无法联系到他。
英国广播公司的数学家名单上,下一个就是我,于是他们邀请我去电台解释这个问题。我以前从未理解过这个问题,但为了准备电台节目,我深入研究了它,现在不仅理解了,还找到了一种通俗易懂的解释方式——这个内容后来还被收录到我和艾伦·戴维斯合作的电视节目中。
作为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教授,所有人都认为我必须通晓所有科学知识。我接手理查德·道金斯的工作后,经常有人打电话来问:“端粒诺贝尔奖刚刚公布,你能解释一下什么是端粒吗?”如果说我不擅长概率论,那生物学就是我的软肋。但我会先查阅维基百科,作为科学家,我能够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并找到向记者解释的方式。后来我意识到,最好的做法是联系大学里相关领域的专家,把他们介绍给记者。这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敢于尝试,也要认清自己的局限。
SH:当然,还有“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指个人无法内化自己的成就,总觉得自己配不上所获得的荣誉)。玛丽安·米尔札哈尼(Maryam Mirzakhani)获得菲尔兹奖时,我就有过这种感受。英国广播公司显然认为“伦敦广播大厦附近最近的女性数学教授是萨拉”,所以邀请我去快速解释米尔札哈尼的研究成果。
虽然我是纯数学家,但这仍然非常困难——我只能大致了解她的研究方向,要在12秒内向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的听众解释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差点就说“不行,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后来我想,我不需要成为世界顶尖专家,也能给出一个大致的概述。如果只谈论自己真正擅长的领域,那么你的科普生涯将会非常短暂。
JAP:无论何时写作或解释某个知识点,都必须考虑到你的受众。只要你提供的内容能以某种方式启发他们,即使你不是X、Y或Z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也没关系——只要你比受众知道得更多,并且能真正帮助他们理解这些知识。
SH:关键是不要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要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需要避免的一个潜在问题是,让人们误以为你是某个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你的角色是解释者,即使不是该领域的顶尖人物,也可以进行科普。
SS:如果作为数学家,我们只局限于谈论自己的研究成果,那么相比浩瀚的数学知识海洋,这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这才是真正的“冒名顶替综合征”。但作为科普工作者,你可以自由地谈论整个数学领域,这自然比只谈论自己的研究成果要好得多。我一直认为这是科普的一大优势——我不需要谈论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研究,而是可以分享伟大数学家的成果。
或许还应该说,科普不一定只关注顶尖数学家的成就,因为还有很多不那么“出名”的数学家,他们的工作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对他们自己来说非常有意义,也为数学学科和社会做出了贡献。有时候我们可能过于关注那些最顶尖的人物——比如玛丽安·米尔札哈尼这样的大师,但那些稍逊一筹的研究成果,同样可能非常优美、有趣且具有影响力,也值得科普。
JAP:我认为我们应该用“科普者综合征”(expositor syndrome)来取代“冒名顶替综合征”。
SH:我同意史蒂夫的观点——科普不应该只关注顶尖人物。对于学生来说,了解那些“普通”的数学家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出贡献。你可能只听说过少数顶尖人物,但他们只是庞大数学社区中的一部分。我在写作或给本科生上课时,会特意提到一些做出小贡献的数学家,这不仅能展现数学社区的多样性,也非常有意义。
SS:这个观点可能有点超前。说到ChatGPT之类的人工智能,我认为用不了多久,包括最伟大的人类数学家在内,我们所有人都将成为“普通人”。因为最伟大的定理很快就不会再由人类提出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关注最顶尖的数学成就,那么未来我们可能再也不需要谈论人类的研究成果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意识到,各种数学贡献都有其价值,包括那些被视为“娱乐性”的数学内容。数学研究有多种形式,都能带来成就感,而不仅仅是产出最伟大的定理。
JAP: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聊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带来的令人沮丧的一面。高中和大学学到的所有数学知识,现在在某种程度上都变得无用了。至少我觉得这非常令人沮丧——知道这些知识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SH:我们确实不再需要手动做长除法了,对吧?但不知何故,你学习的具体技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学习过程中培养的思维能力。我总是这样安慰自己:数学课程中学习的具体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如何思考——这一点永远都很重要。而且目前来看,ChatGPT在数学方面还很糟糕,所以我们暂时还不用担心。
MW:你的同事和更广泛的数学社区对你的科普工作有什么反应?
KD:我刚开始做科普时,同事们的反应非常负面。我当时在兰卡斯特大学任教,他们觉得“你在自降身份”。我收到了很多讽刺和挖苦的评论,比如“这就是那个连多项式都不懂的人”。这种负面评价没完没了,一直困扰着我。我记得有个同事在我为《新科学家》写稿时说:“你又在为《漫画天地》
Comic Cuts写东西了。”
SS:那后来呢?现在的情况还这样吗?
KD:哦,不,早就不是这样了!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可能是转折点。当像他这样顶尖的学者都写出了一本面向大众的科普书(虽然很多人其实没读完),并且大获成功时,科普工作就获得了认可。后来罗杰·彭罗斯等顶尖数学家也纷纷出版科普书籍,这些“大佬”的参与,让科普工作正式合法化了。
SH:但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仍然有这样的声音:“不要陷入科普工作,因为这会占用你做研究的时间。”在英国,还有一个略带贬义的词——“媒体学者”(media don)。如果你为公众做科普,就会有人认为你是因为做不出研究才这么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G·H·哈代《一个数学家的辩白》的影响。哈代在书中说,他写这本书是一种“认输”,因为他已经无法再做出杰出的研究了。书中还有一句令人不快的话:“数学是年轻人的游戏。”虽然我很喜欢这本书,但哈代确实需要为这种观点负责——“如果你再也做不出研究,那就去做科普吧”。
SS:很高兴听到你也认为哈代需要为此负责。作为应用数学家,我一直这么认为。但我觉得他的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从历史上看,科普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爱因斯坦、庞加莱、冯·诺依曼都做过科普。事实上,哈代只是个例外。当然,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科学家与军方合作,研发更具杀伤力的武器,这让他对科学应用产生了抵触情绪。所以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他的态度。但就当代而言,比如陶哲轩在他的博客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做科普,他做得非常好,涵盖了各种主题和不同难度的内容。
JE:我一开始也有点担心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博客名字有点晦涩(博客名为“Quomodocumque”——拉丁语,意为“无论如何”)——上面完全没有提到乔丹·艾伦伯格这个名字。因为我刚开始写博客时,这还只是一个奇怪的爱好,我会混合发布一些数学相关和不相关的内容。我担心“这会显得我在学术上不严肃”。
但我从未觉得,我的同事或大学会因为我写科普而对我有看法。事实上,在大学层面,只要有人能以积极的方式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大家都会非常高兴。这就像那些真正关心本科课程设计的人一样——我们大多数人对此不感兴趣,但都很感激那些愿意为此付出努力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很重要。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我是在职业生涯稍晚的时候,已经获得终身教职后,才开始认真做科普的。我博士后期间曾为《石板》
Slate杂志写过一些文章,但那都是小打小闹,没有投入太多时间,一年也就写几篇。我直到获得终身教职后,才开始撰写通俗科普书籍。
MdS:我刚开始做科普时,确实担心会遭到反对——部分原因正如萨拉所说,我们都受到了哈代观点的影响。但令我惊讶的是,我的研究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学会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我当时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大学研究奖学金,他们与研究员的联系非常密切。有一次有人对我说:“你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以为他们会说“请不要再做这种事了,你应该专注于研究”,但他们却说了完全相反的话:“我们希望有更多科学家站出来做科普。我们意识到,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缺口。”事实上,我还受邀加入了英国皇家学会科学与社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英国上议院詹金斯报告发布后成立的,该报告指出,科学家没有承担起向社会传达科学对政治影响的责任,这是一个严重的危机。
对我来说,向政客解释科学对社会的重要性非常重要——这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家长、教育领域,最终惠及孩子。我非常高兴,在我开始想要投身科普事业的时候,英国皇家学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一直给予我支持。
乔丹提到了大学的态度。牛津大学认为科普是一种双赢——每次我做科普演讲,都会提到牛津大学,数学也会因此与牛津大学联系在一起。我所担任的职位是1995年专门设立的,目的是让任职者无需承担教学和行政工作,能够专心从事科普工作。这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此类职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设立类似职位(上周我刚见到了圣母大学新设立的类似职位的现任持有者凯特·比伯多夫——我和史蒂夫还和她一起做了一场线上活动)。
大学们逐渐意识到,这类职位非常有价值,因为科普能带来一定的曝光度,甚至可能带来经济回报——比如牛津大学新建数学系的资金,部分就来自对冲基金,而这些对冲基金之所以了解牛津大学的数学学科,正是因为我在电视上做的科普工作。所以大学们意识到,科普工作确实值得支持。
SS:这就是为什么听到基思的负面经历时,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会再发生了。以前卡尔·萨根就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尽管从客观来看,他在行星大气等领域的研究成就斐然,本应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但他最终却未能入选。这可能是因为他在电视上过于活跃,甚至有以自己为中心的倾向,导致了一些反弹。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系主任曾告诉我:“助理教授不要写教科书——这会显得你本末倒置,应该专注于研究。”所以确实有很多信号表明,在职业生涯早期,我们不应该过多地投入科普工作。
MW: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SH:我想说的是,不必勉强自己做不擅长的事情。你不需要跟风做最新的潮流,从自己舒适的领域开始,然后再逐步拓展。我不做TikTok视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尝试的话,肯定会显得很不自然。所以我选择做公开讲座、写作,以前还会在推特上分享内容(在它变成“地狱景观”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我不会成为TikTok博主或照片墙(Instagram)网红,但汉娜·弗莱在照片墙上做得非常出色。
JAP:你可以从一些小事做起,不一定非要写一本书或为杂志、报纸撰稿。
SS:甚至可以为《美国数学会通告》写一篇科普文章。如果你想做,就去做;如果不想,专注于自己的数学研究也很好。
JAP:我还想建议大家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数学——有些主题可能被称为哲学、物理学或公共政策,但它们都与数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应将数学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我的第一本书是《数学与幽默》
Math and Humor,第二本书《我思故我笑》
I think, therefore, I laugh则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观点:一本优秀而严肃的哲学著作,完全可以由笑话构成。如果你能理解这个笑话,你就能理解其中的核心观点。你可以以轻松的方式走进数学。数学涉及很多领域,事实上,所有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数学相关——我并不是想夸大数学的重要性。
KD:我们讨论的话题中,其实就蕴含着一个新闻故事。我最近为《德夫林的视角》写的一篇文章,被《观察家报》的专栏作家约翰·诺顿注意到了。他链接了我的文章,而那篇文章只是讲述了我为什么开始为大众撰写数学科普。他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MdS: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有一次在牛津的一场晚宴上,我坐在《泰晤士报》的特写编辑旁边,我告诉他我的工作后,他说:“你做的事情听起来太有意思了。”他让我为他写一篇文章,但我当时没有写。三年后,我又在同一场晚宴上遇到了他——牛津有句老话:“客人不变,研究员在变。”但我仍然在那里。他说:“你当时答应给我写的文章,一直没写。”我很惊讶,三年后《泰晤士报》的特写编辑竟然还记得我们当时的谈话。
我想:“事实上,我们确实有责任向公众解释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如果我们的研究经费来自公众的话,更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很重要。”那天晚上,很多记者都说:“你应该写这篇文章,因为你拿了公众的钱,需要告诉我们你用这些钱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正是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走上了科普之路。
文章DOI:
10.1090/noti3285,载于《美国数学会通告》
AMS Notices2026-01。
参考资料
https://www.ams.org/journals/notices/202601/noti3285/noti3285.html
https://quoteinvestigator.com/2021/09/30/stree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yal_Institution_Christmas_Lec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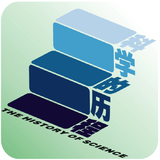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