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莱臣后人捐赠南京博物院的仇英《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场事件,这两天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政府已分别组建工作组与调查组赶赴南博进行调查。我相信以此图卷为核心,围绕着南博藏品管理而产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官方说法,关注此事的诸位可以静观事态的发展。我在此想先谈一点关于博物馆文物藏品的鉴定问题。
庞家后人在与南博的所有争议中,首要的一点就是仇英《江南春》图卷的真伪问题。毕竟南博后续所有的操作,都是建立在他们认为此卷是赝品的前提之上。南博方面宣称此作曾于1961年经张珩、韩慎先、谢稚柳三人组成的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小组”鉴定,结论为赝品。1964年经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三人复检,依然维持“伪作”的结论。而庞家显然不认可南博方面的这一鉴定结论,并给出了该作曾经王任堂“话雨楼”、顾麟士“过云楼”、庞元济“虚斋”等名家递藏、拥有郑振铎、杨仁恺等鉴定家背书、以及一系列的权威出版及著录等佐证其为流传有序之名家真迹的材料。
虽然笔者在十数年前就曾亲睹此卷,并为其精彩所深深折服,但坦率而言,面对像仇英这样自古以来真伪问题就相当复杂的个案,确实无力就其真伪给出一个斩钉截铁的判断,唯一肯定的是,即便该作系赝品,也是一件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都非常高的“伪好物”。

注:“伪好物”的概念由米芾提出,他在对一件传为钟繇所书《黄庭经》作鉴定时,认为其虽然系唐代摹本,但临写极佳,乃以“伪好物”称之。2018年台北故宫举办“伪好物——十六至十八世纪'苏州片'及其影响特展”,这一说法遂为世人所熟知。
之所以会如此,就涉及到文物鉴定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鉴定结论的“模糊性”。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诸如“瓷器”、“玉石器”、“金属器”等文物类别可以通过引入“科学鉴定法”,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结论。
现有的“科学鉴定法”包括“热释光测年”(陶瓷器)、“显微观察”(玉石器等)、“X射线荧光分析”(金属器)等,但即便是可以采取“科学鉴定法”的文物,也因为面临着“破坏性取样”、“鉴定结果合理误差”、“检测费用高昂”等一系列现实性的难题而无法全面铺开。
但诸如书画、碑帖、古籍版本等文物类别的鉴定依然有赖于传统的“目鉴法”。由于每位鉴定人员的情况(包括学识、经验甚至于鉴定时的身体状况)各不相同,这就难免会出现不同的鉴定人员在面对同一件作品时给出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因此合理的做法是,在面对此类争议时,不宜轻易肯定或者否定,应如实记录每一位鉴定人员的观点,留待后人在条件成熟时再作出结论。我们需要明白一点,鉴定意见是学术观点,不是行政结论,学术是允许争议存在的。
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文物局组织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七人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全国范围内对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所藏书画作品开展巡回鉴定工作时,即采用了此原则,并在作为工作成果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如实刊出各位专家的意见。

关于文物的定级,虽然国家公布有《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但基于文物的单一性与特殊性,实践工作中对于存在一定争议性的文物,也应该秉承“从宽”的原则,尽量不要因为个人的认知局限而错杀珍贵文物。
“我们经常对鉴别,还不能不发生错误,第一在于学习唯物辩证法不够,对书画本身的认识不够,这是主要的。”——谢稚柳
而且我们需要明白一点,鉴定意见与文物定级应该是允许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情况的发展随时修订的。墨守陈规,迷信前人结论,都有可能对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严重伤害的。
比如1975年,谢稚柳就确定了万育仁从赝品中检选出的《上虞帖》为南唐及北宋内府珍藏的唐摹本;1978年徐邦达在对青岛市博物馆馆藏书画鉴定中,确定了唐摹本《食鱼帖》。又比如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现在基本上每周都会选一天前往周浦的文物库房对馆藏书画作复检,而工作的重点就是审查在博物馆传统观念中不被重视的近现代书画,并将其中诸如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潘天寿等名家的作品提到其应有的文物等级上来。
由此可见,即便刨去时代因素,以最大的善意来推测,南博方面仅依赖1961年与1964年的两次鉴定意见,就没有将《江南春》图卷交由1986在南博进行文物复检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进行复检,并于1997年将之剔除出藏品序列,无论如何也都是存在严重瑕疵的。毕竟这是一件名家递藏且1961年鉴定意见认为“陈鎏题引首真”、“伪做得很好,原庞家是当真的藏的”。
已出版工作笔记的杨仁恺、刘九庵都未曾在当年南博的鉴定工作中记录该画卷,有理由相信是因为南博将其列为“伪作”没有拿出来的缘故。
而《艺术澎湃》最新的报道中援引谢稚柳之子谢定伟的表述,对谢稚柳是否参加了1961年的鉴定工作也表示了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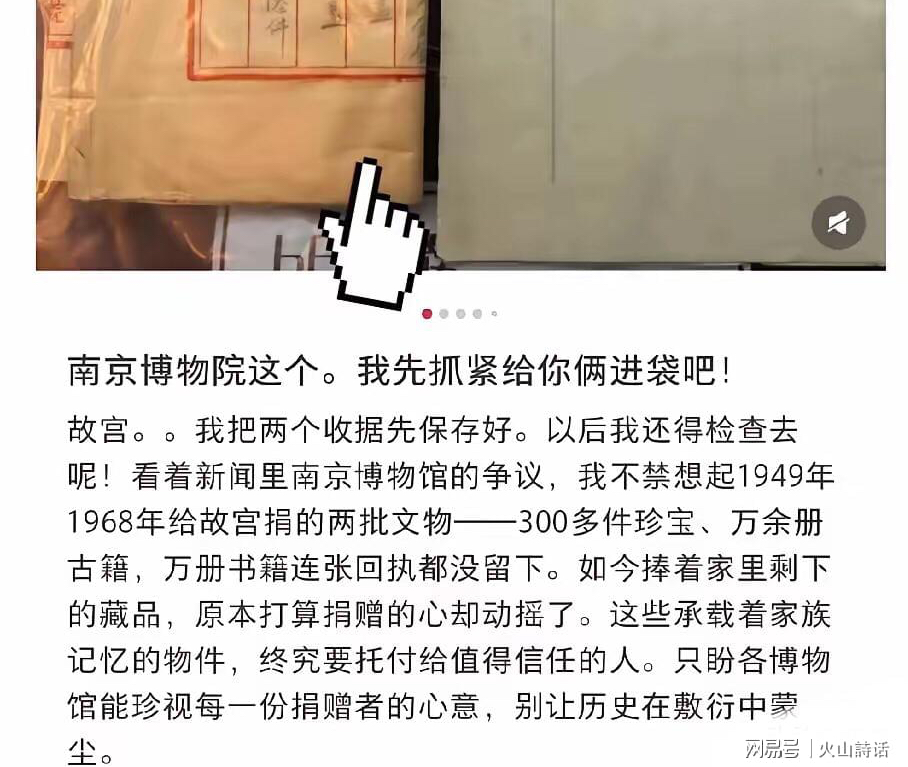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