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100道古代美食》的嘉宾风味彩蛋,来自英国的美食作家扶霞。她用西方的食探目光,带我们重新审视这碗宋朝的“液态历史”。
“宋嫂鱼羹”,一道杭州名菜,却又不只是名菜。它承载着《礼记》里的“大羹不和”,晏子的“和如羹焉”,一段又一段独属于中国的烹饪治国智慧。这篇文章里,扶霞以人类学的嗅觉,打捞起一锅被遗忘的中餐“炖煮”奥义。
为何“调羹”之勺,至今仍叫“调和之羹”?那些载入史册的一汤一饭间,多的是我们没曾听过的故事。

本文摘选自扶霞·邓洛普2024年新书《君幸食》,有删减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宋嫂鱼羹(Mrs Song's Fish Stew)是中国东南部城市杭州的特色美食。
碗中的热气飘然而上,深深地吸入一口,你会不由自主地沉迷在那隐约带着清爽醋香的柔和鲜味之中。这碗羹,既非固体,也不是完全的液体,只能形容为一个旋转的万花筒,可食用的多彩威尼斯玻璃;一条流动的食材之河,只是因为加入淀粉增稠而凝固住了。这碗“风味调色板”上色调平衡均匀:白色的鱼肉碎,金黄的蛋黄碎,深色的香菇丝和象牙白的竹笋,最后还点缀了几丝粉红的火腿和翠绿的葱花。这道羹汤以十几种不同的食材熬制而成,但没有任何一种过于突出,喧宾夺主;大家都交汇在一起,其乐融融,一团和气。

和很多杭州菜一样,这一道也有个故事可讲。它最初诞生于这座城市著名的西湖,那是一片如梦似幻的水域,两岸垂柳依依,间或有茶馆、小岛与小桥点缀其间。如今,船夫们划着游船,将客人带到那波光粼粼、宽阔静谧的湖面上欣赏美景。但这里曾经是非常繁忙的水道,游船与商船熙熙攘攘穿梭其间。
大约九百年前,中国的北方都城被游牧民族侵占,宋朝的残兵败将南逃杭州(当时称为“临安”),建立了新的都城。流亡偏安期间的一天,皇帝乘自己的御船游览西湖,并找一些流动货郎询索货物样品。其中有位卖自制吃食的女人毛遂自荐,自我介绍说因为嫁给了宋家老五,所以人称“宋五嫂”,也和皇帝一样,从北方逃亡来到杭州,以售卖鱼羹为生。皇帝品尝了她做的羹,自觉美味非常,融合了北方的烹调方法与南方的食材。一时间,国仇家恨、思乡之情,百感交集,皇帝赐宋嫂“金银绢匹以表感谢(在有些传说版本中他还邀请她去御膳房工作)。
中餐语境下,汤分为两大类:汤和羹。汤,清爽澄澈,其中可能会漂浮着一些食材,但不能“吃”汤,只能“喝”汤。相反,宋嫂鱼羹这样的“羹”,就更为浓郁,几乎可以称为一锅炖菜了,里面会放很多切好的配料,通常都会放淀粉勾芡增稠——就像过去西方唐人街餐馆菜单上必有的鸡肉或蟹肉粟米浓汤。
羹,丰富扎实;汤,清淡微妙。西方人好像通常更偏爱前者,也许因为它与西餐中常见的奶油般稠腻丝滑的浓汤不谋而合。很多讲究的粤菜馆会将肉或禽类与当季蔬菜、补药一起小火慢熬,煮成清澈而滋补的每日例汤,但西方人很少点这种汤,可能他们的舌头觉得这种“清汤寡水”太淡了,没什么内容,因此性价比太低——那些好料看都看不见,不像鸡肉粟米浓汤或热腾腾的酸辣汤,“丰富的配料和浓郁的风味在舌尖上就有直观感受。
这边厢,中国人几乎每餐都得喝汤:要是一餐饭食没有汤,就显得干巴巴的,叫人心有不甘,尤其主菜是炒饭或炒面时,更亟需一碗汤来滋润和清口。家常便饭时,餐桌上唯一的液体可能就是汤,既是食物,也是饮料。羹则没那么不可或缺,并非日常饮食,只是偶尔一品。

然而,虽然现在的大家可能觉得羹只是中餐桌上的一个龙套,人家曾经可是所有中餐菜肴中最重要的主角。大概可以这么说,在所有菜肴大类中,羹最能说明中餐烹饪的历史与特色。
远古时期,人们用原始的方式生火烤食;新石器时代,陶器应运而生,于是有了煮食。稻、黍、稷等谷物被放入锅中,煮成粥;又有鼎上放打孔的坦盘,蒸作饭。至于其他食材,无论肉、鱼还是菜,则大部分都是切割后放进水中煮,成品就被称为“羹”。穷人吃菜羹,偶尔能尝尝鱼羹;富人则奢侈地享受肉羹、禽羹或野味羹。古籍《礼记》中说人无论贵贱都会吃羹:“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 在大约两千年前的汉朝,宴席上的第一道菜就是羹。
通常,羹与大米或小米形影不离,不仅搭配着一起吃,还可能一起煮:羹在下面的鼎中咕嘟咕嘟,谷物则在上面的蒸笼中吸收水汽,变得蓬松绵软。 “羹”,说不清是汤还是炖菜,它其实就是中餐最原始、最初的“菜”,是万肴之源,其出现时间只略晚于“烤”,比其他菜肴都要早。在古代中国,人们几乎每餐都要用羹配饭,也就是说,羹就是上文提到的“饭以外的一切”。

羹里有各种食材,包罗万象。《礼记》中提到了一些羹,每种都有特定的佐餐搭配,看上去实在美味至极:雉羹搭配菰米饭和田螺酱、肉羹或鸡羹搭配麦饭、犬羹或兔羹搭配糯米饭。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公元前三世纪竹简文物清单列出了墓主(一个贵族家庭的三位逝者)往生之旅需要的所有生活用品,其中就有二十四座青铜大鼎,里面装的是羹,入羹的食材包括乳猪、野鹿、鲤鱼、鲟鱼、野雁和雉鸡,有时是独料成羹,更多的时候是与蔬菜混合。有些羹里加了米屑,变得浓稠丝滑,这就是现在用淀粉给汤羹勾芡的雏形。在马王堆年代之前不久的诗人屈原,试图在一首诗中用凡俗生活的乐趣招回逝者的灵魂,其中提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菜肴,有一道地方特色菜就是融合了酸苦之味的吴国之羹:“和酸若苦,陈吴羹些。” 也是在那时候,贫苦百姓的常见饮食就是用野菜制成的羹——“食藜藿之羹”,成了清贫困顿中守正节俭的象征。
北方有羊下水做成的羊杂羹(直到今天也是当地广受欢迎的美食);杭州所在的江南地区,正如《史记》中记载,早在宋嫂为皇帝奉上那碗鱼羹之前的一千年左右,人们就开始以鱼为羹、以稻为饭了。而华南粤人从古至今都一样,以口味千奇百怪而著称,他们对蛇羹情有独钟,颇为外人议论。(如今的广东人仍然热爱好味的蛇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几年前和朋友们在广州品尝到极其正靓的蛇羹,用五种不同的蛇做成,上面撒满了细细的香茅草和菊花瓣。)有个著名的历史故事:一位君主在家宴上不让客人中的某位大臣品尝非常诱人的甲鱼羹,让人家脸上相当挂不住,相互之间起了大龃龉,因此发生了连锁反应,最终导致这位君主被刺杀。
“历史向前推进,厨房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铁器和木炭,于是人们可以用高温更迅速地烹饪食物了。宋朝时期,一种新的烹饪方法开始在中国的厨房中流行起来,就是用专门的工具“追赶”热锅中细细切好的食材,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炒”。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在鼎中烹煮的羹这种历史悠久的菜品,仍然是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十三世纪的南宋时期,钱塘人吴自牧对杭州的市井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其中列出了临安城中餐馆和面馆提供的不同羹汤,真是五花八门的一长串,包括“五软羹”“三脆羹”“虾鱼肚儿羹”“杂辣羹”和“杂彩羹”。

“做炒菜,最好是在热炒锅中小份小份地出菜,而羹不同,可以用巨大的锅进行大量制作。也许正因如此,宴会的菜单上,羹总是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比如十八世纪末期在扬州举行的一场宴会,在九十多道菜肴中,就有数道羹的身影,有的用不同食材切丝混合熬煮而成——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鱼翅螃蟹羹、鲨鱼皮鸡汁羹、鹅肫掌羹;有的只用一种主要食材的羹——鸭舌羹、猪脑羹、文思豆腐羹。 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使团访华,北京城的一场筵席上,第四道席面是“十二大碗浸润在浓郁羹汤中的炖菜”。类似地,1838年,法国海军上校拉普拉斯(Laplace)在广东参加了一场晚宴,提到“大量盛在碗中的炖菜,接连不断地端上桌来。所有的菜肴,无一例外都浸泡在汤里。”
后来,随着中餐的技法越来越多样和精妙,“羹”的光彩逐渐被其他多种菜肴夺去。然而,在华夏大地的各个地方菜系中,羹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有粟米蟹肉羹这样的家常菜,还有地方特色菜,如杭州的宋嫂鱼羹、“丝绸之路”重镇西安的驼蹄羹和南粤的至高佳肴蛇羹——每一道都能让人蓦然回想起遥远王朝中那些最辉煌耀眼的美食。

在古代中国,羹也是被赋予了神圣意义的菜肴。在盛大的祭典上,安抚神灵的供品不止黍稷和美酒,还有装满羹的大鼎。不过,给人吃的羹汤调味可能丰富大胆、美味非常,比如那导致君主覆灭的甲鱼羹;而祭典供奉的神圣羹汤,也就是“大羹”,是不加调味料的白味羹,因为人们认为鬼神已经超脱了这些凡尘琐碎,不再会因味觉上的感官刺激而兴奋。毕竟,他们吃的也并非供品的实体,而是祭典过程中往天空升腾的“气”。人们笃定,最能取悦神灵的羹,一定要代表纯粹清明、返璞归真、空灵脱俗。无味之羹,恰恰象征着尘世间一切味道的融合,恰如光谱中一切喧嚷鲜艳之色,最终却汇成纯白之光。
烹饪是一门精湛的技艺,甚至算得上一种“炼金术”,这样的理念在古代文献中被反复表达和提及。圣贤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 这话在英国人听来大概是在轻视治国理政,毕竟他们觉得烹饪很容易,就是烤只鸡,再烤几块土豆嘛;但放在中国的语境下,则恰恰相反——这句话寓意深刻,意思是无论治国还是将小鱼烹制成讲究的菜肴,都需要敏锐细致的洞察。
说得再具体一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治国理政之道常常被比作给羹调味。公元前六世纪,齐景公的辅政卿相晏子就曾发表过一番著名的政论,用烹饪作喻,来解释政治上的和谐是来自不同意见的融合,这与盲目和谄媚的一致附和是不同的: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
厨师与统治者有个相同的使命,就是创造和谐。统治者调配手下服务的人才,来创造和谐的国家和社会;厨师则通过刀工、融合与调味来创造和谐的味道。

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套哲学在二十一世纪的中餐厨房中依然铿锵有力地绕梁不绝。当代中国厨师和古代治国的君臣一样,仍然在努力用对比鲜明、喧喧嚷嚷的食材与调料创造和谐与平衡,利用它们在颜色、口感与风味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谱写美味的菜肴与合理的菜单。“你只需要加一点点糖,”我的朋友戴双在向我解释一个菜单时说道,“不是要突出甜味,而是要’和味’,让菜肴的风味更加和谐。”在中文里,“和”这个字,既可以读“he”,“和谐”的“和”;也可以读“huo”,“拌和”的“和”。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尤其是南方,至今还把汤勺叫做“调羹”,调和羹汤之意。
如今,要说代表性的中餐,大家似乎都会说炒菜,也许事实的确如此。但炒菜的大部分基因都承袭于古老的羹:将食物切成筷子可以夹着吃的小块,荤素的搭配,将不同的食材融成和谐的整体。炒菜算是(相对)近代崛起的形式,而羹则是起源。杭州餐桌上的一碗鱼羹,讲述的故事不仅是一位宋朝厨师巧遇思念故土的皇帝,其外沿要大上很多,涵盖了中餐烹饪的起源与演变。
曾有宋嫂羹汤的杭州西湖,如画的风景历久弥新。只要住在附近,我每天晨起都会去湖边走走看看,觉得平静而愉悦。早春时节,初生的柳芽嫩绿欲滴,绽放的玉兰粉白可喜。之后便有桃红夭夭,到秋天空气中便会弥漫桂花的甜香。晴好的天气里水光潋滟;雨天则山色空蒙,全部的美景都像隐没在神秘的中国传统水墨画中。
夜幕降临时,我站在西边的湖岸远眺渐隐在暮色中的群山与湖水,感觉即便历经了种种王朝兴衰、叛乱、战争与革命,这里的景色也没什么变化,还是九百年前宋嫂划船烹羹的那个西湖。西湖美景,叫我身心恬静,正如这里催生的温柔羹汤将各种食材和谐统一,安抚品羹人的口腹与灵魂。在中国,厨师其实一直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医师。“药食同源”,古人诚不欺我。
2025年11月27日起,每周二、四、六中午12点,腾讯视频《100道古代美食》独家播出。传承着治国智慧的“羹”是什么味道?本周六中午不见不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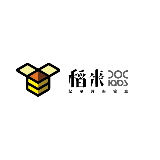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