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去深圳闯荡睡天桥,一个收废品的大叔说:跟我干,我教你
一
高铁的车窗像一块巨大的、流动的墓碑,碑身上刻着南方连绵的雨。
雨点斜斜地打在玻璃上,汇成细流,蜿蜒而下,模糊了窗外飞速倒退的山峦与田野。
车厢里很安静,只有轨道规律的“喀哒”声,像一枚枚秒针,精准地钉入时间的骨骼。
我靠在椅背上,指尖冰凉。
手机屏幕的光,在我脸上投下一片冷白。
屏幕上,是一款常用的出行软件。我丈夫徐峰的账号。
他的常用同行人列表里,有一个陌生的名字。
备注是:小安。
系统自动统计的同行次数,是八次。最近一次,就在上周。目的地,邻市的一家温泉酒店。
我点开那个头像,是一个年轻女孩的侧脸,笑容干净,背景是蓝天白云,像一株向日葵。
小安。
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公司所有姓安的员工,没有这张脸。
那么,她是谁?
我关掉手机,屏幕暗下去,倒映出我自己的脸。一张平静的、看不出太多情绪的脸。
三十九岁,林岚。我和徐峰结婚十二年,创业十五年。
从深圳城中村的一个电脑档口,做到今天,公司不大,但在行业里,也算有了一席之地。
我们没有孩子。
不是不想要,是早年拼得太狠,伤了身体。试了几年,花了无数钱,最后医生摇着头,让我们接受现实。
从那之后,我和徐峰之间,就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彼此看得见,却再也看不真切。
我们成了最默契的战友,最亲密的室友,却不再是情人。
我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走到老。
直到“小安”的出现。
像一根细小的针,悄无声息地,刺破了那个名为“稳定”的肥皂泡。
高铁报站的声音在车厢里响起,柔和的女声提醒着终点的抵达。
我拿起身边的大衣,站起身。
雨还在下。
深圳北站的灯火在雨幕中氤氲开来,像一团团模糊的、暖黄色的记忆。
我走出站厅,冷风夹着雨丝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车厢里的暖气。
我没有给徐峰打电话。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或者说,是给我自己一个答案。
二
两天前,我出差的那个晚上,我们通过一次电话。
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岚岚,还在忙?”
“嗯,刚和客户吃完饭,回酒店。”我一边说,一边脱下高跟鞋,赤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
“早点休息,别太累了。”他的声音隔着电波,有些失真。
“你呢?在家?”
“嗯,在家看文件。”
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微的猫叫。
我们家没有养猫。
我顿了一下,没有追问。
“那我挂了,你也早点睡。”
“好。”
挂断电话,我站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城市的车水马龙。
每一盏亮起的车灯,都像一个孤独的灵魂,在这座钢铁森林里仓促地游走。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雨夜。
1991年,我刚到深圳。
十九岁,兜里揣着从家里偷跑出来的三百块钱,站在深南大道的天桥上,看着脚下流光溢彩的车河,感觉自己像一粒被风吹来的尘埃。
那晚,我就睡在天桥底下。
半夜被冻醒,一个收废品的大叔,披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递给我一个滚烫的烤红薯。
大叔姓钱,别人都叫他老钱。
他看了看我冻得发紫的手,叹了口气,说:“女娃,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跟我干吧,收废品。饿不死。我教你。”
我捧着那个红薯,眼泪“吧嗒”一下就掉下来了。
不是委屈,是温暖。
那是深圳给我的第一份,也是最刻骨铭心的一份温暖。
我跟着老钱,收了三年的废品。
他教我怎么分辨不同的金属,怎么和收货站的老板们打交道,怎么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别人丢弃的“黄金”。
他常说一句话:“小岚,人活着,得像个合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有条款,有底线。谁违约,谁就得出局。”
老钱的这套“合同理论”,成了我后来人生的信条。
无论是做生意,还是结婚。
我和徐峰的婚姻,就是一份我亲手拟定的合同。
有共同财产条款,有忠诚义务条款,甚至有违约责任条款。
签下字的那一刻,徐峰笑着说我,“像在签一份商业并购案。”
我当时很认真地看着他:“婚姻,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并购案。”
他愣了一下,然后拥抱我,说:“好,都听你的。”
十二年了。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这份合同最忠实的履行者。
现在看来,有人可能想单方面撕毁它。
三
家里的钥匙插进锁孔,旋转。
门开了。
客厅里很暗,只有玄关的感应灯亮着一小片昏黄。
空气里,有一股陌生的香水味。
淡淡的,像栀子花,混着一丝甜腻。
不是我的味道。我的香水是冷冽的木质香调。
我换下鞋,把行李箱无声地放在墙边。
徐峰的卧室门关着。
我走过去,手放在门把上,却没有立刻推开。
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像沉闷的鼓点。
最终,我还是收回了手。
我转身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冰箱里很空,只有几瓶啤酒和一盒过期的牛奶。
台面上,放着一个外卖餐盒,里面的面条已经坨了,红油凝固在碗边。
我关上冰箱门,靠在冰冷的金属门上,闭上了眼睛。
我的脑子,像一台高速运转的计算机,开始飞快地处理信息,建立模型,推演各种可能性。
香水味。
外卖。
电话里的猫叫。
以及,那个叫“小安”的女孩。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清晰的结论。
我没有愤怒,也没有悲伤。
我的情绪,像被抽干了水分的海绵,只剩下一种近乎麻木的冷静。
我是一个习惯了处理危机的人。
在商场上,任何突发状况,我的第一反应都不是情绪失控,而是:
一,确认事实。
二,评估损失。
三,制定解决方案。
现在,我正在执行第一步。
我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等待。
等待天亮,等待徐峰走出那扇门。
等待他给我一个解释。
或者说,等待他亲口承认他的违约。
四
天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给黑暗的客厅镀上了一层灰白的边。
卧室的门开了。
徐峰走出来,他穿着睡衣,头发凌乱,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我时,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的表情,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惊慌,错愕,还有一丝无法掩饰的心虚。
“岚……岚岚?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只是看着他,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昨晚睡得好吗?”我问。
他喉结滚动了一下,避开我的视线,“还……还好。你怎么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想给你个惊喜。”我说。
这四个字,我说得云淡风轻,却像四根针,扎在他心上。
他的脸色更白了。
“我……我去给你倒杯水。”他转身想逃进厨房。
“不用了。”我叫住他,“徐峰,我们谈谈。”
他停下脚步,背对着我,肩膀的线条绷得很紧。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朝上,划开,停留在那个出行软件的界面上。
“小安,是谁?”
他的身体猛地一震。
沉默。
空气仿佛凝固了。
他缓缓地转过身,看着茶几上的手机,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等了很久。
久到窗外的天色,已经从灰白变成了亮白。
“我需要一个解释。”我说,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一个符合事实的解释。”
他终于抬起头,看向我。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还有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她……她只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他开口,声音干涩,“我们……就是一起出过几次差,顺路而已。”
“顺路?”我轻轻重复着这两个字,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顺路去温泉酒店?”
他的脸,瞬间血色尽失。
“我……”他张口结舌,后面的话,再也编不下去。
我看着他。
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十二年的男人。
这个曾经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抱着我说“别怕,有我”的男人。
此刻,他站在我面前,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我忽然觉得很没意思。
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这种试探与谎言的拉锯,太消耗能量,也太不体面。
“徐峰。”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
我比他矮半个头,但我仰视他的时候,气场却足以将他笼罩。
“我不想听你的谎言。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说实话。”
“否则,你知道后果。”
我的语气很平淡,但“后果”两个字,我说得很重。
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是全然的恐慌。
他知道。
他当然知道。
我们那份白纸黑字的“婚姻合同”里,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写得清清楚楚。
一旦一方出现不忠行为,过错方,将净身出户。
五
他终于还是说了。
断断续续,语无伦次。
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却只能吐出一连串绝望的泡沫。
女孩叫安然,二十三岁,刚毕业。
是公司合作的一个供应商那边派来的实习生。
年轻,漂亮,充满活力。
看他的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崇拜。
她说他成熟,稳重,有魅力。
她说在他身边,有种特别的安全感。
她说,她喜欢他。
“我……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徐峰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真的,岚岚,我没想过要背叛你。”
“可是……我太累了。”
“公司的事,家里的事,压得我喘不过气。每天回到家,面对你,我感觉自己像个……像个黑洞。”
“你太强了,岚岚。你像个永动机,永远不知道疲倦。在你身边,我……我压力很大。”
“和小安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放松。我感觉自己又变回了那个……可以为别人遮风挡雨的男人,而不是永远跟在你身后的影子。”
他说了很多。
像是在忏悔,又像是在为自己辩解。
我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
直到他说完,客厅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看着他痛苦而纠结的脸,心里没有波澜。
累?
压力大?
想找回做男人的感觉?
这些,都不能成为违约的理由。
合同就是合同。
签了字,就要履行。
“说完了?”我问。
他点点头,像个等待宣判的囚徒。
“好。”我说,“现在,我们来谈谈解决方案。”
我从茶几下,拿出一份文件,和一支笔。
那是我昨晚在客厅里,用平板电脑连夜草拟的。
一份《婚内财产及忠诚协议补充条款》。
我把它推到他面前。
“看一看。没问题的话,就签字。”
他低下头,看着那份文件,手开始发抖。
“岚岚,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明确。”我说,“你违约了。按照我们最初的约定,我可以让你净身出户。”
“但是,我念在十二年的情分上,再给你一次机会。”
“签了它。从今天起,我们重新开始。”
“如果你再有下一次,那么这份协议,就是呈上法庭的,最直接的证据。”
我的声音,冷静得像手术刀。
一刀一刀,剖开我们之间最后一点温情。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你……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他哑着嗓子问,“我们十二年的感情,在你眼里,就只是一份……一份合同?”
我笑了。
那笑容,很轻,也很冷。
“徐峰,你搞错了一件事。”
“不是我不念感情,是你先破坏了规则。”
“当你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寻找放松和安全感的时候,你就已经亲手撕毁了我们的合同。”
“我现在做的,不过是在废墟之上,重新建立秩序。”
“至于难过?”我顿了顿,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的难过,在发现这件事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
“剩下的,只有如何处理问题。”
我把笔,放在协议上,推到他面前。
“签,还是不签。你选。”
六
他最终还是签了。
手抖得厉害,名字签得歪歪扭扭。
签完之后,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坐在沙发上。
我把协议收好,一式两份,一份放进我的公文包,一份留给他。
“好了。”我说,语气像是在宣布一个会议结束,“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给你三天时间,处理好你和那个女孩的关系。我不希望再从任何渠道,听到或者看到你们有任何牵连。”
“三天后,生活恢复正常。”
他没有说话,只是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我。
那种眼神里,有恐惧,有怨恨,还有一丝……解脱?
我不想去深究。
我转身走进卧室,那个我们共用了十二年的卧室。
床上,很整洁。
但我还是掀开了被子,把所有的床单、被套、枕套,全部扯了下来,扔进脏衣篮。
然后,我打开衣柜,拿出新的。
整个过程,我的动作流畅而迅速,像一个熟练的酒店客房服务员。
换好床品,我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热水从头顶淋下,冲刷着我的身体,也仿佛冲刷着那些看不见的,肮脏的痕迹。
我不是善良。
我只是不喜欢脏。
无论是物理上的,还是情感上的。
从浴室出来,我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职业套装。
化了一个精致的妆。
对着镜子,我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自己。
眼神锐利,嘴角紧抿,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疏离感。
这才是林岚。
那个十九岁就敢一个人闯深圳的林岚。
那个跟着老钱,在废品堆里刨食,却从不喊一声苦的林岚。
那个白手起家,把一个小档口做成一家公司的林岚。
婚姻,孩子,这些东西,曾经一度让我变得柔软。
我以为,那就是幸福。
现在我明白了。
对一个从底层爬起来的女人来说,最大的安全感,从来不是男人,不是家庭。
而是掌控力。
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事业,对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拥有绝对的掌控力。
我走出卧室。
徐峰还坐在沙发上,像一尊雕塑。
“我今天要去公司处理一些事。”我说,“午饭和晚饭,你自己解决。”
他抬起头,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
我没给他机会。
“还有。”我走到玄关,换上高跟鞋,声音透过空旷的客厅,清晰地传到他耳朵里。
“克制,不是恩赐,是成年人最基本的义务。”
说完,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
隔绝了两个世界。
七
我没有立刻去公司。
我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滨海大道上行驶。
雨停了。
太阳从云层里挣扎着露出来,给海面撒上了一层碎金。
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了。
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的、怯生生的女声。
“请问……是林总吗?”
“我是。”
“我……我是安然。”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有事?”我的声音很平静。
“我……我想跟您见一面。”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徐……徐总他,跟我说分手了。我想……我想当面跟您道个歉。”
道歉?
我差点笑出声。
“没必要。”我说,“你们之间的事,是你们的事。和我道歉,没有任何意义。”
“不,不是的!”她急急地辩解,“林总,我知道我错了。我……我只是太喜欢他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会给您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伤害?”我重复着这个词,“小姑娘,你太高看自己了。”
“你对我,构不成伤害。你只是一个……瑕疵品。一个出现在我的合同里,本不该出现的,错误的条款。”
“而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错误的条款,删掉。”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然后,是压抑不住的哭声。
“林总,我知道您很厉害,很成功。徐总跟我说过,您是他最敬佩的人。”
“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他跟您在一起,真的很累。”
“他就像一棵需要阳光的植物,而您,是遮住他阳光的那棵大树。”
“他和我在一起,笑得很开心。那种笑,我从来没在你们的合照里见过。”
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
海风从半开的车窗吹进来,带着咸湿的气息。
“说完了吗?”我问。
她的哭声顿住了。
“安小姐。”我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冰冷,“我不管徐峰在你面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只告诉你三件事。”
“第一,徐峰是我法律上的丈夫。我们共同拥有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有一家公司,和过去十几年的所有资产。你,一个刚出校门的实习生,你觉得你在这场博弈里,有几分胜算?”
“第二,你所谓的‘爱情’,所谓的‘让他开心’,是建立在对另一个人背叛的基础上的。这种廉价的情感,除了能感动你自己,一文不值。”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看着远处的海平面,那里,有一艘货轮,正缓缓驶向远方。
“我,林岚,从我十九岁睡在天桥下那天起,我就明白一个道理。”
“我想要的东西,我会自己去争取。我拥有的东西,谁也别想抢走。”
“你,最好不要来挑战我的底线。”
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
然后,拉黑。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我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阳光,有些刺眼。
我从储物格里拿出墨镜,戴上。
世界,瞬间暗了下来。
也清静了。
八
那次通话之后,安然再也没有出现过。
徐峰也像变了一个人。
他开始准时下班,开始学着做饭。
他会记得我胃不好,每天早上给我熬一锅小米粥。
他会在我加班晚归的时候,留一盏灯,温一碗汤。
他不再和我谈论工作上的压力,而是会说一些轻松的话题。
我们之间,好像又回到了很多年前,刚刚创业时,相濡以沫的样子。
只是,我们都心知肚明。
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
即便用再好的胶水粘起来,裂痕也永远都在。
我们的卧室,分了床。
我睡床,他睡旁边的沙发床。
我们之间,隔着一条不到一米的过道。
却像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几次试图靠近,都被我用冷漠的眼神逼退了。
“徐峰。”我告诉他,“信任的重建,需要时间。”
“我现在,是在给你时间,也是在给我自己时间。”
他看着我,眼神黯淡下去,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生活,就像一架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而乏味地运转着。
直到有一天,我妈来了。
她提着一大袋子石榴,风尘仆仆地从老家赶来。
“岚岚,我听你爸说,你和阿峰最近……闹别扭了?”我妈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问。
我爸,是徐峰打电话叫来的救兵。
我看着徐峰,他心虚地低下头。
“妈,没什么事,就是工作上有点分歧。”我不想让老人担心。
“胡说!”我妈的眼圈红了,“阿峰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她一边说,一边用拳头捶着徐峰的后背。
徐峰也不躲,就那么站着,任由她打。
“妈,您别这样。”我拉住我妈。
“我怎么能不这样!”我妈哭了起来,“我把你交给他,是让他好好疼你的!不是让他来伤你的心的!”
“岚岚,你听妈说,男人,都一个样。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只要他知道回家,知道谁才是他老婆,你就……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日子,不都这么过来的吗?”
我看着我妈。
她一辈子,都在为家庭,为丈夫,为孩子而活。
她的世界里,隐忍和妥协,是女人的美德。
“妈。”我扶着她坐到沙发上,给她倒了杯水。
“时代不一样了。”
“在我这里,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有‘零容忍’。”
我妈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这孩子,怎么……怎么这么犟呢?”
那天晚上,我妈在厨房里,炖了一锅莲藕排骨汤。
她把徐峰叫进去,两个人关着门,说了很久的话。
我坐在客厅,能隐约听到我妈的抽泣声,和徐峰压抑的保证声。
汤炖好了。
我妈盛了一碗,端到我面前。
“岚岚,喝吧。喝了,这事儿,就让它过去。”
我看着那碗汤。
汤面上,飘着一层油花,还有几粒红色的枸杞。
很香。
是我从小喝到大的味道。
我接过来,却没有喝。
“妈。”我说,“汤,我会喝。但事,过不去。”
“我和他之间的问题,不是一碗汤,就能解决的。”
“这是我的原则。”
我妈看着我,眼神里,是全然的陌生和不解。
她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她的女儿,为什么会活得这么“硬”。
硬得像一块石头。
九
我妈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里,她用尽了各种办法,撮合我和徐峰。
她让我们一起去买菜,一起做饭,一起看电视。
她甚至把我推到徐峰的卧室里,然后把门反锁。
那天晚上,我和徐峰,隔着那条不到一米的过道,一夜无话。
我妈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叹了口气。
“岚岚,妈知道你委屈。但是,一个家,散了,就什么都没了。”
“你手里的沙子,握得越紧,流得越快。”
我抱着她,拍了拍她的背。
“妈,你放心。这个家,散不了。”
“我只是,在用我的方式,重新把它盖得更结实一点。”
送走我妈,家里又恢复了那种诡异的平静。
徐峰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他开始主动向我汇报他每天的行程,见什么人,谈什么事。
他把所有的银行卡,密码,都交给我。
公司的财务章,行政章,也全部放在我的办公室。
他像一个主动戴上镣铐的囚犯,用这种方式,向我表达他的“忠诚”。
我没有拒绝。
这是他该付出的代价。
也是我重建安全感,必须要做的一步。
时间,一天天过去。
秋天来了。
院子里的桂花开了,满屋子都是甜腻的香气。
那天,是老钱的忌日。
他三年前走的,肝癌。
我每年都会去墓园看他。
我买了一束白菊,和他最喜欢喝的二锅头。
墓碑上,他的照片,笑得一脸褶子,像个弥勒佛。
我把酒倒在墓前,蹲下来,用手擦了擦墓碑上的灰尘。
“钱叔,我来看你了。”
“公司今年效益不错,又签了几个大单。”
“就是……最近遇到点事儿,心里挺烦的。”
我絮絮叨turkey絮地,把我和徐峰的事,都跟他说了。
风吹过,墓园里的松柏,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回应我。
“钱叔,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我妈说我太硬了,会把人推开。”
“可是,我学不会软。从我十九岁那年,决定一个人来深圳开始,我就把所有的软弱,都扔掉了。”
“软弱,会让我饿肚子,会让我被人欺负。”
“只有硬起来,像个刺猬一样,才能保护自己。”
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这是自从事发以来,我第一次哭。
不是为徐峰的背叛,而是为我自己。
为那个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的,坚硬而孤独的灵魂。
我在墓园里,坐了很久。
直到夕阳西下,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徐峰。
“岚岚,你在哪儿?”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焦急。
“在外面,有点事。”
“你……你晚饭吃了吗?”
“还没。”
“那……你回来吧。我给你下了一碗面。”
一碗面。
我愣住了。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很穷,住在一个没有厨房的城中村出租屋里。
他用一个电磁炉,在阳台上,给我煮面吃。
面里,只有一个荷包蛋,和几根青菜。
我却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好。”
我听到自己说。
十
我回到家。
一进门,就闻到了熟悉的,葱油面的香味。
徐峰穿着围裙,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大碗。
“回来了?快去洗手,面要坨了。”
他的语气,很自然,就像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看着他。
看着他眼角的细纹,看着他鬓边夹杂的白发。
看着他端着那碗面,小心翼翼地,像是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我的心,忽然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不疼,但是酸。
我洗了手,坐在餐桌前。
面,还是那个味道。
我吃得很慢。
他就在对面看着我,不说话。
“我今天,去看钱叔了。”我吃完最后一口面,放下筷子,说。
他愣了一下,点点头,“应该的。”
“他以前常跟我说,做人要像一份合同,要讲规则,守信用。”
“我一直记着。”
“所以,当你的行为,超出了合同的范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启动违约处理程序。”
“清理,切割,重塑规则。”
“我承认,我的处理方式,很冷酷,很理性,甚至……毫无人情味。”
“但徐峰,那就是我,林岚。”
“一个从废品堆里爬出来的女人,我唯一懂得的,就是如何保护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切。”
“我的公司,我的家,我的尊严。”
“我没有我妈那样的智慧,可以用隐忍和妥协,去维系一段关系。我只会用最笨,也最直接的办法。”
“那就是,建立不可逾越的边界。”
徐峰静静地听着。
等我说完,他站起身,走到我身边,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了我。
他的怀抱,不再像以前那样,让我感到窒息和压力。
而是,带着一丝……久违的温暖。
“对不起,岚岚。”他的下巴,抵在我的头顶,声音闷闷的。
“是我错了。”
“我只看到了你的坚强,却忘了,你也是个女人,也需要人疼。”
“我把自己的无能和压力,当成了放纵的借口,去伤害了你。”
“你放心,以后不会了。”
“我愿意,遵守你制定的所有规则。”
“我只想……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一次……重新学着如何去爱你的机会。”
我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我就那么静静地,靠在他的怀里。
窗外,月光如水。
客厅里的那盆绿萝,不知不owo觉间,又长出了新的藤蔓。
十一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那层冰,开始慢慢融化。
他不再睡沙发床。
他搬回了床上,睡在我身边。
我们之间,依然隔着一拳的距离。
但夜里,他会下意识地,把手伸过来,轻轻地搭在我的被子上。
我没有推开。
公司的运营,也逐渐回到正轨。
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项目的研发中。
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我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和越来越深的黑眼圈。
有一天晚上,我给他冲了一杯咖啡,端到书房。
“别太拼了,身体要紧。”
他抬起头,接过咖啡,对我笑了笑,“没事,这个项目做成了,公司就能再上一个台阶。”
“到时候,你就可以轻松一点了。”
我看着他眼里的光。
那种光,我很久没见过了。
那是属于创业者的,充满激情和渴望的光。
我忽然意识到,或许安然说对了一件事。
我的强大,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他的光芒。
我习惯了冲在前面,习惯了做决策,习惯了掌控一切。
却忘了,他也曾是一个,意气风发的男人。
“徐峰。”我坐到他对面,“这个项目,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年终分红,我给你提五个点。”
他愣住了,随即笑了,“跟我还算这么清楚?”
“当然。”我看着他,很认真地说,“亲兄弟,明算账。夫妻,也是一样。”
“这是规矩。”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些我读不懂的东西。
良久,他点点头,“好,都听你的。”
十二
日子,就像白开水,平淡,却也解渴。
我们都在努力,修复着这段关系。
像两个工匠,小心翼翼地,打磨着一件有了裂痕的瓷器。
我知道,它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样子。
但或许,它可以变成一件,有着独特纹路的,新的艺术品。
周末,我们会一起去逛超市,一起去爬山。
他会记得买我喜欢吃的车厘子。
我会记得给他带他常喝的那个牌子的茶叶。
我们开始分享彼此的生活,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
虽然,有些话题,我们依然会默契地避开。
比如,孩子。
比如,安然。
那就像两道疤,结了痂,但不能碰。
一碰,还是会疼。
我脖子上,一直戴着一个玉坠。
是老钱送我的。
当年我离开他,自己去开电脑档口的时候,他把这个玉坠挂在我脖子上。
他说:“女娃,这个能辟邪,也能压惊。以后遇到事儿了,就摸摸它。钱叔,就在这儿。”
这么多年,我一直戴着。
它陪我走过了所有的风风雨雨。
那天晚上,我洗完澡,发现玉坠的绳子,断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徐峰看到了,拿过去,说:“我明天拿去金店,给你换根新的。”
第二天,他下班回来,把修好的玉坠递给我。
绳子换成了更结实的红丝线。
玉坠,也被他擦得温润透亮。
他帮我戴上。
冰凉的玉,贴着我的皮肤。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和身后,那个专注地为我系绳子的男人。
忽然觉得,一切,似乎真的可以,重新开始。
就在我以为,生活会这样,一直平静下去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
短信很短,只有一句话,和一个地址。
“林总,你真的以为你赢了吗?”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我看着那个地址。
那是市中心一个高档小区的名字。
我拿出手机,打开一个我很久没有用过的软件。
那是我之前,悄悄在徐峰车里装的定位器。
自从他签了那份协议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
我点开。
地图上,那个红色的小点,正在那个小区里,一动不动。
而现在,是晚上十点。
他说他今晚,在公司加班。
我关掉手机,走到窗边。
窗外,是深圳璀璨的夜景。
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的。
我拿起车钥匙,走出了家门。
那个被我亲手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平衡。
在这一刻,再次,轰然倒塌。
而这一次,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力气,去重建它。
我只知道,今晚,我必须去。
去那个地址,去看一看。
我的合同,我的规则,我的婚姻。
是不是,真的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笑话。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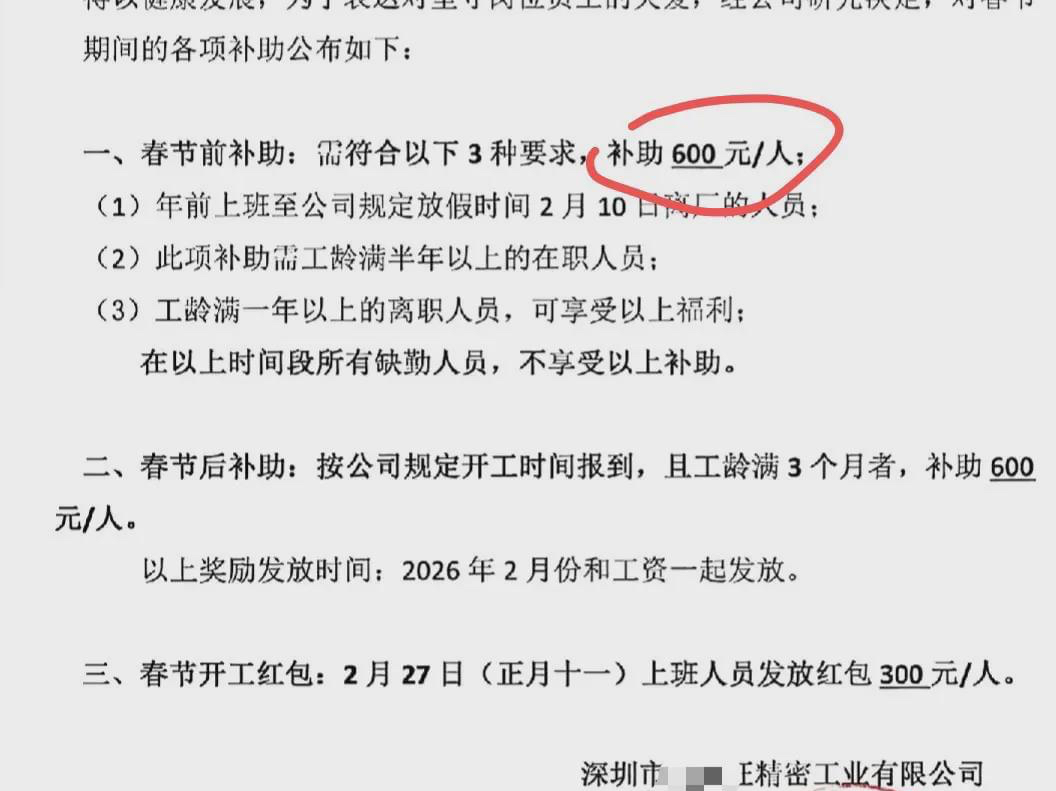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