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死前最后一道“难题”:不去八宝山,非要去种地?
1978年6月,北京的天气已经有些燥热了,但对于此时的中央办公厅来说,气氛却冷得像冰窖。
一份只有几十个字的遗嘱,把负责治丧的领导们全都整不会了。
按说像他这种级别的开国元勋,走了之后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那是组织给的荣誉,也是最后一块金字招牌。

可谁能想到,老人家临终前脑子清醒得很,对着八宝山的方向连连摆手,死活不去。
他就要去山西大寨,要把自己烧成灰,撒在那片梯田里当肥料。
这哪是安排后事,分明是把自己当成了最后一袋化肥,要给庄稼地再最后“冲”一把劲。
这事儿一传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不信,觉得这是老头子病糊涂了,要么就是在搞什么“行为艺术”。
但你要是真耐下性子,把日历一页页翻回去,扒开郭沫若这86年大起大落、在大是大非里反复横跳的人生,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一时兴起。

这是一个活得太累、背了太多骂名、也享了太多盛名的老人,在生命尽头给自己找的唯一一条退路。
说实话,郭沫若这一辈子,活得太“满”了,满到有点溢出来。
1892年他生在四川乐山一个地主大院里,家里那会儿给他铺的路多稳当啊:去日本学医,回来当个受人尊敬的大夫,这在当时那就是妥妥的金领。
1914年他真去了,结果你也猜到了,那把手术刀还没捂热乎就被他扔了。
为啥?

因为他觉的治病救不了中国人,得治脑子。
这股子不管不顾的叛逆劲儿,就像是他骨子里自带的基因,怎么压都压不住。
这事儿在老家那是大逆不道,毕竟家里还有个明媒正娶的原配呢。
但他不管,为了自由恋爱,哪怕背上陈世美的骂名也在所不惜。

这种“为了理想能把天捅个窟窿”的性格,成就了他前半生的辉煌,也埋下了后半生痛苦的雷。
时间跑到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一响,郭沫若的人生直接撞上了南墙。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送命题:一边是给他生了一堆娃的日本媳妇,一边是快要亡国的祖国。
这中间根本没有骑墙的余地。
45岁的郭沫若一咬牙,做出了那个让后人骂了半个世纪的决定——抛妻弃子,只身回国。

咱们现在拿键盘喷他“渣男”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你设身处地想想,在那个亡国灭种的节骨眼上,是选小家还是选大家?
每当夜深人静,或者有人拿私德攻击他的时候,他只能受着。
这种心里的煎熬,估计比吃黄连还苦。
如果说私生活的烂摊子还能拿“家国大义”来挡一挡,那1956年的定陵发掘,就是郭沫若这辈子真正的滑铁卢,也是他晚年心态崩盘的导火索。
那会儿他当了中科院院长,那是真想给考古界露一手。
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定陵被强行打开了。
结果呢?
考古队刚把地宫门推开,那三百年前的织锦龙袍,见风就烂,瞬间变黑,眼睁睁看着宝贝变成了垃圾。
那一幕,成了中国考古人心头永远的伤疤。

后来万历帝后的尸骨更是在动荡里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舆论炸锅了,所有的唾沫星子都喷向了郭沫若,骂他是“掘墓人”,说他为了满足好奇心毁了老祖宗的家底。
也就是在经历了这么多风光和狼狈、赞美和唾骂之后,大寨这个地方闯进了他的视线。
1964年,72岁的郭沫若第一次站在大寨的虎头山上。

他看到的不是什么风景,而是一种最原始、最粗粝的生命力。
这种冲击力对晚年的郭沫若来说太大了。
而在大寨,他看到了一种不需要解释、不需要洗白的真实——汗珠子摔八瓣,粮食就长出来,这是天地间最硬的道理。

他去了三次大寨,一次比一次激动。
说白了,他那是羡慕,甚至嫉妒那些农民活得那么干净、那么踏实。
到了1978年,躺在病床上的郭沫若,算是彻底活通透了。
八宝山那种地方,那是给完美无缺的英雄留的。
而他看看自己这一生,虽然位极人臣,但也满身枪眼。

与其死后躺在冰冷的石碑底下继续被人指指点点,不如干脆回归泥土。
他选大寨,不是为了再贴个什么政治标签,而是真心想做一回“有用”的东西——哪怕是变成肥料去喂庄稼。
6月20日,那架飞机起飞了。
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仪式,只有漫天飞舞的骨灰,飘落在山西昔阳县的梯田里。

他用一种最卑微的方式,在这个他认为最干净的地方,跟自己这拧巴的一生达成了和解。
他把自己最后一点价值,揉碎了撒进土里,这或许是他这辈子写下的最浪漫、也最沉重的一首诗。
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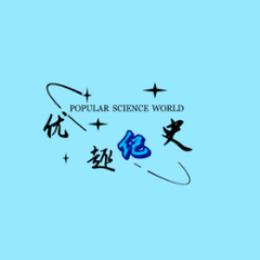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