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8日清晨,京城的秋意已经透出凉意。秦城监狱狭长的通道里,61岁的姚文元被值勤干警领到铁门前,这里是他十八年刑期的终点,也是他重新面对社会的起点。那一刻,他沉默地望向太阳,似乎在估量外面的世界究竟变得多快。
陪同前来的家人早已准备好棉外套和硬座车票。车厢里广播反复播放着港台流行曲,身边乘客谈论的是“下海”“个体户”“股市”。姚文元低头打量手里的报纸,改革、市场、外汇这几个词来回跳动,他突然冒出一句:“怎么连粮票都撤了?”邻座小伙闻声抬头,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大叔,粮票十年前就废了。”这句对话只占几秒,却像锤子一样砸在姚文元心口,提醒他时代真已彻底翻篇。
抵沪之后,他并没有在昔日的新闻单位或旧居停留,而是根据组织安排悄然转往浙江湖州。湖州一带竹林环绕,江南水汽浓重,正适合远离视线。当地派出所只知道来了一位“重点对象”,却不清楚这位不苟言笑的老人,曾在十年前的法庭上几乎把审判员逼到无话可说。
进入湖州第二个月,他开始翻箱倒柜找资料:旧报纸、批示、评论、手稿——凡是留下墨迹的都要复印备份。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抿着茶,只淡淡答一句:“怕忘了细节。”从1956年到1976年,二十年文件交叉嵌套,他用钢笔一点点写下,白天伏案,夜里对照资料改词删句。由于长期缺乏运动,手指关节肿胀,他干脆改用毛笔,“这样写得慢,脑子也清楚”。
到了1999年春天,42万字的手稿初稿装订成册,另有一份5万字的补遗提纲。编写过程比外界想象艰苦得多:没有电脑排版,全靠硬笔与蜡纸;引用文件需要自行注明出处,否则无法通过审读;部分事件中涉及的当事人尚健在,每一句评述都可能触及法律边界。不得不说,这部手稿更像一份自我辩白和一纸口供的混合体。
有意思的是,消息一泄露,香港、台湾乃至北美的学术出版社迅速闻风而动。1999年年底,三家香港出版社集体派代表赶到杭州,提出五百万港币买断海外出版权,条件是保证原文不删改。提出报价的人是一位惯用英文名片的“顾先生”,自称代理学术市场。对方在湖州宾馆房间里摊开支票,当场表态:“如果姚先生点头,今天就可以开具预付款。”这笔钱在当时足以在上海买下四套花园洋房。
然而交易最终未能达成。原因并非像外界传说的“姚文元狮子大开口”,也并非“顾先生”临阵反悔,而是北京方面事先递到湖州的一个红头文件:回忆录可以送审,但不得外流,尤其不能在境外公开售卖。对刚刚获得自由的姚文元来说,这一纸要求等同命令。加之每月四千元的生活补贴足以维持衣食,他权衡后婉拒出版商,只留下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文字不会跑,急什么?”
实际上,五百万港币究竟能否一次到账也存疑。出版圈私下议论,那位“顾先生”更多是试水行情,真正掏钱还得看审稿风险和律师评估。如果回忆录被认定含有大量未解密档案,海关环节就过不去,印刷厂也不敢开机。投资人很可能只是打着高价旗号制造话题,未必真的准备全额支付。

2001年至2003年间,国内有关部门先后派出三名研究者赴湖州,与姚文元进行对口访谈,核实回忆录中涉及的部分人名、笔名和会议记录。其中涉及1967年上海“联络站”夺权行动的章节,删减近一万字;“重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节,改动约三千字。姚文元偶尔表现出不满,但整体配合,甚至主动提供同一时期他编辑《解放日报》的版面成果,显露出对“史料”二字的强烈执念。
2005年12月某天凌晨,他在湖州住处离世,心脏骤停,没有留下最后交代。当地卫生院的死亡证明列明死因为“心源性猝死”。新华社随后发布通告,字数不多,只提到“曾任文化专案负责人”。坊间随即再度炒热那张五百万的支票,有自媒体写成“神秘买家已提前采购”,更有人称“手稿在港岛印厂悄悄开印”。但是,经香港出版总会内部调查,并未找到任何付印或报版纪录。
现在回看,那笔五百万港币更像一次媒体放大后的市场噱头。姚文元手里确实握有42万字手稿,但受限于审批与法律环境,公开发行的可能性极低;对投机资本而言,赌这本书无异于赌一个遥遥无期的许可。至于手稿最终下落,据知情人士透露,两份原件已分别由中央档案馆和浙江省档案馆封存,十年之内不会解封。500万买稿的故事,留在茶余饭后的聊天里,倒也成了那个时代关于纸质档案的最后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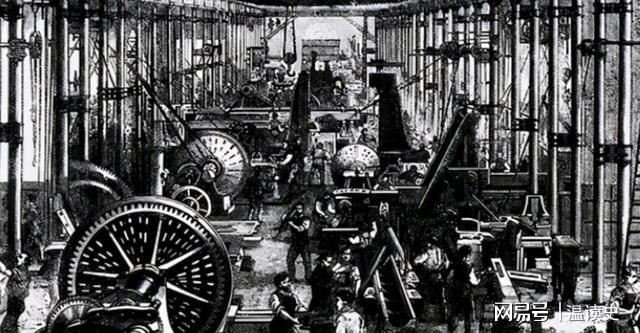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