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的目光挣脱地球的束缚,投向夜幕中璀璨的星河,一个古老而执着的疑问便在文明的基因中苏醒: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吗?从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之外是否有其他居所”的思辨,到现代科幻作品中对星际文明的瑰丽想象,这种对宇宙同伴的探寻从未停歇。

直觉告诉我们,生命不该是地球的专属造物。毕竟,可观测宇宙中存在着超过2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又孕育着数以亿计的恒星,即便只有万分之一的恒星系统拥有类地行星,万分之一的类地行星诞生生命,万分之一的生命演化出智慧,宇宙中也该遍布文明的踪迹。这份基于概率的乐观猜想,支撑着人类向宇宙深处不断发问。
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对地外生命的探讨始终停留在哲学与想象的范畴。科学研究遵循着严谨的逻辑实证原则,对于无法观测、无法验证的命题往往避而不谈。直到20世纪90年代,天文学界的一项突破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1995年,天文学家米歇尔·梅耶和迪迪埃·奎洛兹首次确认了太阳系外行星“51 Pegasi b”的存在,这颗围绕类太阳恒星旋转的气态巨行星,如同打开了宇宙的一扇新窗,让人类意识到行星系统在宇宙中并非特例。
此后二十余年间,系外行星探测技术飞速发展,开普勒太空望远镜、TESS凌日巡天卫星等设备相继服役,截至目前,人类已发现的系外行星数量已突破5000颗,远超原文中“接近300颗”的早期数据。
这些探测成果呈现出丰富的行星图景:既有像木星一样的气态巨行星,它们因体积庞大、引力效应显著而更容易被发现;也有岩石质地的类地行星,其中不乏处于“宜居带”内、可能存在液态水的天体。
2008年欧洲天文学家发现的三颗超级类地行星,便是早期类地行星探测的重要里程碑。而近年来,更精密的观测揭示了更多惊喜——NASA在202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已发现的53颗低质量类地系外行星中,26%可能是地质活动活跃的海洋世界,17%可能存在冰火山活动的寒冷海洋行星,这些拥有地下液态水和地质循环的天体,极有可能成为生命的宜居港湾。这些发现不再仅仅是“寻找地外智慧生命”(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简称SETI)运动的间接证据,更将地外生命的搜寻范围从“类地行星”拓展到了更广泛的“宜居天体”范畴。
哈佛大学物理学家、SETI领域的领军人物保罗·霍洛维茨,在1996年接受《时代杂志》访谈时的表态,正是当时天文学界乐观情绪的缩影:“若问宇宙中的智慧生命,那是绝对有的。若问银河系中有没有,极有可能我会说几率或大或小,全看你怎么想。”这种信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系外行星探测初期成果与概率逻辑之上的合理推断。然而,这份热情很快便遭遇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终极拷问——费米悖论。

195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与同事讨论地外生命问题时,突然抛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直击核心的疑问:“他们在哪里?”这个疑问后来被正式命名为“费米悖论”,其完整表述是:如果宇宙中广泛存在技术发达的地外智慧生命,那么他们理应通过星际航行或电磁信号等方式留下存在的痕迹,为何人类至今从未发现任何确凿证据?无论是拜访地球、主动联络,还是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的热量、光或电磁辐射,都未被人类观测设备捕捉到。费米悖论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部分过于乐观的猜想,也迫使天文学界开始冷静思考:地外智慧生命的存在,真的如概率推断那般普遍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仅凭哲学思辨和定性猜想远远不够。科学家们迫切需要一种定量工具,将影响地外智慧生命存在的复杂因素系统化、公式化,从而精准估算其存在概率。

1961年,为筹备人类历史上第一次SETI正式会议,射电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公式,这便是后来被全球熟知的“德雷克等式”。该公式旨在估算银河系中目前能够被人类探测到的技术文明数量,为地外生命搜寻提供了明确的科学框架。尽管自提出以来,德雷克等式始终伴随着争议——核心争议在于部分变量的取值缺乏明确观测依据,导致计算结果差异巨大——但它至今仍是人类量化地外智慧生命存在概率的最核心、最权威的工具。
对地外生命存在概率的计算,本质上是对一系列宇宙演化与生命进化关键环节的概率叠加。宇宙并非静止的舞台,而是一个动态演化的系统:恒星在星云的引力坍缩中诞生,在核聚变的燃烧中存续,最终在燃料耗尽后走向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的终结;行星在恒星形成的尘埃盘中凝聚而成,有的与恒星保持适宜距离,形成稳定的轨道环境,有的则被恒星引力吞噬,或被抛出恒星系统成为“流浪行星”。在这亿万星体的生灭循环中,只有极少数天体能够满足生命诞生与存续的苛刻条件。
而生命本身,更是宇宙中最复杂、最难以捉摸的变量。从化学演化到生物诞生,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从简单生命到智慧文明,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行星可能只演化出复杂的有机分子——比如蛋白质、核酸等生命的基础物质,却始终未能跨越“非生命到生命”的鸿沟;有些行星可能孕育出了单细胞微生物,却因环境变化或进化瓶颈,永远停留在低级生命阶段;只有极少数行星,才能幸运地孕育出能够发展出技术、实现星际通讯的智慧文明。更重要的是,任何文明都无法摆脱“诞生-发展-消亡”的周期律:地球上,恐龙统治地球超过1.6亿年却因小行星撞击而灭绝;人类历史上,罗马帝国、玛雅文明等曾经辉煌的文明也最终走向衰落。地外文明若存在,大概率也会面临类似的命运,可能在发展出可探测的技术之前就已消亡。

弗兰克·德雷克在构建等式时,首先明确了核心研究目标:并非所有地外生命,而是“银河系中能够与人类进行星际通讯的智慧文明”——因为只有这类文明,才有可能被人类的观测设备探测到。在此基础上,他将影响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拆解为7个核心变量,构建出如下公式:
N = R×fp×ne×fl×fi×fc×L
其中,N代表银河系中目前可探测的技术文明数量,其余7个变量分别对应从恒星形成到文明存续的完整链条,每个变量的含义与取值争议如下:
1. R:星系中恒星的形成速率。这是整个等式中取值最明确、最具共识的变量。根据对银河系的观测,作为典型的旋涡星系,银河系中每年大约有4颗新恒星诞生,这一数值经过多年观测验证,误差范围较小。
2. fp:拥有行星系统的恒星比例。随着系外行星探测技术的成熟,这一变量的取值逐渐清晰。早期观测认为fp可能在0.5左右,但近年来的研究显示,绝大多数类太阳恒星都拥有行星,甚至一些红矮星周围也存在行星系统,目前天文学界普遍认为fp的取值接近1,即几乎所有恒星都拥有自己的行星系统。
3. ne:每个行星系统中,处于“宜居带”、具备生命诞生基本条件的行星数量(类似地球的行星)。早期基于太阳系的观测,认为ne约为0.25(太阳系8颗行星中,仅有地球明确处于宜居带并诞生生命)。但最新研究显示,宜居带的定义并非绝对——除了表面存在液态水的行星,拥有地下液态海洋的冰卫星、存在冰火山活动的寒冷海洋行星,也可能具备宜居条件。因此,ne的取值存在较大争议,保守估计为0.1-0.5,乐观估计可达到1-2。
4. fl:宜居行星上实际诞生生命的比例。这是等式中第一个涉及生命起源的核心变量,也是争议最大的变量之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只要行星具备适宜的环境(液态水、稳定的能量来源、复杂的有机分子),生命的诞生是必然结果,因此fl取值接近1;但也有科学家认为,生命起源是一系列极其偶然的化学与物理过程的叠加,地球生命的诞生可能是宇宙中的特例,因此fl的取值可能极低,甚至接近0。
5. fi:诞生生命的行星上,演化出智慧生命的比例。这一变量同样充满争议。地球生命演化史显示,从单细胞生物到智慧人类,经历了超过35亿年的时间,期间多次遭遇灭绝事件,智慧的诞生并非必然。有观点认为,智慧是生物适应环境的一种极端表现,并非进化的唯一方向,因此fi的取值可能较低;也有观点认为,随着生命的复杂化,智慧的出现是进化的必然趋势,fi取值可接近0.5。
6. fc:演化出智慧生命的行星上,发展出能够进行星际通讯技术的文明比例。这一变量与文明的技术发展路径相关。人类文明在掌握无线电技术后,才具备了星际通讯的能力,这一过程大约用了数千年。有观点认为,只要智慧生命持续发展,最终都会掌握星际通讯技术,因此fc取值接近1;但也有观点认为,部分文明可能因环境限制或自身选择,始终无法发展出相关技术,或主动选择隐藏自身存在,因此fc的取值可能低于0.5。
7. L:技术文明能够维持可探测状态的时间长度。这是整个等式中最不确定、对结果影响最大的变量。文明的存续受到多种因素威胁:小行星撞击、气候变化、资源枯竭、核战争、人工智能失控等。早期德雷克与卡尔·萨根等科学家乐观地认为,L的取值可达到100万年以上;但近年来的研究则更为保守——2002年《怀疑论者》发行人迈克尔·舍默通过分析人类历史上60个文明的存续时间,推断L的取值仅为304.5年-420.6年;2025年的一项研究甚至提出,考虑到能源消耗、环境危机等因素,技术文明的可探测时间可能仅为几十年。

基于不同的变量取值,德雷克等式的计算结果差异巨大。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典型的取值,直观感受这种差异:
乐观场景(萨根的估算):R=4,fp=1,ne=2,fl=1,fi=0.5,fc=0.5,L=1000000。代入公式可得:N=4×1×2×1×0.5×0.5×1000000=1000000。即银河系中可能存在100万个可探测的技术文明。
中性场景(德雷克的原初估算):R=4,fp=0.5,ne=0.5,fl=0.5,fi=0.5,fc=0.5,L=100000。计算结果为:N=4×0.5×0.5×0.5×0.5×0.5×100000=100000,即10万个可探测文明。
保守场景(舍默的估算):R=4,fp=0.5,ne=0.25,fl=0.2,fi=0.2,fc=0.2,L=304.5。计算结果为:N=4×0.5×0.25×0.2×0.2×0.2×304.5≈2.44,即银河系中可能仅有2-3个可探测文明,甚至可能只有人类文明。
这种巨大的结果差异,正是德雷克等式的核心争议所在。但即便如此,它依然为SETI运动提供了明确的研究方向——通过观测逐步缩小各变量的取值范围,从而更精准地估算地外文明的存在概率。难怪20世纪60年代,当天文学家们首次通过德雷克等式得出乐观结果时,会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地外生命的搜寻中。那么,这些搜寻工作究竟取得了哪些进展?又面临着哪些困境?
在德雷克等式的指引下,SETI运动明确了两大搜寻方向:一是“主动接触”,即人类主动向宇宙发送信号,尝试与地外文明建立联系;二是“被动监听”,即通过射电望远镜等设备,捕捉宇宙中可能来自地外文明的电磁信号。从实践来看,“被动监听”始终是SETI的主流方式——因为主动发送信号需要明确目标方向,且存在暴露地球位置的潜在风险;而被动监听则更为稳妥,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宇宙区域。
1974年,阿雷西博天文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主动信号发送——“阿雷西博信息”。这串长度为210字节的二进制代码,包含了人类文明的核心信息: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人类的基本生理结构、DNA的化学组成、关键元素的原子序数等。信号被指向距离地球25000光年的球状星团M13,因为这个星团包含数十万颗恒星,存在宜居行星与智慧文明的概率相对较高。不过,由于M13距离地球过于遥远,信号到达目的地需要25000年,即便那里存在智慧文明并立即回复,人类也需要再等待25000年才能收到回应。因此,这类主动发送信号的尝试,更多是象征性的科学探索,而非实用的联络手段。
被动监听的核心工具是射电望远镜。与光学望远镜相比,射电望远镜能够捕捉到波长更长的电磁信号,而这类信号在宇宙中传播时,受到星际尘埃、气体的干扰较小,是星际通讯的理想选择。SETI的监听工作有明确的技术标准:首先,监听频率集中在1000MHz-3000MHz的微波频段,这一频段被称为“宇宙安静带”,宇宙背景辐射的干扰极小,适合信号传输;其次,重点监听1420MHz的氢原子发射线——氢是宇宙中最丰富、最原始的元素,任何智慧文明都不可能忽视氢的存在,因此这一频率被认为是地外文明最可能选择的通讯频率,被称为“宇宙通信用频”。
在半个多世纪的监听历程中,SETI取得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疑似信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77年的“Wow信号”。

当年8月15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大耳朵”射电望远镜,在监听1420MHz频段时,捕捉到一个持续72秒的强烈射电信号。信号强度极高,远远超过宇宙背景辐射,观测员杰瑞·埃曼在分析数据时,激动地在打印纸上写下“Wow!”,这一信号也因此得名。“Wow信号”的频率、强度都符合地外文明信号的特征,但遗憾的是,后续多次对同一方向的监听,都未能再次捕捉到该信号,因此无法确认其是否来自地外文明。除了“Wow信号”,SETI还捕捉到一些其他疑似信号,但均因无法重复验证而未能成为确凿证据。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监听无果,让天文学界对德雷克等式的取值逐渐趋于保守。曾经断言“宇宙中必有智慧生命”的保罗·霍洛维茨,后来通过优化变量取值,计算得出N≈1000,远低于早期的乐观估算。而迈克尔·舍默对L变量的严苛取值,更是将N的结果压低至1以下——这意味着,人类可能是银河系中唯一的技术文明。这种保守化的趋势,并非对“地外生命存在”的否定,而是对宇宙复杂性与生命稀缺性的重新认知。
近年来,随着天文学、生物学、信息学的跨学科融合,科学家们开始尝试优化德雷克等式,以解决其变量取值模糊的问题。2025年,arXiv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指出,原等式中的L变量(文明可探测时间)定义过于模糊,应替换为更具体的变量,包括文明的能源消耗能力、信号传播范围、熵产生速率等,这些变量能够更精准地反映文明的可探测性。该研究通过新的变量计算得出,技术文明的可探测时间可能仅为几十年,因此SETI需要扩大监听范围,至少覆盖100颗以上的邻近恒星,才有可能在数千年内捕捉到有效信号。
与此同时,新一代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为SETI带来了新的希望。

中国的FAST“天眼”射电望远镜,凭借500米的口径,成为目前世界上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已累计获得超过116小时的SETI观测时间,在高灵敏度信号捕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国际大科学工程SKA(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则通过多基线干涉阵的设计,能够有效压制地面干扰信号,精准定位信号源,与FAST形成观测天区互补,其“生命摇篮”项目已将地外文明搜寻列为核心科学目标之一。这些先进设备的加入,让SETI的监听范围更广、灵敏度更高,有望突破此前的观测瓶颈。
值得注意的是,SETI的探索范围也在不断拓展。早期的搜寻主要集中在银河系内,但宇宙中存在着2万亿个星系,即便每个星系中仅有3-4个可探测文明,整个宇宙中的智慧文明数量依然极为庞大。因此,部分科学家提出“跨星系SETI”的构想,通过监听星系级别的电磁信号,寻找更遥远的地外文明。这种构想虽然面临着信号衰减、干扰加剧等技术难题,但为地外生命搜寻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SETI的支持者而言,“监听无果”并非放弃的理由,反而更能激发探索的决心——正如博彩者的心态:“如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这种探索精神,正是科学进步的核心动力。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海里始终浮现着《超时空接触》中的经典场景:艾莉·爱罗薇躺在新墨西哥州荒漠的车顶上,仰望璀璨星河,射电望远镜的天线在她身后缓缓转动。突然,耳机中传来一阵规律的、脉冲式的无线电信号,那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回响,是她追寻一生的答案。她飞奔回实验室,一边大声向同事下达指令,一边调整望远镜的观测参数,试图锁定信号源。这个场景之所以令人动容,不仅因为它展现了“发现地外文明”的激动与狂喜,更因为它折射出人类对“宇宙归属感”的深层渴望——我们害怕孤独,渴望证明自己并非宇宙中的偶然与特例。
第一次看《超时空接触》时,我尚未接触德雷克等式,那时的我和艾莉一样,坚信宇宙中必然存在其他智慧生命,坚信人类终有一天会与他们相遇。而当我深入了解德雷克等式的变量争议、SETI的半个世纪探索历程后,才真正意识到:地外智慧生命的存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稀缺。银河系或许真的如舍默计算的那样,只有人类一个技术文明;那些曾经被我们寄予希望的类地行星,可能只是一片没有生命的荒芜之地;那些在宇宙中传播的电磁信号,可能只是恒星演化的自然产物,而非智慧文明的问候。
但这种“稀缺性”的认知,并非一件坏事。正如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德雷克项目”所强调的,对地外生命的探索,本质上是对地球生命独特性与脆弱性的反思。德雷克等式中的每个变量,都是地球生命与人类文明得以存在的“幸运密码”:银河系每年4颗的恒星形成速率,让太阳系拥有了稳定的能量来源;地球恰好处于宜居带,拥有液态水与适宜的大气;生命在35亿年的演化中,多次躲过灭绝危机,最终诞生智慧;人类文明成功发展出无线电技术,得以向宇宙发出信号。这一系列“幸运”的叠加,才造就了今天的人类文明。
地外生命搜寻的深层意义,早已超越了“寻找宇宙同伴”本身。从科学层面,它推动了天文学、生物学、工程学的跨学科发展——SETI对高精度观测设备、海量数据处理算法的需求,催生了射电望远镜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的迭代,这些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脉冲星探测、医疗数据分析等领域;从哲学层面,它重构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定位——如果地外文明存在,我们将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意识到自己只是宇宙文明共同体的一员;如果地外文明不存在,我们将更深刻地认识到地球与人类文明的珍贵,从而更加重视对地球环境的保护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回到最初的疑问: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吗?目前的答案依然是“未知”。德雷克等式给出了探索的框架,SETI的观测正在逐步缩小未知的范围,新一代观测设备的加入,让我们离答案更近了一步。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个射电望远镜会突然捕捉到来自宇宙深处的清晰信号,那将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现;或许我们将永远无法找到地外文明,但这种探索本身,就已经让人类的视野变得更加广阔,让我们对生命与宇宙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
就像艾莉·爱罗薇在电影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宇宙中只有我们,那也太浪费空间了。”这份乐观与执着,正是人类探索精神的最好写照。无论最终答案如何,对地外生命的搜寻都将继续下去——因为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认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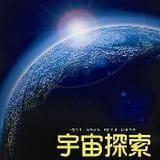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