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府曲阜县有位医士,姓魏名承祖,世代行医,尤擅接生一道。经他手落地的婴儿,百无一失,从未有过夭折之例,乡邻们都敬称他为“魏神医”。承祖性情温厚,心善如佛,不论病患家贫家富,只要有人相请,无不应允,深夜顶着风霜出诊更是常事。
雍正七年深秋,寒意浸骨。承祖应约去三十里外的李家庄接生,忙前忙后直到三更天,产妇才平安诞下一名男婴。主人家盛情留他歇息,承祖念着家中刚满月的妻儿,婉言谢绝了,只讨了盏油纸灯笼,挑着沉甸甸的药箱,踏着月色往家赶。
月色昏黄如蒙尘的银箔,洒在荒寂的官道上。路旁的老树枝桠交错,影影绰绰地映在地上,风一吹便扭曲摇摆,活像张牙舞爪的鬼影。承祖走惯了夜路,本不畏惧这些,可今夜秋风萧瑟,卷着枯叶打在灯笼上,让烛火忽明忽暗,光影变幻间,竟平添了几分疹人的寒意。
行至乱葬岗附近,忽闻路旁矮树丛后传来断断续续的女子呻吟声,细弱却急促,听得人心里发紧。承祖脚步一顿,侧耳细听,那声音里满是痛苦,不似寻常路人遇险。
“是谁在那里?”他扬声问道,话音在空旷的夜色里荡开,却无人应答,只有呻吟声愈发急切,像是快撑不住了。
承祖犹豫片刻,医者仁心终究压过了顾虑。他握紧药箱提梁,提着灯笼缓步走过去,拨开半人高的杂草与树丛。月光下,只见一个女子蜷缩在地上,身着一袭褪色的红裙,面色惨白如纸,双手死死捂着隆起的腹部,额上布满豆大的冷汗,发梢都被浸湿了。见有人靠近,她眼中先是闪过一丝惊恐,随即化为哀求,虚弱地抬了抬眼。
“先生……救救我……”女子声音微弱得像风中残烛,气若游丝。
承祖见她腹部高高隆起,显是身怀六甲,心下了然:“你是要生产了?家在何处?我送你回去找稳婆。”
女子缓缓摇头,泪水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混着冷汗浸湿了衣襟:“我没有家……先生,我快不行了,求你……求你帮我接生……”
承祖行医多年,从未见过产妇独自一人在这荒郊野岭生产的,心中虽满是疑虑,可看着她痛苦不堪的模样,终究不忍置之不理。“此处风大露重,不是生产的地方。我扶你去前面的土地庙,那里能避避风。”
女子点了点头,承祖放下药箱,小心翼翼地将她扶起。入手处一片冰凉,竟无半分活人的暖意,他心中猛地咯噔一下,下意识低头看向女子的脚——月光皎洁,那双脚竟轻飘飘地悬在半空,未沾半点尘土!
承祖头皮发麻,浑身汗毛倒竖:这分明是鬼!他本能地想撒手逃离,可女子痛得蹙紧眉头,腹中隐隐有动静传来,呻吟声撕心裂肺,带着对生命的眷恋与哀求。
“先生……求你了……”女子艰难地转头看他,眼中竟渗出两行血泪,“我死得冤,可孩子是无辜的,不能再跟着我受苦……”
承祖心中一软。他想起家中刚满月的儿子,粉雕玉琢的模样,又念及无论人鬼,母爱总归是真切的。他咬了咬牙,压下心中的惧意:“你……你且忍着,我带你去庙里。”说罢,稳稳地扶着女子往土地庙走去。
土地庙早已破败不堪,蛛网挂满梁柱,灰尘厚积,只有一尊泥塑的土地公像歪斜地立在角落,神色模糊。承祖将女子扶到墙角的草堆上,打开药箱,取出干净的布巾、剪刀和止血药,又点燃了随身携带的艾草——艾草能驱邪避秽,他虽决意帮忙,却也不得不防。
艾草燃起,青烟袅袅。女子似对艾草气息颇为不适,微微瑟缩了一下,却依旧咬牙忍着,没有半句怨言。“先生,我知晓自己非人,不敢害你,只求你保我孩子一命。若能如愿,来世做牛做马,我定当报答你的大恩。”
承祖不再多言,定了定神,开始为她接生。他虽是男子,却接生过数百名婴儿,手法娴熟老练。只是这女子情况格外凶险,似是难产,折腾了一个多时辰,婴儿仍迟迟不肯降生。
女子痛得几乎昏厥,气息越来越弱,那袭褪色的红裙上,渐渐渗出点点暗红血迹,在月光下显得愈发诡异。“先生……保孩子……一定要保孩子……”她突然伸出手,死死抓住承祖的衣袖,那力气竟大得惊人,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肉里。
承祖额头满是冷汗,既有劳累,更有焦急。他急中生智,取出银针,快速在女子几处催生穴位上扎下,又从药箱里取出一小瓶参汤——这本是给产后体虚的产妇准备的,此刻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小心翼翼地喂了女子两口。
片刻后,女子腹中传来一阵明显的异动。她像是积攒了最后一丝力气,猛地发力,一声凄厉的痛呼划破寂静的夜空。紧接着,一声微弱却清晰的啼哭响起,一个瘦小的婴儿终于降生了。
承祖连忙剪断脐带,用干净的布巾将婴儿细细裹好。那婴儿虽瘦小,哭声却中气十足,断断续续的啼哭里,满是顽强的生命力。
女子看着襁褓中的婴儿,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眼神却渐渐涣散。“多谢先生……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了……”她颤抖着从怀中摸出一块温润的玉佩,塞进婴儿襁褓里,“若日后遇着姓苏的人家……把孩子和玉佩……交给他……”
话音未落,女子的身影便渐渐变得透明,化作一缕青烟,在月光中缓缓消散,只留下那身褪色的红裙,轻飘飘地落在草堆上,仿佛从未有人穿过。

承祖抱着啼哭的婴儿,愣在原地良久。手中的玉佩温润细腻,竟带着一丝淡淡的暖意,驱散了些许夜寒。他低头看向怀中的婴儿,小小的脸庞皱巴巴的,闭着眼睛,哭声虽弱,却顽强得令人心疼。
这一夜,承祖终究没能回家。他抱着婴儿,在破败的土地庙里守了半宿,直到天快亮时,才提着药箱,小心翼翼地抱着孩子往家赶。
到家时,天已微亮,东方泛起一抹鱼肚白。妻子赵氏见他抱着个陌生婴儿回来,惊得瞪大了眼睛,连忙迎上前:“当家的,这……这是哪里来的孩子?”
承祖疲惫地坐下,喝了杯热水,才将昨夜遇鬼母托孤的事一五一十地告知妻子。赵氏听得心惊肉跳,可当她看到襁褓中婴儿乖巧睡着的模样,小小的脸皱巴巴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惹人怜爱,心中的惧意便淡了几分。
“这孩子着实可怜,女鬼托孤,咱若是不管,她在九泉之下也不安心。”赵氏叹了口气,轻轻抚摸着婴儿的小脸,“只是……她毕竟是鬼胎,养在咱们身边,会不会招来什么灾祸?”
“她生下来便有气息,哭声清亮,与寻常婴儿别无二致,想来是借了那女鬼最后的精气,已是个活生生的孩子了。”承祖也轻抚着婴儿,目光温柔,“你看这玉佩,上面刻着个‘苏’字,定是她亲生父母的信物,咱们先养着,再慢慢打听姓苏的人家。”
夫妻二人商议已定,决定暂时收养这孩子。赵氏刚生过孩子,奶水充足,便一并喂养两个婴儿,倒也方便。承祖为孩子取名“魏念苏”,意为不忘其本,铭记她的身世。
念苏虽起初瘦小,却很能吃,被赵氏悉心照料了几日,便养得白白胖胖,哭声也愈发洪亮起来。她与承祖的儿子魏念亲一起,成了家中的两个小宝贝。只是念苏夜里常无故啼哭,一哭便停不下来,任凭赵氏怎么哄都没用。后来承祖发现,只要将那块苏字玉佩放在她枕边,她便能立刻安静下来,睡得安稳香甜。赵氏感叹道:“怕是她娘在惦记着她,这玉佩是念想,有它在,孩子才安心。”承祖听了,心中愈发不忍,夜里便多起身照看念苏,总觉得对不住那素未谋面、舍命保子的女鬼。
转眼半年过去,念苏渐渐长大,眉眼间已显露出几分清秀,尤其那双眼睛,像极了夜空中的月光,清澈透亮,却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承祖时常拿着那块苏字玉佩端详,四处向乡邻打听姓苏的人家,可曲阜县及周边村镇姓苏的不在少数,却始终没有头绪。
这日,承祖去县城赶集采买药材,路过一家布庄时,忽闻里面传来打骂声和孩童的哭喊声。他驻足一看,只见布庄老板正拿着鸡毛掸子抽打一个学徒。那学徒约莫十三四岁,穿着破旧的短褂,面黄肌瘦,却长得眉清目秀。他被打得蜷缩在地上,浑身发抖,却咬着牙不肯求饶,眼神里满是倔强。
承祖看不过去,连忙上前劝阻:“老板,这孩子年纪尚小,犯了什么过错,值得你下如此重手?”
布庄老板见是远近闻名的魏神医,脸上的戾气收敛了些,却仍愤愤道:“魏先生有所不知,这小东西竟敢偷我的钱!要不是看他还有点力气能干活,我早把他赶出去饿死了!”
“我没有偷!”学徒挣扎着抬起头,眼眶通红,却倔强地喊道,“是你自己把钱弄丢了,凭什么赖在我头上!”
“还敢顶嘴!”老板怒火又起,扬起鸡毛掸子就要再打,被承祖伸手拦住。“些许钱财,何必如此动怒。这孩子我看着面善,不如你把他卖给我,我正好缺个帮着抓药、打理药铺的帮手。”
布庄老板本就嫌这学徒性子倔强,不好管教,闻言正中下怀,当即要了五两银子,便让承祖将人领走了。
路上,承祖见学徒浑身是伤,便取出随身携带的药膏给他涂抹,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为何会在布庄当学徒?”
学徒低头看着地上的影子,声音沙哑道:“我叫苏明,没有家。爹娘早死了,去年流落到这里,被布庄老板收留,其实就是给他当牛做马。”
“你姓苏?”承祖心中猛地一动,连忙从怀中取出那块苏字玉佩,递到苏明面前,“孩子,你看这玉佩,认得吗?”
苏明抬眼一看,目光落在玉佩上时,眼睛瞬间睁大,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涌出:“这是……这是我娘的玉佩!我爹说,我娘当年生产时难产死了,这玉佩是她唯一的念想……我娘肚子里还有个妹妹,我爹说,妹妹也跟着娘一起去了……”
承祖愣住了,原来念苏竟是苏明的亲妹妹!他连忙将念苏的来历一五一十地告知苏明。苏明听得泣不成声,“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承祖连连磕头:“魏先生,您是我苏家的大恩人!我妹妹……我妹妹现在在哪里?我能看看她吗?”
承祖连忙扶起他,拍了拍他的肩膀:“快起来,孩子。你 妹妹就在我家,被我妻子悉心照料着,过得很好。”
回到家,苏明一眼就看到了赵氏怀里的念苏。他快步走上前,小心翼翼地看着,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轻轻喊了声:“妹妹……”念苏似是天生与他亲近,竟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摸着他的脸,咯咯地笑了起来。赵氏见了这一幕,也忍不住红了眼眶:“真是天意啊,让你们兄妹俩重逢了。”
苏明便留在了魏家,帮着承祖打理药铺。他聪明伶俐,又肯吃苦耐劳,学东西极快,深得承祖夫妇喜爱。他对念苏更是呵护备至,有好吃的先给妹妹留着,晚上还会坐在床边给她讲故事,哄她入睡。
念苏渐渐长大,性子愈发活泼开朗,只是夜里偶尔还会啼哭。每当这时,苏明便会拿起那块苏字玉佩,轻轻放在她枕边,轻声安慰道:“妹妹不怕,哥哥在呢,娘也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念苏听了,便会渐渐安静下来,睡得格外香甜。
这年中元节,承祖带着苏明和念苏去乱葬岗附近烧纸。苏明在当年女鬼蜷缩的矮树丛旁,摆上了娘生前最爱的桂花糕,对着空旷的夜空磕了三个头,声音哽咽却坚定:“娘,谢谢您拼了性命把妹妹留下来。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妹妹,我们兄妹俩会好好活下去的,您安息吧。”
念苏似懂非懂,也学着哥哥的样子磕了个头,奶声奶气地说:“娘,我会听话的,会好好跟哥哥在一起。”
一阵秋风吹过,卷起地上的纸灰,打着旋儿飞向天空,像是女子温柔的回应。承祖望着天边渐渐沉下的晚霞,心中一片安宁。
后来,苏明勤奋好学,不仅跟着承祖学通了医术,还继承了他的药铺,成了当地有名的大夫。他沿袭了承祖的品性,医术精湛,为人和善,尤其对贫苦的产妇和孩童,常常分文不取,深受乡邻爱戴。念苏长大成人后,嫁给了一个老实本分的秀才,夫妻和睦,不久后便生了一双可爱的儿女。
每年清明和中元节,苏明都会带着念苏,还有自己的妻儿,一起去乱葬岗祭拜母亲,风雨无阻。村里有人说,在他们祭拜的时候,偶尔会看到一个穿红裙的女子身影,远远地站在树丛旁,望着他们,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
异史氏曰:“鬼,常被世人视为凶戾之物,然此女鬼,为保腹中胎儿,不惜现身求人,其母爱之深切,不输世间任何一位母亲。魏承祖医者仁心,不惧鬼魅,仗义援手接生鬼胎,其善举之伟大,可昭日月。苏明兄妹,虽身世坎坷,却能相互扶持,铭记母恩,终得善果。所谓阴阳殊途,情意相通,女鬼之托孤,承祖之相助,明苏之孝悌,皆源于一个‘情’字。世人畏鬼,多因未知与偏见,若能见其情、明其义,又有何惧?噫,万物有灵,唯情不灭,此之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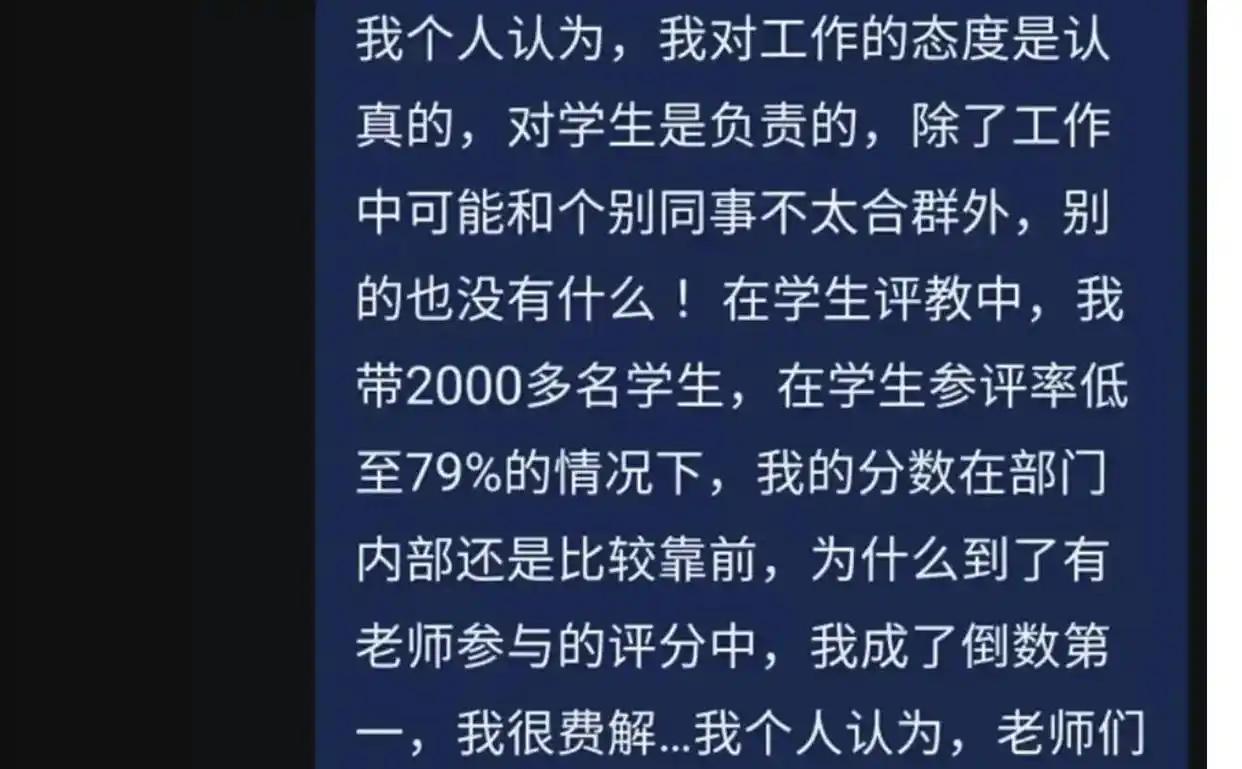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