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象大使罗子健(倮倮)
【2017年1~3月《星星》• 封三( 上旬刊 )】
两个世界(组诗)
• 倮倮
两个弗里达
谁能在伤口里种花?
唯有你——
因你体内住着两个弗里达
软弱的与坚强的,被钢钉
铆进同一副破碎的骨架
酗酒的欲望,与在画布上
沉思哭泣的灵魂,彼此撕扯
如同一只被敲开的石榴
那么多颗心,拥挤在同一具身体里
你漂亮的裙摆
与一边高一边低的高跟鞋
在掩饰什么?
那一字眉,像一座桥
又在渡着什么?
把床抬进作品展览厅,如同
将奥里萨巴火山移入玻璃匣
你在燃烧,所有画作都在燃烧
将人间的无病呻吟,燃为灰烬
生命不是空洞的仪式
你,便是你最好的作品
伟大的灵魂雌雄同体
苦难的灵魂也是
于是,痛苦是双倍的
欢乐,也是双倍的
一个声音高喊:
“我宁可不要欢乐!
也不要痛苦!”
另一个声音,从画布的裂缝挤出:
“我要欢乐! 如果必经痛苦——
那就让潮水,涌来吧!”
弗里达,亲爱的弗里达
世上从无真正的感同身受
他们赞美你裙摆的烈焰
却听不见钢钉在骨缝间的悲鸣
我在你黑色的深渊里行走
随时提醒自己要记得走出去的路
你的身体是一个熔炉
历经2000℃的背叛
飞出了一群不死的蜂鸟
谁能在伤口里种花?
除了你,弗里达
还有我们——
所有在自身的裂隙里
固执地制造光芒的人
2025.10.3,墨西哥城至北京途中
沙滩上的名字
在科巴卡巴纳沙滩上
一笔一画写下你的名字。
只一会儿,它就被海浪抹平。
那会儿,我在想你!
阳光在你的名字上闪了一下
像我突然亲吻了你。

特鲁希略的黄昏
傍晚。暮色从矮矮的屋顶,从窄窄
的街道上空,从教堂的尖顶上,慢慢降下来——
我站在plaza旅馆的门前抽烟。对面
一幢黄色的房子在暮色中宁静、悲悯
它的二楼废弃已久。
突然,一张脸
从一个破烂的窗口冒出
抽搐着……嘴里发出怪异的叫声。
明天清晨,我将离开这座小城
它留给我的最后印象竟如此
偶然,强烈!
我喜欢这偶然
它有着迷人的真实。
他原谅了世界对他的冒犯
今夜,他是另一个人
喝酒,不写诗。
不能抵抗寒冷,也不能
抵抗黑暗和劣质生活的入侵。
酒后,坐在山脚下的草地上发呆,
弯曲的天空下,命运俯下身来,
安静的群山不动声色地铺展——
他成为群山的一部分。
在隐秘的洗礼中,
他原谅了世界对他的冒犯。

倮倮(前排左一)与洛夫(前排中)
身体剧场
邀请桃树、梨树和柿子树,
邀请知了、蜻蜓和松鼠,
邀请花神、水神、树神和土地神,
邀请血管里的火焰与灰尘,
邀请我和经常与我打架的自己,
邀请十里范围内路过的灵魂,
邀请此时此刻的空间,
进入一个神奇的剧场:我的身体。
闭上眼睛:呼吸与大地的呼吸同频,
生命的密语,青草般汹涌——
身体里的奇迹已经余额不足,
一件蒙尘的乐器怯懦出场,
弹奏大地和天空之歌,没有比
不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更要命的。
雕刻
雕刻一个夜晚不比雕刻一个灵魂容易多少。
天使有时穿着魔鬼的外衣,而魔鬼
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天使。
语言的意外与生活的意外比邻而居,
一只灰喜鹊也可能是一颗子弹,它飞过
我的午寐时,我身后的百荷图蛙声一片。
我偶尔会假装成其中一朵,偷窥它们
与天空和白云的倒影嬉戏。一个人
如果不再好奇,生命里的奇迹之火就会熄灭。
人生的魔盒里藏着火焰,打开却是灰烬,
灰烬里还藏着火焰。一个人要翻开
多少灯光下的黑暗,才能看见光明的自己?
——雕刻一个夜晚像雕刻一粒灰烬。

倮倮 与 梁小斌
金黄的老虎
一只金黄的老虎抖落身上的树叶,
从墙壁上的画框里跳出来,
在我的梦里金黄地飞行。
它比博尔赫斯的孟加拉虎更加雄壮,
没有铁栅栏的束缚,它显得更加自由。
黑夜绸缎般燃烧,火焰像一条飞龙
在风中长出无数翅膀,从春天飞到秋天,
可金黄的、无羁的田野始终拒绝现身——
直到我的目光,被甲板的锈迹咬伤。
我立于这艘巨轮的骸骨之上,冷眼看见:
那飞翔的、疲惫的虎,与我自己,
正被一个巨大而无形的栅栏共同囚禁。
码头边,是那根黝黑而磨损的缆绳。
它缄默,钩住过多少声未发出的咆哮,
凝视着一艘艘轮船的远航与沉没。
它们将愤怒熔铸,浇入铁钩般的时间。
铁水嘶吼,融入海水——
海水,复归于一片亘古的湛蓝。
——本作品原发表于《滇池》贰月 Feb.2025
跑步家
跑步家从黑暗中
出发,跑向更深的黑暗
脚步越来越轻
跑成一束光
他喜欢光芒涌现的样子
跑步家
因焦虑而奔跑
左脚才从中年迈出
右脚已暮年
他要使劲跑
才能从暮年中跑出来——

替万物言说它们自己的秘密
我阴差阳错地成为诗人,这冥冥之中决定我的诗歌之路是不同的道路。
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一个忙碌的人,出差、学习、开会、研究产品和消费者习惯、旅行……循环往复……可以说是毫无诗意,但也并非不可以找到诗意,套用罗丹的句式:生活中不是缺少诗,而是缺少发现诗的眼睛。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作用于我,诗成为我对世界的一种反应,或者说是一种反射,一种作用力的反作用。
诗,是诗与诗人的互相发现。
我一直在物质挤压心灵的生存现场,而且,我既是受益者,又是受害者,我处于一种微妙的尴尬中。诗歌成为我精神救赎的工具,我想象自己在词语中获救。
我的绝大部分诗都完成于旅途,汽车上、飞机上、酒桌上、宾馆里……甚至有的诗在KTV里写就。因此,我的诗是现场的、是真实的,是有温度有烟火气的。
我热爱诗歌就像我热爱生命,我渴望看到的生命形态是热气蒸腾的,是与众不同的:有粗粝,有温情,有单纯,有复杂……我希望有一天它能够精确而通透,匠心和佛心同在。以朴素的笔触重新发现现实生活是我希望达到的境界。
我喜爱的诗歌一定要有那种能真正打动人的东西,有对事物新的发现和理解,对心灵的触摸以及穿透。
在我心里,真正的诗歌是要有精神的,真正的诗人要有非同凡响的认知力。我觉得,技巧决定一个诗人的下限,对世界的认知则决定了一个诗人的上限。
潘天寿说:“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
写诗写到最终,也是写境界。
一个好诗人应该让高处的光照到低处,或者从尘埃中挣扎着站起来去仰望高处的光。
一个好诗人必须具有精确进入事物的内部的能力,这里,我想强调一下精确——只有精确,才能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原——这样的“看见”才是诚实的、可靠的、有效的、凶狠的,这样才可能让自己处于语言与生命相互打开的状态,跳脱的文字与胸中奇气浑然一体,真我真气充沛,无所畏惧!
他冒犯尘世,也被尘世冒犯。
但他宽厚、悲悯,原谅一切。
我从来对所谓的灵感写作都表示怀疑,所谓的灵感丢失不过是灵魂枯竭的托词。
写诗是诗人的一门手艺,这手艺一旦形成便不会丢失——手艺只会荒废,不会丢失。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诗人可以用诗歌给万物命名。
然而,这几年,我常常怀疑“诗人用诗歌给万物命名”。
诗人与世界与万物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的行走之诗就比蜗居之诗写得开阔和深邃?2017年,我在齐白石纪念馆看到“得江山助”这句话,似有所悟。这句世人评论唐代文宗张说的话给我莫大启发,我常行走于山峰河流沙漠海洋,访谈奇人异士,与有趣的灵魂一起在天空中舞蹈,这种滋养对我来说胜过读万卷书。
一个心中有大江大河大灵魂亦有大趣的人配得上一切好的东西。
我很庆幸,我至今还保有一颗童心,所以我对这个世界始终充满好奇心。
在这里,我应该要感谢诗歌,是诗歌让我保持童心,并且由好奇心诞生出创造力。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世界始终保持好奇心是诗歌给我最大最好的回馈。
但是,诗人并不能给万物命名。
世上万物,即使它们没有名字,无名也是无名山、无名水、无名花、无名草,诗人无非是从一个秘密通道进入事物内部,品咂、体味它们的秘密,替万事万物说出它们自己的秘密。
我们往往以为诗为诗人代言,事实上诗人是诗的代言人,是万物的代言人。
谢有顺先生曾跟我说:“倮倮,就要敢于裸出身体,裸出思想。”我想这就是我追求的无拘无束的写作。我的诗,既是诗,又不是诗,它是一种媒介,连接我和世界,和万物。
在我的人生经验中,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地警惕“路径依赖”,我害怕自己不断重复自己,就写诗而言,我特别害怕自己写出一些很像诗却没有任何发现任何创造任何价值的诗。与友人聊天,他说,如果语言不能向超越语言的东西奉献自己,还是沉默为好。我以酒杯敲击桌面,大叫三声:好!好!好!
“与其更好,不如不同”是我做事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同样适应于我写诗,我想写出不一样的诗歌,我把与自己说话的诗上升为与自己对话的诗,我有意让我与自我对峙,产生一种强度。
我希望有一天能写出一种让自己也感到惊讶的诗,虽然目前实验并不成功,但我不会放弃。在以后的写作中,我不但要“裸出身体,裸出思想”,还要裸出灵魂。

简介:
倮倮,本名罗子健,7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博鳌国际诗歌节副主席,香港诗歌节基金会理事,凹地成员,新归来诗人代表诗人。作品散见《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创世纪》《国际诗坛》等国内外刊物,入选年选、年鉴等上百种选集,作品被翻译成英、韩、日、俄、西班牙等多国文字,曾获《诗神》探索诗特别奖,《九头鸟》爱情诗大奖赛一等奖,首届香山文学奖一等奖,2019博鳌国际诗歌奖年度诗人奖,首届创世纪诗歌奖,第二届诗经奖,第四届十佳当代诗人奖。
足下有路 诗行万里
微信号:qrsgwl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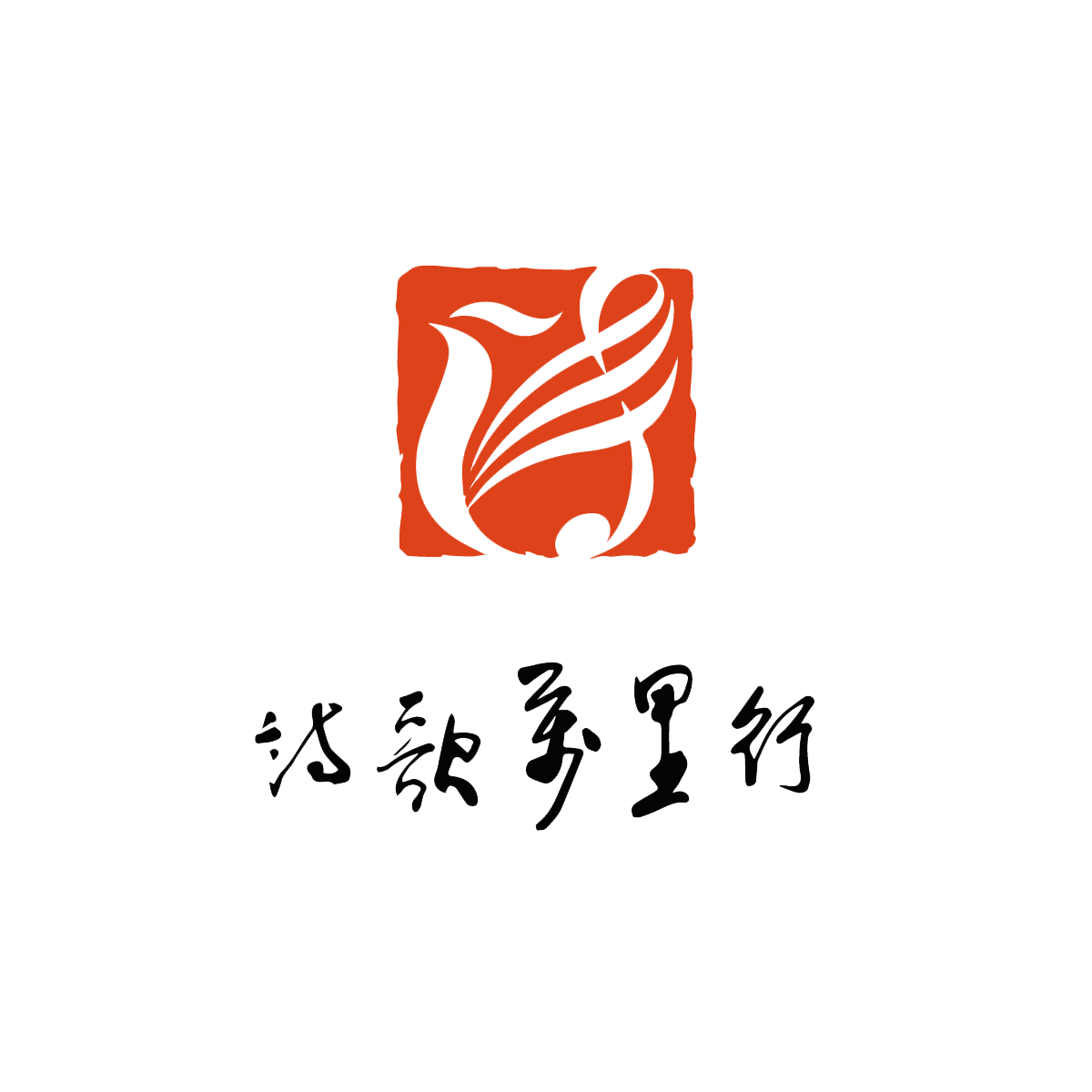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