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9年冬天,一列列闷罐车从河南、安徽、四川驶出,车厢里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农民。
他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只听说新疆有饭吃。这批人后来有个特殊的名字——自流人员。

不同于兵团战士、支边知青,他们游离在体制之外,却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用双手在戈壁荒滩上刨出了活路。
1959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晚。
河南、安徽、四川的农村,饿殍遍地。公社食堂早就断了炊,树皮草根都被刨光了。活不下去的人开始往外跑,有人听说东北有粮,有人说新疆缺人。
消息是这么传的:新疆地大,荒地多,只要肯干活就有饭吃。

于是人们动了。扶老携幼,拖家带口,能走的都走了。没有组织,没有动员,完全是求生的本能。火车站、汽车站挤满了人,站台上到处是行李包袱,哭声一片。
这就是"自流"——自己流出来的。
新疆方面其实早有准备。1959年到1961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但新疆情况相对好一些。粮食虽然紧张,还不至于饿死人。问题在于,外来人口突然暴增。
数字是惊人的。1960年1月到1961年3月,22万自流人员涌入新疆。其中仅1960年前10个月,就来了15.3万人。加上国家安置的支边青年、复转军人,新疆人口从1957年的561万,三年间暴增到730万,增长33%。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三个新疆人里,就有一个是新来的。
吐鲁番成了中转站。当时南北疆各地州都派人在这里设点,负责接收分流。自流人员下了火车,被带到临时安置点,听各地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北疆气候冷,一年只能种一季;南疆温暖,可以种两季。就这么简单的信息,决定了无数家庭的命运。
有的人选了北疆,理由是"那里汉人多,说话方便"。有的人去了南疆,图的是"气候暖和,庄稼长得快"。还有兄弟几个,分别去了南疆北疆,从此相隔千里。
当时没人想过,这一去可能就是一辈子。

同样是进疆,命运却天差地别。
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国家从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等地,有组织地招收知识青年、支边青壮年。这些人有编制,有配给,属于国营农场职工。
兵团的待遇是明确的:每月有工资,有口粮指标,生老病死有保障。虽然条件艰苦,但起码饿不死。1960年初,兵团按计划安置了近10万支边人员。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指示,又接收了21万"自动支边人员"。
但自流人员不在这个体系里。

他们没有工资,没有编制,甚至连户口都悬着。到了新疆,被分配到各个县、各个乡,或者直接划一片荒地:你们自己开垦吧。
这就是体制内外的分野。
兵团战士住地窝子,自流人员也住地窝子;兵团战士啃窝头,自流人员也啃窝头。表面上看生活水平差不多,但本质不同——一个是国家职工,一个是自谋生路。
兰新铁路1960年前后通车,更是打开了进疆的大门。以前去新疆,要么坐汽车在戈壁滩上颠簸半个月,要么徒步走上一两个月。铁路一通,几天就到了。

但铁路只通到乌鲁木齐、吐鲁番。再往南疆去,还得坐汽车。
去和田的那批人最惨。从吐鲁番坐敞篷大卡车,在土路上颠簸十几二十天。车轮卷起的沙尘,把人埋得灰头土脸。左边是荒漠,右边是荒山,看不到尽头。很多人坐在车厢里,闭着眼睛,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到了地方,县里的干部把人分到各个公社、各个生产队。有的单独划出一片荒地,让他们自己开垦;有的直接插到维族村子里,跟着当地人一起干活。
刚开始的日子,几乎是绝望的。
没有房子,就挖地窝子;没有水,就到几里外去挑;没有农具,就用手刨。最难熬的是吃。口粮不够,只能吃玉米面做的窝头,有时连窝头都没有,就煮玉米粒。很多人水土不服,拉肚子拉到脱水。

但活下来的人,慢慢站稳了脚跟。
1958年到1960年,新疆掀起了垦荒造田的高潮。
兵团的任务是开发南疆塔里木河流域和北疆玛纳斯河流域。三年时间,开荒56.67万公顷,新建农牧团场107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血汗。
自流人员虽然不在兵团编制内,但干的活并不少。
和田地区的开荒,维族农民和汉族自流人员一起上。1964年的影像资料显示,于田县红旗公社的社员们,正在挖掘沙丘,开辟农田。1958年以来,和田专区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开垦了70多万亩荒地,建立了30多个社办农场。

这些数字里,有自流人员的一份功劳。
他们的优势在于会种地。内地来的农民,祖祖辈辈种田,对庄稼有感情。新疆的土地虽然贫瘠,但只要有水,就能种出东西来。
问题是水从哪里来?
修渠,挖井,修水库。六十年代初,和田地区修建了总长5000多公里的干支渠。皮山县红光公社新建的渠道,从山里引水下来,灌溉了上万亩农田。
自流人员跟着维族村民学修渠,维族村民跟着汉族农民学种菜。一来二去,关系就近了。
汉族人会精耕细作,种菜种瓜有一套。

维族人看到汉族种的黄瓜、西红柿长得好,也开始学。汉族人不会说维语,就比划着教;维族人不懂汉话,就看着学。
语言反而不是最大的障碍,能不能吃饱饭才是关键。
几年下来,汉族自流人员学会了说维语,虽然带着浓重的河南腔、四川腔。维族村民也学会了种菜,田地里开始有了规整的菜畦。
更重要的是,汉族人开始吃馕,维族人开始吃面条。
这种融合是自然发生的。没人强迫,也没人宣传,就是生活在一起,慢慢就习惯了。汉族妇女跟着维族大嫂学做抓饭、拌面,维族小伙跟着汉族师傅学种棉花、打井。

南疆的很多地方,开始能看出"经济强弱"了——哪里汉族人多,哪里的田地就整齐,蔬菜瓜果就丰富。这不是民族优越性,而是农业技术的差异。
到了60年代中期,自流人员基本站稳了脚跟。
他们在荒地上建起了房子,娶妻生子,成了真正的新疆人。很多人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维语,甚至能跟维族老乡开玩笑。孩子们在村里的小学上学,放学后满院子乱跑,分不清是汉族还是维族。
但他们始终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新疆。政策开始松动,被下放的知识分子、干部可以返回原籍。很多在新疆待了十几二十年的人,终于等到了回家的机会。

自流人员也动摇了。
老家的亲戚来信说,现在好了,包产到户了,有地种了。有人心动,想回去看看。但更多的人犹豫了——回去干什么?地还在吗?房子还在吗?
1981年开始,新疆人口迁移增长率首次变成负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孔雀东南飞"——人才、劳动力开始往内地跑。
自流人员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回去了。
他们收拾行李,告别了二十年生活的村子,坐上火车往东走。但很快,有人又回来了。
原因很简单——已经不适应了。

在新疆待了二十年,生活习惯全变了。回到老家,发现自己说话带着西北口音,吃饭离不开馕和羊肉,甚至下意识地会蹦出几句维语。村里人看他们的眼神怪怪的,像是看外乡人。
更重要的是,没有地了。
当年逃荒走的时候,地早就分给别人了。现在回去,凭什么要回来?就算要回来,二十年没种,早就荒了。
于是,很多人又回到了新疆。
这次回来,心态不一样了。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外来户",迟早要回老家的。现在明白了,新疆才是家。
但也有人一直守在新疆,从没想过回去。

他们在荒地上建起了家园,儿女都在这里出生长大。老家对他们来说,已经只是记忆里的一个地名。过年过节的时候,偶尔会想起小时候的村子,想起那条河、那棵树。但仅此而已。
新疆就是他们的故乡了。
80年代、90年代,这批人渐渐老去。有的病死了,有的老死了,被埋在汉族墓园里。墓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还有"河南籍"、"安徽籍"、"四川籍"的字样。
但他们的儿女,早就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了。
这些第二代、第三代,不会再说什么"老家在河南"、"祖籍在四川"。他们在新疆长大,在新疆上学,在新疆工作,对内地没有任何记忆。如果有人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新疆人"。

但父辈的经历,他们还是知道的。
知道爷爷是从河南逃荒来的,知道奶奶当年坐了半个月汽车才到和田。知道父亲小时候住地窝子,吃玉米窝头。知道一家人是怎么在荒地上,一锹一锹地刨出几十亩田地。
这些故事,像一种隐秘的家族记忆,传递下来。
当年的自流人员大多已经不在了。
他们留下的,是南疆、北疆那些曾经的荒地,如今变成的良田。是那些汉族、维族混居的村庄,早市上卖馕的大妈和卖菜的大爷。是那些墓园里斑驳的墓碑,刻着"籍贯:河南"、"籍贯:四川"的字样。

历史不该忘记他们。
他们不是英雄,没有立过功,没有上过报纸。他们只是一群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了活命而逃荒的人。但正是这群人,用最原始的方式——挖地、种田、修渠、打井——在戈壁荒滩上,刨出了一片生机。
他们是体制外的建设者,是被遗忘的拓荒者。
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缺乏足够的记录和研究。没有详细的档案,没有系统的口述史,甚至连准确的人数都说不清楚。我们只知道,1960年前后,有几十万人自流进疆;我们只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再也没有离开。
但具体是谁,从哪里来,到了哪里,过得怎么样——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这是一段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历史,一段鲜为人知的边疆移民史。它不属于兵团的辉煌叙事,也不属于知青的集体记忆。它属于那些在历史夹缝中求生的普通人,属于那些用双手改变命运的无名者。
历史欠他们一个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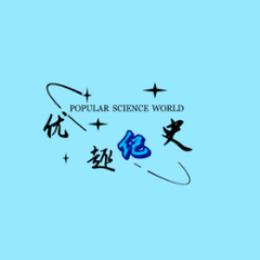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