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们!在下张大少。
前文回顾
萨法维王朝的起源可追溯至14世纪的阿塞拜疆,该王朝于16世纪初在波斯崛起并掌权,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8世纪早期。从萨法维王朝及后世视觉艺术与建筑的角度来看,重要城市包括大不里士、阿尔达比勒、卡尚、克尔曼、设拉子和伊斯法罕。在萨法维王朝最著名的统治者阿巴斯沙阿统治期间,伊斯法罕被选定为新首都和政府所在地,并在此规划兴建新城(建于旧城旁),其核心建筑是沙阿广场(即皇家区域)。从艺术风格上看,萨法维视觉艺术深受土库曼文化及中国、奥斯曼帝国和西欧艺术源流的影响。
视觉艺术领域最显著的成就在于细密画、手稿彩饰、纺织制造以及地毯与陶瓷生产——所有这些对国际贸易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一种新的萨法维绘画风格得以形成。该时期最重要的彩饰手稿之一是史诗《列王纪》。大量高品质地毯及其他纺织品被生产出来,包括雕版印花棉布、各类丝绸织品、运用金银金属纱线的锦缎,以及刺绣与天鹅绒制品。建筑领域也取得丰硕成果,大量清真寺、陵墓及宫殿建筑群在此期间兴建。
建筑
在伊斯法罕,重要的相关建筑项目包括盖萨里耶大巴扎、谢赫·卢特夫拉清真寺、国王清真寺以及阿拉维迪汗桥。清真寺建筑中使用的瓷砖装饰尤为创新,穆卡纳斯(钟乳石状三维瓷砖结构,常用于天花板或壁龛)的运用也极具特色。正如希伦布兰德所述:“穆卡纳斯或称蜂窝状拱顶在伊斯兰建筑中具有多种功能:它既能勾勒曲线空间,又能消解平面感,连接对比鲜明的空间,并为相关的独立图案创造框架”(1999: 230)。
手稿
在萨法维王朝统治下,波斯细密画(尤其与书籍制作相关)成为推动整体视觉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力。皇家作坊影响力深远,其大量作品被广泛摹制传播,在设拉子等地方艺术中心尤为盛行。各类书籍得以抄写、彩饰并装订成册,包括《古兰经》及其他宗教典籍,以及《列王纪》等波斯文学经典,还有诸多与苏菲主义相关的科学论著。13世纪,中国发明的纸张传入波斯。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阿巴斯沙阿统治时期,绘画艺术持续繁荣,但创作重心已从完整手稿转向单幅画作。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形式的视觉艺术(如书法与绘画)遵循着相似的构图法则。手稿彩饰与挂毯织造并行发展,二者在构图模板上也呈现出高度一致性。
地毯
数个世纪以来,波斯一直以地毯(或挂毯)制作的重要产地而闻名。在萨法维时期及之后,地毯生产发展成为重要的民族产业。正如希伦布兰德所言,萨法维时期首次为地毯制作提供了"具有关键意义的实物证据",使得1500年至1700年间的可靠历史与年代序列得以确立(1999: 246)。地毯采用多种纤维原料织造,包括丝绸、羊毛、棉以及金银金属线。工艺涵盖平织(齐卢斯毯与基里姆毯)以及粗绒与精细绒面编织品。希伦布兰德曾提及一件编织紧密的作品,其密度达到每平方英寸800个结(1999: 246)。无论设计类型如何,红色、黄色、蓝色和白色始终是主导色彩。许多装饰主题与纹样也出现在其他视觉艺术中,包括瓷砖装饰、金属工艺和手稿彩饰(1999: 246)。希伦布兰德评论道:"众多萨法维地毯鲜明的绘画性特征,显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萨法维书籍绘画的影响——这种借鉴甚至延伸到空间表现理念,例如高远地平线、阶梯式平面构图以及繁密精细的细节处理"(1999: 249)。中国纹饰在萨法维地毯中的运用尤为普遍,包括云纹、凤凰、龙纹、牡丹与莲花等意象。
其设计可划分为多种类别:狩猎场景、花园景致、动物纹饰地毯、团花与花瓶图案地毯、花卉地毯以及礼拜毯。重要产地包括大不里士、加兹温、卡尚、伊斯法罕和克尔曼。斯通指出:"卡尚被认为是精美丝绸狩猎地毯的产地,伊斯法罕则可能是波兰式地毯的发源地。大型团花地毯多产自大不里士,而花瓶图案地毯则常归源于克尔曼"(1997: 194)。地毯装饰与书籍装帧及彩饰艺术一脉相承。16世纪的地毯以团花式为主导,其典型特征为中央饰以大型多叶形团花纹,四角配以四分之一团花纹样。现存博物馆最著名的团花地毯当属阿尔达比勒地毯(一件藏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另一件为大幅残片藏于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这些地毯制作于16世纪三四十年代。
17世纪初,花瓶图案地毯开始流行(以中央花瓶造型缀以花枝为特征)。至17世纪末期,花园式地毯(模仿规整园林布局分割为矩形区块)已颇为常见。描绘狩猎场景的地毯也广泛流行。波斯各地的地毯编织村镇皆有其独特专长:例如卡尚出产相对小幅的全丝质地毯,常以红或蓝底色为背景,呈现取材自中国神话的动物搏斗场景。
其他纺织品
萨法维王朝之前,波斯的纺织业已相当成熟,能够熟练生产各类织物,包括"印花棉布、剪绒丝绸、金银线双面锦缎以及刺绣品"(希伦布兰德 1999: 250)。希伦布兰德进一步评论道:"建筑、绘画与地毯足以代表萨法维王朝在视觉艺术领域的主要成就,但这也是其他多种艺术形式蓬勃发展的时期。"
该时期的波斯丝绸纺织品以其精妙细腻的质地尤为著称。17世纪国家对丝绸贸易的控制日益加强,特别是在里海各省——这些地区是全国丝纤维的主要产地。复合织造结构(采用金银条带及包覆金属纱线)与丝绸天鹅绒(兼具连续绒面区域与通过平织与绒面相邻形成的留空效果)已十分普遍。色彩搭配极具创新性,出现了诸如开心果绿、鲑鱼粉、茜草红、乳白与赭石等组合色调。伊斯法罕、卡尚与克尔曼的官方纺织工坊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
陶瓷研究
波斯陶瓷的研究与断代工作常面临诸多困难,因为鲜有器物标注年代,产地信息亦十分罕见。虽已确定多处窑址位置,但考证结果往往缺乏确定性。萨法维时期的陶匠发展出多种受中国启发的青花瓷新类型。其装饰纹样极其丰富,与地毯制作情况相似,许多纹样源自中国元素,包括云带纹、仙鹤、凤凰、龙纹、莲花与牡丹等。当了解到阿巴斯沙阿曾邀请三百名中国陶匠及其家族迁居伊朗(希伦布兰德 1999: 250),这种现象便不足为奇了。
纹饰方面,伊斯兰元素包括伊斯兰黄道十二宫图与蔓藤花纹,奥斯曼世界则贡献了忍冬纹(土耳其常用纹样)。17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市场准入受限,萨法维陶瓷的需求量增长。这促使中国纹饰得到更广泛运用,甚至偶尔出现仿冒中国窑口标识的现象(以此伪装中国制品),皆因欧洲市场对东方风格陶瓷的旺盛需求。事实上,克尔曼出产的某些花瓶足以媲美中国瓷器(希伦布兰德 1999: 250)。虹彩陶器曾大量生产,但据希伦布兰德描述,波斯虹彩陶呈现"黄铜色光泽",且纹样大多局限于植物主题(1999: 250-1)。
一张萨法维时期礼拜毯设计稿
在利兹大学国际纺织品档案馆(ULITA)一批未经整理的纺织品残片中,发现了一个未标注信息的包裹,内藏一幅丝绸礼拜毯的设计稿,并附有一封1900年7月28日那不勒斯英国领事馆西德尼·J·A·丘吉尔手写信件的抄本。信件原文转录如下。
那不勒斯英国领事馆
1900年7月28日
尊敬的先生:
我已收到您7月23日的来信。由于当时须匆忙离开巴勒莫以临时接管此处事务,未能及时致信详告包裹内容——其中已附入一幅丝绸礼拜毯的完整工艺设计稿。该设计现已制作完成。图中丝绸部分将向织毯女工准确展示所需使用的色调与染料。
在巴勒莫收拾行装准备搬家时,我在众多物品中发现了它。这幅设计稿颇具价值,将其赠予阁下,正表明我十分乐意为推动英格兰的纺织教育尽绵薄之力。
我在波斯某处应当还藏有一块华丽的古地毯残片。我会设法寻得它。
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尼收藏有一张波斯丝绸地毯,虽多处修补,但我认为正因如此其教育价值更高——相较于完整品,它保留了更为丰富的纹样设计。我曾希望能说服爱丁堡****分会购入此物,但R·M·史密斯爵士的去世打乱了我的计划。
您诚挚的
西德尼·J·A·丘吉尔
设计稿绘制于布纹衬底的方格纸上,采用细笔勾勒并施以水基颜料着色(见图9.1-9.6)。图纸多处粘贴有染色丝绸样本。图案包含部分米哈拉布(祈祷壁龛)造型,以曲线勾勒出蔓藤花纹与花卉纹样(莲花、牡丹、菊花和玉兰)。

图9.1 丝绸祈祷毯设计稿

图9.2 丝绸祈祷毯设计稿细部

图9.3 丝绸祈祷毯设计稿细部

图9.4 丝绸祈祷毯设计稿细部

图9.5 丝绸祈祷毯设计稿细部

图9.6 丝绸祈祷毯设计稿细部
20世纪末期,利兹大学论文研究生N·L·柯比在笔者指导下,咨询了多位专家(来自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及伦敦佳士得拍卖行),以期整体了解波斯地毯制作工艺,并探究这幅设计稿在丘吉尔信中所提丝绸祈祷毯生产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本案例研究简要探讨了信件内容,概述了典型祈祷毯的特征,对不同专家提出的可能产地(被分别认定为克尔曼、伊斯法罕或卡尚)进行了评述,并重点关注了设计稿所呈现的图案风格特征。文中提供了西德尼·J·A·丘吉尔、R·M·史密斯爵士以及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尼的简要生平信息。适当时引用了N·L·柯比未发表的学位论文(1992年)作为参考依据。
礼拜毯、祈祷毯或拜垫是一种纺织品(通常为编织制品,表面或有绒头),穆斯林将其作为便携的洁净区域,用于一日五次朝向麦加礼拜。礼拜毯尺寸或有差异,但需足够覆盖信徒跪拜区域——一端供跪姿使用,另一端在祈祷俯身时承托前额。便携式礼拜毯的典型尺寸约为长一米、宽四分之三米。其图案设计必然包含米哈拉布(拱形祈祷壁龛,常见于清真寺内部,通常以瓷砖装饰,用于指示麦加方向)的象征表现。多数情况下,礼拜毯上米哈拉布形制内的空间不设满铺纹样,但本案例中的设计稿似乎并未遵循此惯例。
设计稿绘制于方形网格纸上(纸张以亚麻布或光面棉布为衬底)。网格被划分为10×10方格的区块(每格平均13毫米×13毫米),这些区块又以四倍组合方式构成更大的20×20方格单元(26毫米×26毫米)。多数权威学者认为,设计元素具有典型的萨法维时期地毯特征,尽管该稿本很可能创作于后世。其设计风格确与萨法维陶瓷装饰艺术相契合。据推测,设计稿中呈现的单角装饰纹样会在地毯四角重复出现,而所示的边饰部分将沿矩形毯面周界延续。此外,中央的半米哈拉布造型应会沿中轴线镜像对称,形成完整的预设壁龛形态。若按设计稿1:1比例制作地毯,每个最小网格代表一个结,则成品地毯的经纬向结密度将达每厘米略超7结(此计算未计入固定绳结的间隔纬线)。若考虑加固纬线的存在,实际密度约为每厘米经向3结、纬向7结,即每平方厘米约21结。
尽管信件声称该设计稿是一幅完整的丝绸祈祷毯工艺图,但自1900年包裹抵达利兹后,很可能已有部分内容遗失。在祈祷壁龛(米哈拉布)区域内明显存在一处空缺,推测原应绘有清真寺吊灯或花瓶图案。根据设计稿附带的文件资料,可推定该图案确为单一竖式米哈拉布祈祷毯设计(此为最常见形制)。另一种可能是通过镜面对称形成的双米哈拉布造型(将完整米哈拉布沿其下部水平轴镜像反射),从而构成大型椭圆形中心区域——但这将导致地毯长度远超现有预期。此外,该设计稿是否曾属于更大规模图稿的一部分尚不可知。或许出售此物的匠人持有更完整的版本(可用于编织更多地毯)。丘吉尔虽声称设计已制作完成,但其是否亲眼见过成品仍属未知。
曲线与蔓藤纹的设计特征使多位专家推断,该设计可能产自克尔曼、伊斯法罕或卡尚——这些均为重要的地毯编织中心。学者们一致认为此设计诞生于固定的工坊环境,而非游牧式地毯编织的产物。关于设计稿的创作年代存在分歧:一位专家推测为16或17世纪,另一位则认为属于19世纪中叶。但学界共识在于其波斯属性及对萨法维装饰风格的明显传承。设计中的棕叶纹与各类花卉纹样皆可辨识,均属萨法维装饰典型元素,而该风格本身又受到明代瓷器的深刻影响。拱肩区域(米哈拉布与上边框之间的三角区)强烈的结构性蔓藤纹造型,暗示着建筑装饰的影响可能源自瓷砖或类似的墙面装饰形式。
设计稿中角落处使用的蓝色底色,很可能不仅计划用于所有边角区域,也拟作为整体边饰的统一背景色。然而,米哈拉布区域内部是否也计划采用相同底色尚不可知。
总结而言,可注意到:预期成品的丝绸质地所对应的高品质,暗示该地毯可能产自伊斯法罕。它很可能是为某位显赫人物定制。编织工艺或采用立式织机,所用丝绸很可能为进口(尽管此点尚不确定)。曲线纹饰的设计特征证实,最终成品应出自成熟的工坊体系(很可能与贵族阶层存在关联),而非游牧或乡村匠人之手。
西德尼·J·A·丘吉尔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曾为大英博物馆收集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及希伯来语手稿,并为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采购地毯。罗伯特·M·史密斯是职业军人(官至少将)兼考古学家,1888年因在波斯的贡献获封爵位(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爵士)。他后来担任爱丁堡科学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斯特凡诺·巴尔迪尼是画家、文物修复师兼古董收藏家。笔者未能核实信中提及的其他物品:"华丽古地毯残片"与"多处修补的波斯丝绸地毯"。
阿尔达比勒地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伦敦)所藏的阿尔达比勒地毯原为一对地毯中的一件,另一件现藏于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伦敦藏品保存最为完整,因洛杉矶藏品部分区域曾被拆解用于修复伦敦这件地毯。伦敦藏毯尺寸为10.5米×5.3米,以丝绸为经纬底布,羊毛绒头结编织而成。织物采用三种蓝色调、三种红色调以及黄、绿、黑、白色。该地毯完成于十六世纪中叶萨法维王朝塔赫玛斯普一世统治时期。有学者认为这件作品最初陈设于阿尔达比勒的一座大型圣殿,但此说尚未确证。其产地可能为大不里士或卡尚(图9.7)。

图9.7 阿尔达比勒地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该地毯曾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伦敦)垂直悬挂于墙面展示数十年。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博物馆改为将其平铺陈列于特制的玻璃展馆内,并置于伊斯兰艺术展厅中央区域。展区照明被严格控制在最低限度(仅在开馆时段每小时短暂调亮数分钟),以确保为地毯创造最适宜的保存环境。
该地毯饰有四重边饰,每层边饰在纹样内容与结构设计上均不相同。最外层边饰以蔓藤花纹为基础,饰有盘绕的花苞与卷须纹。梅森(2002: 215)指出该层存在垂直于边饰边缘的镜像对称轴。第二层边饰为四重边饰中最宽者,其纹样与地毯中心区域的图案存在相似之处。两种尺寸各异的团花纹样(内含各类花卉元素)沿地毯周界重复排列。梅森(2002: 216)在此层发现了双向反射对称结构(平行与垂直于边饰方向同时存在)。第三层边饰由植物花苞与卷须的重复纹样构成,梅森在此检测出多种对称形式,包括单向反射对称、双折旋转对称及纹样的滑移反射对称(2002: 216)。第四层边饰描绘了带有枝叶与卷须的花苞图案,梅森(2002: 217)在此层发现了滑移反射对称轴。被多重边饰环绕的地毯中心区域构成了观赏者(及历史上的使用者)的主要视觉焦点。盘曲的花苞与卷须纹是中心区域的整体特征,但最突出的主体是一个大型中央团花,其两侧饰有两盏悬挂的清真寺灯造型。中央团花带有16片均匀分布的放射状花瓣,呈现八重反射对称结构,根据对称分类体系可归为d8型纹样。中央团花同时延伸出四组置于中心区域的角隅纹样,每组角隅纹样均由四分之一中央团花及其对应花瓣构成。
韦尔登指出,中心区域的设计具有分层结构:一层由带有花朵与叶片的粗茎纹样构成,其上叠加着另一层仅带花朵的细茎纹样。她进一步评论道,地毯整体呈现沿垂直轴的反射对称特征(1995: 61)。
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中央团花两侧悬挂灯饰的尺寸差异:当地毯横向观赏时,可明显看出其中一盏灯较小——盏显得细长,另一盏则较为短胖。然而当地毯纵向观看时,这种差异并不明显。众所周知,远处物体看起来比近处等大物体更小。因此灯饰的尺寸差异可能是设计师有意为之,旨在确保当地毯纵向观赏时两盏灯呈现相同大小。
设拉子瓷砖建筑立面
设拉子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数百年来始终被誉为文化中心。在赞德王朝时期(1749-1779年),它被指定为波斯都城,城中许多历史建筑即建于该时期。本案例研究聚焦于一组建筑立面的照片,由马尔詹·瓦齐里安在21世纪最初十年研究设拉子古城区域时拍摄。笔者于2012年获悉,照片中所记录的建筑或已进行彻底翻修(原有瓷砖立面被移除),或已被完全拆除(见图9.8至9.11)。

图9.8 设拉子建筑立面照片及重绘的构件设计图(MV)

图9.9 设拉子建筑立面照片及重绘构件设计图(MV)

图9.10 设拉子建筑立面照片及重绘构件设计图(MV)

图9.11 设拉子建筑立面照片及重绘构件设计图(MV)
照片中呈现的瓷砖立面,很可能由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参与清真寺建造或修复项目的建筑师或其他设计师规划。这些瓷砖设计在某些方面与城中清真寺的装饰并无本质差异,其工艺手法、使用材料、色彩搭配乃至单块瓷砖尺寸都显得相近。
本案例研究选取了少量建筑立面照片中的瓷砖图案进行结构分析,并将其以图形形式再现。基于视觉分析,研究进一步尝试创作出一组新的瓷砖设计图案(图9.12-9.15)。

图9.12 基于设拉子建筑立面的原创设计开发(MV)

图9.13 基于设拉子建筑立面的原创设计开发(MV)

图9.14 基于设拉子建筑立面的原创设计开发(MV)

图9.15 基于设拉子建筑立面的原创设计开发(MV)
Bennett, I. (1972). Book of Oriental Carpets and Rugs , London: Hamlyn.
Bennett, I. (1978). Rugs and Carpets of the World ,
London: Quarto Publishing. Hillenbrand, R. (1999). Islamic Art and Architecture ,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Wearden, J. (1995). ‘The Surprising Geometry of the Ardabil Carpet’, Ars Textrina , 24: 61–6.
最后照例放些跟张大少有关的图书链接。
青山 不改,绿水长流,在下告退。
转发随意,转载请联系张大少本尊,联系方式请见公众号底部菜单栏。
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宇宙文明带路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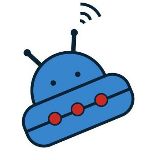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