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老少爷们儿们!在下张大少。
前文回顾
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横跨欧亚贸易网络商品的最终西行目的地是东罗马帝国,其首都位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进入第二个千年后,该城在与垄断地中海地区大部分贸易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竞争中逐渐落于下风。14世纪中叶,黑死病重创该城人口;15世纪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此城,将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并定为不断扩张的帝国的正式首都。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伊兹尼克和布尔萨曾先后作为帝国都城。这两座城市在视觉艺术领域均具有重要地位:伊兹尼克以陶瓷生产闻名,布尔萨则以丝绸产业著称。
奥斯曼人为君士坦丁堡带来了新的繁荣,推行了大规模的建筑修缮计划,并大力拓展贸易。凭借该城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对众多海港的控制,奥斯曼人主导了地中海盆地的大片区域,占据了绝佳的地理位置,得以从亚洲、中东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中获益。最终,奥斯曼人的统治范围从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大部分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延伸至北非沿海地区、叙利亚、阿拉伯和伊拉克。
视觉艺术在贸易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管控的作坊生产地毯与其他纺织品、书法与细密画作品、瓷砖及金属制品。波斯风格传统对装饰艺术整体产生了深远影响,建筑领域(特别是清真寺建筑)则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其设计大量借鉴了古希腊罗马建筑遗产(尤以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为典型)。
圣索菲亚大教堂始建于公元6世纪30年代,由查士丁尼大帝下令建造。这座建筑结构极为复杂,采用穹顶、半穹顶与拱顶相结合的体系。标志性的大穹顶堪称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成就,室内装饰以大理石与石材镶嵌为主。城市被征服后,这座教堂被改建为清真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为阿亚索菲亚清真寺。该建筑一直作为奥斯曼帝国首都的大清真寺,直至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时期被世俗化改造为博物馆。
希尔伦布兰德评述道:"奥斯曼建筑在伊斯兰世界中独树一帜,其始终不渝地恪守单一核心理念——即穹顶方形(立方体)单元……这如同贯穿奥斯曼建筑躯体的脊梁"(1999:257)。因此,主要的建筑特征表现为立方体结构上覆穹顶的形态。其他重要元素包括穹顶扶壁、半穹顶、门廊、穹顶回廊、庭院、宣礼塔和喷泉。纵观奥斯曼时期,数以百计的公共建筑被设计建造,涵盖神学院、医院、浴室及清真寺等各类设施。
米马尔·锡南——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建筑师、皇家建筑师团首席,曾先后效命于苏丹塞利姆一世、苏莱曼、塞利姆二世及穆拉德三世——在16世纪设计了众多清真寺及其他建筑。执政近半个世纪的苏莱曼常被尊称为"大帝",其统治时期被普遍视为文化、艺术与商业活动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他不仅在伊斯坦布尔及土耳其其他地区推行了大规模建筑修缮计划,更着力维护与改进土耳其境外的历史遗迹,包括对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多处遗址进行了扩建工程。
米马尔·锡南——当时最负盛名的建筑师、皇家建筑师团首席,曾先后效命于苏丹塞利姆一世、苏莱曼、塞利姆二世及穆拉德三世——在16世纪设计了众多清真寺及其他建筑。执政近半个世纪的苏莱曼常被尊称为"大帝",其统治时期被普遍视为文化、艺术与商业活动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他不仅在伊斯坦布尔及土耳其其他地区推行了大规模建筑修缮计划,更着力维护与改进土耳其境外的历史遗迹,包括对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多处遗址进行扩建。
著名的建筑及建筑群包括苏莱曼尼耶清真寺(伊斯坦布尔)与塞利米耶清真寺(埃迪尔内),这两座建筑均被视为米马尔·锡南的伟大建筑成就。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伊斯坦布尔)始建于17世纪20年代,因内部瓷砖的主色调为蓝色而广为人知(主要在游客中)称作蓝色清真寺。其外观设计,特别是高耸的中央穹顶,以及建筑的规模、比例与优雅气质,均深受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启发。六座宣礼塔是其标志性特征。
托普卡帕宫自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作为奥斯曼苏丹的皇宫及行政中心,由数十座用于居住、教育和行政的建筑物构成,共同形成一座依花园景观布局、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金角湾(君士坦丁堡半岛)的微型皇家城郭。
大巴扎自15世纪起便持续运营,商贾们在此延续着自古以来的贸易传统。数百年来,这里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金银器皿、陶瓷制品、珍贵珠宝玉石、地毯及其他名贵纺织品、玻璃器皿等各类用途器物,以及香料、草药和各式食材。
书法、细密画与书籍装帧
在书籍绘画或装饰领域,大量宗教题材作品应运而生。然而奥斯曼时期的大多数装饰手抄本侧重于世俗用途,描绘攻城战役或展现整个王朝的编年史。正如希尔伦布兰德所观察:"多位奥斯曼苏丹皆是藏书家,精英阶层成员建立私人图书馆蔚然成风,对知识的尊崇通过装帧精美的奢华手抄本得以彰显。奥斯曼学者虽缺乏独创性,却在诸多领域笔耕不辍"(1999:176)。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土耳其书籍装帧以留白艺术为特征,装饰性圆章或椭圆徽章精准置于封面中央,四隅配以角隅纹样,常施于彩色皮革之上。希尔伦布兰德评述道:"这种本能上令人愉悦的装饰布局或许源于数学计算——其比例关系可能与伊斯兰建筑及书籍绘画中常见的比例法则如出一辙"(1999:276)。
地毯
地毯术语中"carpet"与"rug"常可互换使用(本书亦然)。若需区分,则用"carpet"指代较大型制品,而"rug"指代较小制品(如最大尺寸不超过125厘米×75厘米),这种尺寸的织品恰好能纵向铺设在21世纪英式城镇普通客厅的小型壁炉前。地毯可分栽绒编织与平纹编织两类,两者皆通过编织工艺形成装饰纹样。栽绒指在编织过程中通过添加绕经线打结的绒头形成的立体表面;平纹编织制品则通过多种技法(包括挂毯式织法和锦缎织法)制作而成,成品表面无绒头结构。
最早的奥斯曼地毯可追溯至15世纪初,其风格深受中国纹样影响。土耳其地毯的编织工艺(无论是栽绒编织还是平纹编织的基里姆、苏马克、吉吉姆、齐利等品种)是安纳托利亚以东中亚及突厥/土库曼民族的古老技艺。提及地毯织造区域,必然涉及突厥斯坦——这片边界模糊的地域自里海向东延伸约三千余英里,横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直至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Bennett 1972: 34)。19世纪末至20世纪期间,坚持游牧生活的土库曼部落族群为抗拒定居政策,陆续迁往波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Bennett 1972: 34),显然是为了维系其传统生活方式。
在现代语境中,"土耳其地毯"这一术语不仅涵盖土耳其境内生产的制品,亦泛指安纳托利亚以东突厥民族编织的地毯。然而本书所述土耳其地毯,并非指向先前提及的广袤地域,而是特指今土耳其共和国疆域及其毗邻边境地区。其用意在于强调奥斯曼帝国时期地毯制造业的重要地位,并对若干典型地毯的构图特征作简要阐释。
土耳其地毯与波斯地毯相似,皆从日常实用的朴素部落手工艺品,演变为工艺精湛、备受追捧的奢侈品。最初主要由游牧民族作为便携式家居用品生产,后逐渐融入定居城市环境,被推广为出口商品,并在国家扶持下进行规模化生产,由高级官员监管品质。奥斯曼时期,国家管控的作坊大量生产宫廷御用及外销地毯。与此同时,安纳托利亚各地的游牧族群及乡镇聚落,则持续制作着品质、精细度与工艺稳定性参差不齐的地毯制品。
诸多教科书在介绍早期奥斯曼地毯时,都会提及一件约172厘米×90厘米的珍品:其纵向饰边与两条横向饰边构成装饰框架,剩余区域横向划分为两个近似正方形,每个方格内均描绘着高度风格化的龙凤相争图案,主体以靛蓝绘制,朱红勾勒轮廓,衬以明黄底色。这件21世纪初藏于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地毯,其纹样主题、色彩搭配及构图细节皆为重要物证,充分彰显中国艺术对早期奥斯曼织造工艺的深刻影响。
乡村与游牧地毯通常沿袭祖传(或传统)纹样与构图体系。多数情况下,其采用的纹样已演变为变异形态,原始寓意早已被遗忘,主要凭借记忆或参照前人成品进行复刻,并遵循父辈或祖辈传承的范式准则。
国家管控工坊生产的地毯与乡村地毯形成鲜明对比。这类作坊确保产品的统一性,而这正是出口市场的核心需求。数百年间,国际市场始终认为此类工坊制品比乡村地毯更为精致:它们多采用曲线构图元素,并在严格的质量管控标准下生产——例如整件织品的每英寸打结密度保持恒定,纹样尺寸精准,布局严格遵循设计构图,色彩与原材料类型分毫不差。国家管控产品必定依据等比例蓝图进行编织:这种绘制在方格纸(裱于布面基底)上的设计图,仅呈现整体图案的四分之一,每个方格对应一个织结,附着的染色纱线样本则精确标明各区域的用色规范。
奥斯曼时期,祈祷毯的生产尤为重要,主要与乡村编织相关,尤其是吉尔迪斯、拉迪克和贝尔加马等城镇及其周边地区。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吉尔迪斯,其名被用于指代该地区村庄编织的一种著名祈祷毯类型。可辨识出两种不同的亚型。第一种通常被描述为具有马蹄形拱门,配以素红色米哈拉布(祈祷壁龛),其上悬挂着清真寺灯的图案。在某些实例中,米哈拉布形状的两侧设有柱子(无明显建筑功能)(Bennett 1972: 197)。第二种祈祷毯亚型被一些知名学者认为完全不属于土耳其地毯设计的主流(参见 Bennett 1972: 199),其典型特征为直边、部分矩形形状,带有肩部和V形拱(如同儿童绘制的房屋侧视图),使用深蓝、红、浅黄褐、奶油色或白色,四周环绕着精美的花卉边框,每个边框的宽度都超过米哈拉布本身(Bennett 1972: 199)。Bennett(1999)和Schurman(1982)对这些及许多其他地毯类型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拉迪克祈祷毯常绘有三重拱形米哈拉布(祈祷壁龛)。贝尔加马祈祷毯则多为双头米哈拉布设计,内含两种纹样之一:或是茎蔓曲折的花卉阿拉伯藤蔓纹样,两端饰有风格化的清真寺灯;或是大型中央圆章。无论何种设计,双头米哈拉布本身通常呈浅黄褐色、红色或奶油色,主边框饰有方形与矩形星形图案——前者内含八角星纹,后者则呈现"与米哈拉布纹样呼应的开放式圆章、阿拉伯藤蔓及花卉纹样"(Bennett 1972: 205)。
当然,存在无数变体,本章前述的图案和构图特征绝非所提及地区所独有。正如 Bennett 所指出的,要进行确定且准确的产地归属判定,需要大量积累的经验,以及对纹样、构图规则、纱线类型、染料、色彩搭配和编织工艺的深入了解。众多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由定居于安纳托利亚各城镇的工匠在国家管控的作坊中,以及由各个游牧群体生产的、具有显著差异的地毯系列,均可被识别区分。诸如 Bennett(1972 和 1978)的著作提供了进一步的分类,以及大量图例和关于识别与产地归属判定的提示。
其他纺织品(包括刺绣)
16、17世纪的奥斯曼纺织品大量存世,尤以服饰形式为多。至21世纪初,全球各国国家博物馆均珍藏颇丰。托普卡帕宫的藏品尤为令人瞩目——希尔伦布兰德记载其收藏逾2500件,其中卡夫坦长袍即达千件(1999:277)。该宫还藏有大量刺绣品,许多采用宫廷专业团队制作的金属线材。另有部分刺绣出自居家女性之手,或受宫廷委托而作。
奥斯曼帝国早期,布尔萨尚为都城之时,纺织业活动(包括原材料进口、生产规模及定价)均受政府严格管控。由于坚信优质产品方能保障出口繁荣,当局尤其注重维系高标准的质量管控。纺织与制衣从业者按行会组织,其薪酬由当时政府官僚机构统一核定(Hillenbrand 1999: 278)。
陶瓷
16世纪初,伊兹尼克的工坊已声名鹊起,奥斯曼政府开始监管生产,推动纹样种类扩展、整体品质提升及产量增加。尽管色系相对有限,但持续改良——尤以16世纪60至70年代引入鲜亮的番茄红色为著(Hillenbrand 1999: 270)。流行纹样包括玫瑰、康乃馨、郁金香、风信子、舟船及各类禽鸟,偶见《古兰经》铭文成为主体装饰。关于伊兹尼克陶器特性的进一步阐释,见本章后续第24节。
奥斯曼时期的纹样与符号
奥斯曼时期土耳其视觉艺术中使用的纹样与图案极为丰富,涵盖多种几何形态(如圆形、方形、三角形及六边形)、自然元素(日月星辰、蛇、鱼、花卉、水纹)、人造器物(杯盏、花瓶、各类武器)以及神话意象(龙、美人鱼及其他传说生物)。以下章节将重点探讨核心纹样——其中许多并非盛行于宫廷,而是常见于乡村刺绣等民间工艺之中。
诸多纹样的象征意义往往因文化而异,且可能随时代流转而嬗变(Munro 1970: 51-2)。以圆形为例,既可诠释为"法轮"(佛教术语),亦可象征四季轮回,或单纯作为日轮意象。符号的叠加常衍生出复合意蕴——如中国传统刺绣中常见此类表现手法(Hann, Thomson and Zhong 1990: 4)。女神形象及其关联符号的呈现尤为普遍,根据地域或文化的差异,常与丰饶、生命、死亡或宇宙创生等概念相系。同理,丰饶意象在一文化或区域中以女神形象呈现,在另一文化中则可能化作生命之树(Paine 1990: 65-6)。
环地中海地区(包括今土耳其大部),大地女神形象常作为纹饰出现在各类手工艺品表面。该形象形态多变,例如呈现半树半鸟的复合形态(Paine 1990: 66)。其应用可追溯至地中海区域及欧洲大部分地区,例如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山谷的库尔干墓葬中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毛毡织物上便有此纹样(Paine 1990: 66, 67)。亚洲广大地区的刺绣及其他民间手工艺中,女神形象的衍生纹样亦十分常见。
在某些情况下,具象纹样源自基督教圣经故事或版画印刷品,而非古代神话(Paine 1990: 67)。在伊斯兰教成为主流宗教的地区,具象纹样并不常见;即便存在,也因高度风格化而难以辨认。例如原始形态为半女半蛇的沙赫梅兰,即使在奥斯曼时期,也常以高度风格化的形式出现在土耳其民间刺绣中(Senturk 1993: 151)。
水、鱼和船是常见的纹样,尤其在亚洲众多海洋民族的视觉艺术中频繁出现。水通常象征着生命的神秘,具有与生命之源相关的孕育力量。鱼纹在土耳其、突尼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视觉艺术中十分普遍,有时被解读为灵魂的象征、精神的探寻者或生命的守护者(Paine 1990: 119-20)。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双鱼纹被认为源于佛教,象征婚姻美满与和谐统一(Zhong 1989: 38)。在土耳其视觉艺术语境中,鱼纹则象征丰产、好运或繁荣(Dural 1979)。在孟加拉地区,鱼纹同样被用作丰产符号。石榴、葡萄和瓜果纹样也是常见的丰产象征,这一寓意在土耳其、叙利亚、巴尔干地区的视觉艺术以及中国清朝的艺术创作中均有体现(Paine 1990: 70)。
在诸多文化背景的视觉艺术领域中,生命之树是普遍存在的经典母题,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与变体。其基本构成通常为对称的植物造型,两侧常伴有正面相对的禽鸟、走兽、神祇或朝拜者形象。这种构图模式自古代延续至今,广泛分布于亚洲各地。学界对该母题有多种解读:或视其为支撑宇宙、贯通天地的世界树,或将其与四季更迭及生命本质相关联。树侧动物形象因地域文化而异,常见的有孔雀、雄鸡,以及龙、狮鹫等源自上古传说的神兽(Paine 1990: 71-3)。
自古以来,日轮或单纯圆形即象征太阳,广泛出现在众多文化的视觉艺术中。在环地中海地区,约公元1世纪的陶器上曾出现五重同心圆(每圆代表一颗行星)图案,其最内圈即为太阳象征(Gombrich 1979: 221)。其他表现形式包括中心带点的圆、外缘放射光线的圆以及内嵌十字的圆。万字纹常被视为太阳符号,并与运动、变化的概念相关,马耳他十字和星形纹样亦然。月亮的描绘亦属常见,因其被认为与女性月经周期存在神秘关联(Paine 1990: 80)。在一些亚洲国家,万字纹、星纹和圆形常与螺旋纹、三角形共同出现在视觉艺术中。土耳其刺绣中常见漩涡(或风车)纹、三角形和星纹;印度和巴基斯坦则使用日轮、星纹和圆形;中国传统刺绣中圆形和万字纹出现频繁。
奥斯曼刺绣中鸟纹频繁出现,常与生命之树、花卉纹样及太阳符号相伴。鹰、孔雀与雄鸡是土耳其及亚洲广大地区最常见的鸟纹主题,既可解读为吉祥象征,亦可视为天国信使(Paine 1990: 79-80)。清朝中国刺绣中,成双成对的禽鸟象征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在土耳其刺绣里,飞鸟则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喜讯或幸福。
花卉与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地的刺绣及其他家居制品中广泛应用。就土耳其而言,康乃馨、玫瑰、郁金香、风信子、石榴、松树及柏树是其典型纹样(Palotay 1953-5: 3662)。此类纹样亦出现于直至20世纪仍受土耳其深厚影响的地区,如匈牙利、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希腊北部群岛及叙利亚北部,尽管各地区的风格化程度不尽相同。
风格化的花朵或花枝,配以弯曲或环绕的枝茎、锯齿状叶片及钩状茎端,是土耳其陶瓷与刺绣的典型特征(Wace 1935: 5)。摩洛哥亦使用相似纹样(Wace 1935: 7, 8)。在印度、巴基斯坦和突厥斯坦,花卉纹样通常被简化为圆形图案。波斯与阿尔及利亚的花叶形态则常以阿拉伯藤蔓为骨架呈现。中国传统花卉纹样常见莲花、牡丹、菊花、梅花及海棠花,果实纹样则多采用石榴与佛手(Zhong 1989: 47)。
由三个圆点构成的纹样(即"金塔玛尼")及云纹带,自16世纪起便常见于土耳其陶瓷、织物与刺绣。此类纹样亦见于中国刺绣,其起源被认为与佛教相关(Paine 1990: 115)。
典型的土耳其纹样(尤见于刺绣)是清真寺与柏树图案,由一系列房舍或清真寺式建筑配以树木花卉纹样构成。这种风景式构图是18至19世纪伊斯坦布尔和布尔萨刺绣的典型特征(Wace 1935: 6)。土耳其南部地区亦可发现相似纹样。由清真寺式建筑纹样与单株柏树纹样交替构成的窄边框图案,是土耳其的特色,但也见于今俄罗斯联邦部分地区的刺绣中(Wace 1935: 5)。石榴或洋蓟纹样在土耳其刺绣与纺织品中常见,偶尔也出现在陶瓷上。据韦斯考证,该纹样可能起源于小亚细亚(1935: 11)。图10.1至10.10展示了奥斯曼时期的一系列纹样设计。

图 10.1 奥斯曼刺绣细节,19世纪(利兹大学国际纺织品档案馆藏)

图 10.2 奥斯曼刺绣细节,19世纪(利兹大学国际纺织品档案馆藏)

图 10.3 奥斯曼刺绣细节,19世纪(利兹大学国际纺织品档案馆藏)

图 10.4 奥斯曼刺绣细节,19世纪(利兹大学国际纺织品档案馆藏)

图 10.5 奥斯曼刺绣细节,19世纪(利兹大学国际纺织品档案馆藏)

图 10.6 奥斯曼刺绣细节,19世纪(利兹大学国际纺织品档案馆藏)

图 10.7 奥斯曼刺绣细节,19世纪(利兹大学国际纺织品档案馆藏)

图 10.8 奥斯曼刺绣细节,19世纪(利兹大学国际纺织品档案馆藏)

图 10.9 奥斯曼刺绣细节,19世纪(利兹大学国际纺织品档案馆藏)

图 10.10 奥斯曼刺绣细节,19世纪(利兹大学国际纺织品档案馆藏)
伊兹尼克陶器
伊兹尼克陶器得名于安纳托利亚的一座城镇,其生产始于15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持续至17世纪末。早期制品多采用无色釉下钴蓝装饰。其典型特征是将奥斯曼阿拉伯式蔓藤纹样与(深受奥斯曼珍视的中国青花瓷启发的)中国纹样相融合。中国瓷器似乎为伊兹尼克陶器的生产提供了最初灵感,尽管奥斯曼工匠未能掌握瓷器制作技艺(图 10.11 – 10.20)。

图10.11 16世纪土耳其伊兹尼克陶瓷(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10.12 16世纪土耳其伊兹尼克陶瓷(大英博物馆藏)

图10.13 16世纪土耳其伊兹尼克陶瓷(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10.14 16世纪土耳其伊兹尼克陶瓷(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10.15 16世纪土耳其伊兹尼克陶瓷(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10.16 16世纪土耳其伊兹尼克陶瓷(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10.17 16世纪土耳其伊兹尼克陶瓷(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10.18 苏莱曼大帝图格拉徽号(Septia Andin 绘,印度尼西亚万隆理工学院藏)

图10.19 16世纪土耳其伊兹尼克陶瓷(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10.20 16世纪土耳其伊兹尼克陶瓷(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16世纪陆续引入其他釉色:最初为松石绿配深钴蓝,继而出现鼠尾草绿与浅紫。16世纪中叶,标志性的矾红取代紫色,鲜翠的祖母绿替代鼠尾草绿。至16世纪末,品质渐趋衰退(器形、釉色及玻化程度不复往日精湛),但生产仍延续至17世纪。
21世纪初,大量伊兹尼克陶器存世品收藏于世界各地博物馆。更多实例(尤以瓷砖形式)可见于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埃迪尔内及阿达纳的清真寺、陵墓、图书馆与宫殿建筑中。需知土耳其陶瓷生产另有重要产地,但判定奥斯曼时期陶瓷的具体生产地并非易事。例如屈塔希亚似曾采用相近的纹样、原料与工艺,伊斯坦布尔的皇家作坊亦具有重要地位。
最负盛名的伊兹尼克纹样类型之一是图格拉式螺旋纹饰,其灵感源自与苏莱曼大帝皇室徽号(图格拉)相关的卷轴状装饰。采用这种效果的陶瓷制品,典型特征是在白地上以钴蓝绘制精微的螺旋状卷草纹,其间点缀纤巧花卉与S形藤蔓。
纹样与图案的对称性分析
本案例研究旨在阐释开展对称性分析项目的基本原理。研究数据源于一项针对多种手工打结地毯对称性特征的考察项目(Mason 2002)。
梅森(2002)从以下权威文献中随机选取500幅土耳其地毯图像进行对称性分析:班尼特(1972)、坎帕纳(1969)、塞西尔-爱德华兹(1983)、艾兰与艾兰(1998)、甘斯-鲁丁(1971)、甘茨霍恩(1998)、哈里斯(1977)、肯德里克与塔特索尔(1922)、米尔霍费尔(1976)、里德(1972)、齐佩尔与弗里切(1989)。通过参照对称性特征,对500幅样本的地毯中央区域纹样进行分析与分类,结果显示非随机分布态势,反射对称性明显占主导地位:其中单向反射对称纹样占样本总量近40%;双向反射对称纹样占近25%;四向反射对称纹样占近17%。祈祷毯几乎总是呈现单向反射对称特征,因其核心的米哈拉布(壁龛)造型即具有此特性(图10.21)。1所选地毯纹样多配有复合边框。500件样本共统计出2270条边框纹样,将其归入不同对称类别后,发现以下偏好:二重旋转对称(近18%)、双向反射对称(近16%)以及无其他对称特征的简单平移重复(近15%)。单向反射对称在样本中占10%。²

图10.21土耳其祈祷毯绘图(CW)
在后继的关联研究中,笔者考察了不同源流地毯纹样与符号的对称特征。其中"古尔"纹样作为核心母题,以多元形态广泛出现在各类地毯中,尤以土库曼地毯为最。历史上被称为突厥斯坦的地区曾深受土耳其文化影响。在土库曼语境中,古尔纹样的变体被用于标识部落隶属关系。该纹样既可单独呈现,更常见的是以重复图案形式织就平行序列。通过对100件地毯样本(选自前述权威文献)中单体古尔纹样的对称性分析,发现65%的纹样呈现单向反射对称(d1类纹样),而60%以古尔为基础的重复图案构成单向反射对称结构(p1m1)(图10.22a-h)。双向反射对称(d2类纹样)作为另一重要特征,约占纹样总量的25%。综上所述,土耳其地毯样本纹样明显以单向反射对称为主导,双向反射对称次之。


图10.22a–h 展现单向或双向反射对称的土耳其/土库曼纹样(CW)
Bauman, J. (1987). Central Asian Carpets. Study Guide , Islamabad: Asian Study Group.
Bennett, I. (1972). Book of Oriental Carpets and Rugs , London: Hamlyn.
Bennett, I. (1978). Rugs and Carpets of the World , London: Quarto Publishing.
Campana, M. (1969). Oriental Carpets, London: Hamlyn.
Gombrich, E. H. (1979). The Sense of Order, London: Phaidon.
Munro, T. (1970). Form and Style in the Arts: An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Morphology, Cleveland, OH: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Press.
最后照例放些跟张大少有关的图书链接。
青山 不改,绿水长流,在下告退。
转发随意,转载请联系张大少本尊,联系方式请见公众号底部菜单栏。
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宇宙文明带路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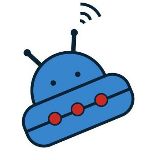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