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的早晨,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
我缩在棉被里,闻着母亲从厨房里飘来的腊肉香,听见父亲在院子里喊我:"起来,今天走你三姑家。"

我不想动。被窝是热的,外头是冷的,三姑家在镇子那头,要走将近四十分钟的土路。我把头埋进被子,含糊地应付:"爸,那么远,不去了吧。"
父亲没有发火。他站在我床边,拍了拍我的脑袋,只说了一句话:"该走的亲戚,再远也得走。"
那年我七岁。我不懂这句话。

我只知道,那天他硬把我从被窝里薅出来,给我套上棉袄,父子俩顶着寒风,踩着结了薄冰的土路,走了四十分钟,去给三姑拜年。三姑把一把花生糖塞进我兜里,眼角都笑弯了,说:"幺儿来了,幺儿来了。"---
后来我慢慢懂得,父亲走亲戚,是认真的。
正月初二走外婆家,初三走大舅,初四走姑妈,初五走表叔……他有一张装在脑子里的地图,哪家今年有喜事,哪家老人身体不好,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每次出门前,他会把带去的东西摆在桌上检查一遍——两斤红糖,一条猪肉,或者几包点心——手掌摩挲过那些东西的时候,神情郑重,像在完成一件重要的事。
我跟着他走了多少年,数不清楚了。走过下雪的腊月,走过桃花开的清明,走过蝉鸣聒噪的暑假,也走过落叶铺地的秋天。
亲戚们见到父亲,都是那种由衷的欢喜。不是客套,是真的高兴。大表伯会把他最好的茶叶拿出来,二舅妈会当场去厨房加菜,连平时话少的堂叔,都会坐下来跟他说很久的话。

我那时候只当是大人的世界,没太放在心上。
真正脱离那个世界,是从我考上大学开始的。
毕业之后留在城里,工作,结婚,买房,生子。日子像陀螺,被什么东西抽着转,停不下来。每年回家的时间越来越短,走亲戚这件事,慢慢变成了一个程序——该打的电话打一个,该发的红包发过去,至于登门,能免则免。

路太远,假期太短,孩子太小,工作太忙。我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
有一年,大表伯生病住院,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然后继续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报表。我当时正在冲一个年终业绩,脑子里全是数字,那个电话像一粒石子扔进水里,涟漪散了,什么都没留下。
大表伯出院之后,我也没去看他。
后来我才知道,那次他在医院住了将近三周,父亲每隔两天就去探一次,来回四十多公里的路,坐公共汽车,换一次车。每次去都带些吃的,坐在病床边陪他说话,说到大表伯睡着了,他才悄悄起身离开。

父亲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提过这件事。是母亲说漏了嘴,我才知道。
那一刻,我坐在沙发上,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羞愧。不是那种戏剧性的、在心口猛烈燃烧的愧疚,而是一种沉的、钝的、慢慢往下坠的感觉,像胃里压了一块石头。
我在追什么呢?那一年的业绩,最终超没超标,我现在连数字都记不清楚了。
真正让我开始改变的,是父亲书桌抽屉里的那个小本子。
他去世前两年,眼睛不太好,但那个本子他一直在记。我整理遗物的时候翻到它,牛皮纸的封面,已经磨得起了毛边。里头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记的是亲戚们的地址、电话,谁家几口人,孩子叫什么名字,老人多大年纪。
有些信息已经过时了。电话号码换了,地址搬了,有几个名字旁边,他用括号标注了"已故"两个字,字迹比旁边的字更用力,像是在郑重地做一个交代。
我翻到最后几页,是他近几年新添的内容。字比以前大了,有些地方写歪了,能看出来手在抖。但每一个名字都还在,一个都没删掉。
我把那个本子捧了很久。
后来我没有舍得把它留在老房子,带回了城里,放在自己书桌的抽屉里。每次走亲戚之前,我会拿出来翻一翻——不是为了查什么,就是翻一翻,看看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看看父亲留下的那些歪歪扭扭的字。
那个本子里,装着他的整个世界。
我走亲戚,已经走了二十九年了。
从跟在父亲身后走,到自己领着儿子走。路换了,从当年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有时候开车,有时候坐高铁,有时候飞机。但那个开头总是一样的——提着东西,登门,敲响那扇门,然后看见里头的人听见敲门声,脸上浮现出的那种由衷的高兴。
上个月去看大表伯,他已经八十一岁了,耳朵有些背,我说话要凑近了说。他拉着我的手,问我儿子读几年级了,问我工作还顺不顺。他记得我小时候的名字,记得我父亲最爱喝的那种茉莉花茶。
临走的时候,他把我送到门口,站在那里,目送我走远。
我回头看了一眼。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还站在那里,没有转身。
我想起父亲,想起那个腊月二十八的早晨,想起他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时说的那句话。
该走的亲戚,再远也得走
我那时以为,这是一句关于距离的话。走了二十九年,我才明白,这是一句关于心的话。
走亲戚走的不是路,走的是记挂;走亲戚走的不是礼,走的是情分。那些我们亲手走出来的路,才是真正把人和人连在一起的线。断了太久,线就凉了;线凉了太久,人就散了。
父亲用一辈子走出来的那张网,我曾经险些亲手剪断它。
还好,还来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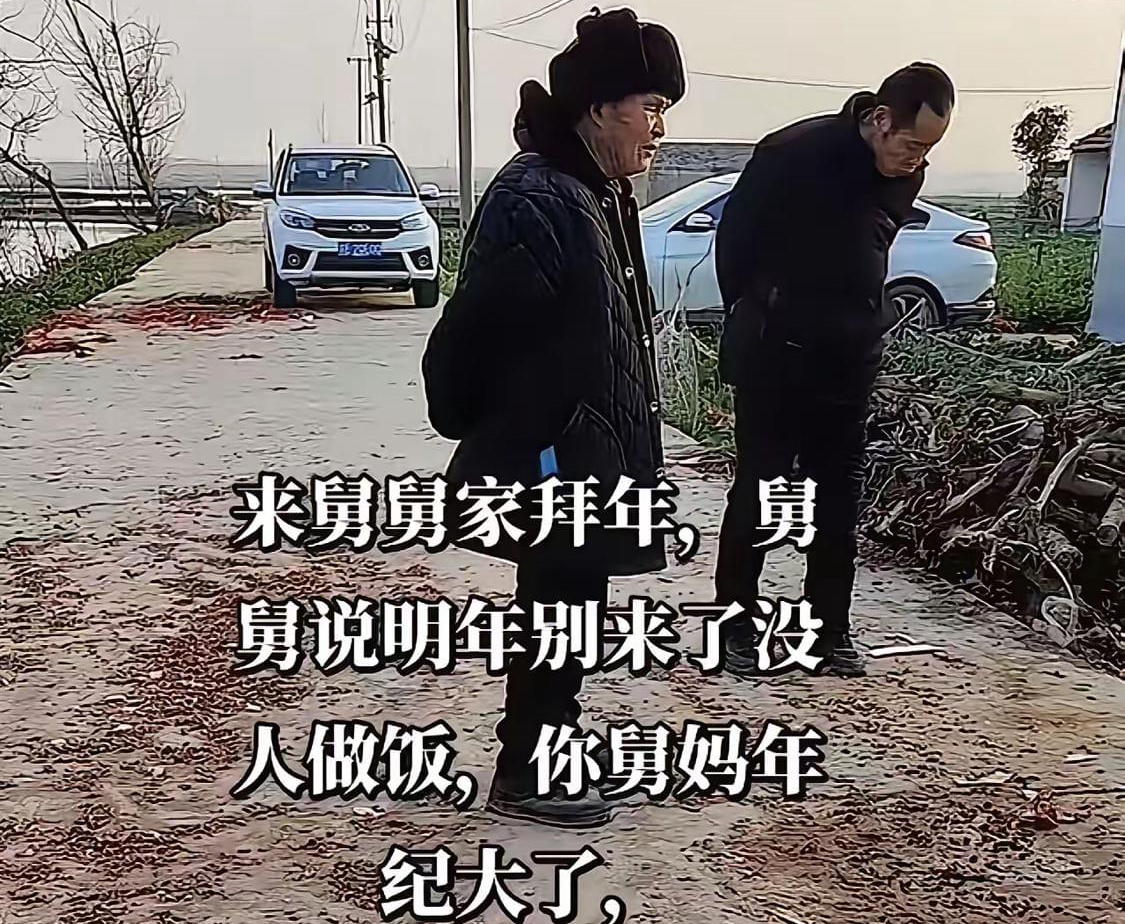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