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12日,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土房里风从门缝灌进来,白求恩靠在枕上,手却还在抖着写字,字很小,最后一封信,没有一句自我陈述,没有功劳簿,只有“把这些东西分给战友”,药箱,手术刀,能用的都给在前面的人,他从加拿大走到这块土地,跨过海洋和山岭,身上背的不是传奇,是一套朴素的判断和做事的方法,这人为什么来,为什么把命压在这里,他心里早有答案,只是一直没说出口。

有一次,工人拖着病体进门,掏不出手术费,病程拖到不可回头,他站在门口听到消息,心口像被戳了一下,回到办公室把窗关上,抬头说了一句重话,“所谓现代医学,如果只属于富人,那只剩外壳”,从那之后,他把自己的门半掩着,给穷人留一条缝,能免就免,能降就降,诊疗之外,他走进工会的屋子,帮人写申请,讲公共卫生的道理,把医疗这件事拉回到公共事务的桌面上。
三十年代风向变冷,电台里传来西班牙内战的消息,他从报纸上看到平民在街角倒下,心里那根弦绷紧,他报名进入援西医疗队,到了前线,帐篷里摆不下需求,他把思路往前推,“移动手术室”的念头落地,手术台往火线边上挪,伤员从担架上放下就能推进,抢回了一条条命,他在广播里说话,“反对法西斯,不是口号,是岗位上的行动”,这段经历让他把医学和正义绑在一起,救人不是单纯的技术动作,还要对准方向。

1938年春天,他抵达延安,见面就把话挑明,“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做客的,把我派到最需要的地方”,很快,他背着箱子去了晋察冀,窑洞做病房,土炕当病床,手术器械凑不够十件,消毒用品见底,麻醉药也紧张,他没有停顿,先把窑洞改出一个角落,搭起台面,又把铁匠叫来,缺器械就自制,煮沸的盐水顶上消毒的空档,场地往前推,手术台挪到离火线很近的位置,“越是艰苦,越能体现医疗工作的价值”,枪声近了,人救得住,队伍对他的信任也跟着稳住。
战事猛的时候,像1938年10月广灵公路伏击战,他连续站了四十个小时,记在本子上的数字是71台手术,手指被刀口划出血,他用纱布一裹,继续,旁边的人劝他坐一会,他看了一眼担架队,“多休息一分钟,就可能有一名战士失去生命”,屋里的人不再说话,只把新的器械递到手边。
救人之外,他把眼光投向更长的线,外来的医生不会永远在这片土地,他开始写教材,把技巧拆成步骤,包扎、止血、切开、缝合一条条拎清,墙上挂示意图,手把手带着学员练,到点就上实战,卫生学校拉起教学的骨架,一批批学员很快顶上岗位,病房里多了熟练的手,救护队里多了可靠的眼睛,有个小护士手抖,输液反复没穿进,他把针拿过来示范一遍,声音压低,“头一次都会紧,练过就好”,哭声停住,人重新站稳。
村里也常见他背着药箱的背影,山路一脚深一脚浅,有人来敲门他就起身走,白天黑夜都一样,有位老人肺气肿卧床,他徒步几十里过去,开方给药,还把饮食起居安排到位,等到人能下地再回去,老乡塞东西,他一概谢绝,衣服打着补丁,吃和战士一样,特殊补给往重伤员那边推,他的原则清楚,自己够用就行。
1939年10月,北岳区遭遇冬季“大扫荡”,原本准备回国筹物资的行程往后放,他把手术台设在涞源县王安镇孙家庄的小庙里,这里离前线很近,也能避开对村民的牵连,伤员一波接一波抬进来,他连轴转了三天三夜,体力被掏空,在一次手术里,划伤的手指接触到了开放伤口,感染很快蔓延到血里,他还是把手头的最后一台做完,才慢慢坐下,周围的人把他抬下去,灯火还亮着。
躺在床上,他还在翻教材,在页边写字,交代救护流程,叮嘱注意事项,“战地救护要做到位,不能让战士们白白牺牲”,1939年11月12日凌晨,他安静地停住了呼吸,年仅49岁,他念叨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工作的念念不忘,“遗憾的是,没能为中国人民做更多的事”,遗书里仍旧写着“遗物分给战友”,这人把一生的方向交代得很明白。

他为什么来,线索都在前面的路上,底层民众的苦难让他走进诊间,反法西斯的判断让他走进前线,对中国抗战正义性的认同让他把名片递到延安,他把中国的战事当成自己的工作,把这片土地上的人当成需要被托付的人群,国际主义精神四个字被他做成了日常作业。
今天再提起他的名字,大家都能说出几件事,更要把背后的方法和标准记住,不是天生的英雄,是一个心怀正义、坚持理想的普通人,做决定时把人命放在第一位,做选择时把纪律和技术并排摆好,跨过国界的是善意,落在岗位上的是真正的责任,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路就不会偏。
他留下的种子早发芽,卫生学校成长为有体系的医学院,战地医疗的理念走出山谷,影响到更宽的领域,救治流程更快,分工更细,装备更适配,回头看,他当年在窑洞里搭的那张台,像是一块模板,后来的人照着加固,照着扩展,我们纪念,不是停在称呼上,是在各自岗位上把这股劲延续下去,心怀正义,专业可靠,温和克制,向着生命,这条路能一直走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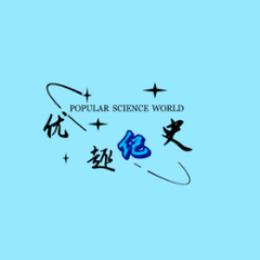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