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城邦的黄昏与花园的避难所
第一章:当城墙倒塌 —— 希腊化时代的精神危机
在深入探讨那些具体的哲学学派之前,不妨让我们先闭上眼睛,穿越回两千三百年前的地中海,去深深地嗅一嗅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混合着旧世界腐烂气息与新世界陌生味道的独特氛围。
公元前三二三年,年轻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那奢华得令人窒息的帐篷中,伴随着高烧的胡话,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以及一个无人能填补的、巨大的权力黑洞。仅仅一年后,公元前三二二年,他的老师、那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优卑亚岛的流亡中孤独地离世。
这两位巨人的相继陨落,就像是一道沉重的铁闸轰然落下,将希腊历史硬生生地切断。辉煌、自信、以城邦为中心的希腊古典时代结束了,动荡、混杂、个人渺小无力的希腊化时代开始了。
罗素敏锐地指出,这绝不仅仅是地图颜色的改变,这是人类心灵史上的一次地质灾变。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黄金岁月里,一个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他的自我认同是清晰、坚固且充满自豪的。他是一个“公民”。他的自由、他的荣誉、他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像常春藤一样紧紧缠绕在“城邦”这棵大树上。城邦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它更是一个伦理共同体,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亚里士多德那句“人是政治动物”,其实是在宣告:“人是属于城邦的动物。”离开了城邦,人就成了断线的风筝,瞬间失去了重量和方向。
然而,随着马其顿方阵的铁蹄踏碎了希腊各城邦的独立梦,旧世界崩塌了。
试想一下,一个生活在公元前三零零年的雅典人,当他早上醒来,他惊恐地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能在一山之隔就听到回声的小国的主人,而是一个庞大、陌生、高度官僚化的帝国的微不足道的“臣民”。
* 政治上的失语:他再也不能在公民大会上通过激昂的演讲来决定战争与和平了。现在的统治者是那些遥远的、虽然说着希腊语但行事像波斯皇帝一样专横的马其顿将军们。个人的声音,在帝国的轰鸣声中,变得连蚊子的嗡嗡声都不如。
* 空间上的迷失:世界突然变得太大了,大得让人感到眩晕。从印度河的丛林到尼罗河的沙漠,不同的种族、奇怪的宗教、陌生的风俗像潮水一样涌入。旧的奥林匹斯神祇似乎只管得住阿提卡半岛那巴掌大的地方,根本管不住这广袤无垠、充满未知的混乱新世界。
* 心理上的孤独:城邦的物理城墙虽然还在,但人们心里的城墙倒塌了。个体第一次被赤裸裸地抛到了一个充满敌意、不可控、也不可知的巨大空间里。
一种前所未有的“形而上学的恐惧”紧紧攫住了希腊人的心。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无力与渺小。他们不再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他们只希望能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中幸存下来。
于是,哲学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根本性的急转弯。
如果说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关注的是“自然”(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政治”(什么是正义的城邦?),那么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们,开始只关心一个最卑微、也最迫切的问题:
“在这个混乱、危险、不可控的世界里,作为一个渺小无助的个人,我该如何安顿我的灵魂?我该如何获得幸福,或者至少,获得一点点免于恐惧的安宁?”
哲学从喧闹的“广场”撤退到了幽暗的“内心”。它不再教你如何治理国家,因为那已经是皇帝的事了;它教你如何治理自己。它从一种探索真理的科学,变成了一种“灵魂的治疗术”。哲学家变成了精神科医生,他们的学说就是开给这个患病时代的处方。
在这个废墟之上,两座新的精神避难所建立了起来:一座是伊壁鸠鲁的花园,另一座是斯多葛的门廊。
第二章:伊壁鸠鲁 —— 被误解的圣徒与他的“花园”
提到“伊壁鸠鲁”这个名字,现代人的脑海里往往会浮现出一幅油腻不堪的画面:一群人躺在罗马式的躺椅上,衣衫不整,吃着山珍海味,饮着美酒,纵情声色。在许多语言中,他的名字甚至直接变成了“美食家”或“老饕”的代名词。
罗素在这一章中,首先做的就是为伊壁鸠鲁平反。他用确凿的史料告诉我们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历史上真实的伊壁鸠鲁,不仅不是一个纵欲者,简直就是一个苦行僧。
伊壁鸠鲁(公元前三四一年至前二七零年)出生于萨摩斯岛,是一个贫穷的雅典殖民者的儿子。他的一生都在与病痛作斗争,身体孱弱,常年忍受着膀胱结石和胃病的剧痛,有时甚至无法行走。但就是这样一个病弱的人,创立了那个时代最温暖、最持久的哲学社群。
公元前三零六年,他在雅典买了一块地产,这就是著名的“花园”。
这不仅仅是一所学校,它更像是一个逃避乱世的乌托邦公社。
在这个花园里,生活着伊壁鸠鲁和他的追随者们。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社团打破了当时所有的社会禁忌——它对所有人开放,包括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和奴隶。在这里,没有主人与奴隶的区别,没有男人与女人的尊卑,只有平等的友谊。
他们在这个花园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绝对不是酒池肉林。
根据记载,伊壁鸠鲁每天的食物只是白水和普通的面包,如果偶尔能加一点奶酪,对他来说就是盛宴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给我寄一点基西拉的奶酪来吧,这样当我想吃顿好的时候,我就有的吃了。”
他甚至在临终前,死于肾结石导致的剧痛时,躺在温水的浴缸里,依然能写信给朋友说:“当我的身体遭受剧烈痛苦、甚至无法排尿时,我依然感到幸福,因为我在回想我们要过的那些愉快的哲学谈话,这些记忆战胜了肉体的折磨。”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清心寡欲、在此岸受苦的人,会被贴上“享乐主义”的标签,并被后世的基督教会视为眼中钉呢?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理论:虽然我们生活简朴,但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快乐。
第三章:快乐的微积分 —— 重新定义“幸福”
伊壁鸠鲁哲学的核心基石确实是“快乐”。他宣称:“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点。”
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语义陷阱。伊壁鸠鲁所定义的“快乐”,与我们常识中的感官刺激(吃喝嫖赌)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像一位精细的心理学家,将快乐分为了两类:
动态的快乐:
这是我们在满足某种匮乏时感到的快乐。比如口渴时喝水,饥饿时吃饭,或者欲望得到满足时的快感。
* 特点:它是剧烈的,但它总是伴随着痛苦(匮乏的痛苦),而且一旦满足,快乐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匮乏或空虚。
* 伊壁鸠鲁认为,追求这种快乐就像是把水倒进一个漏底的桶里,永远无法填满。那些沉迷于酒色的人,其实是在用更强烈的刺激来掩盖内心的空虚,这恰恰是痛苦的表现。
静态的快乐:
这是当身体没有痛苦、灵魂没有纷扰时,我们所处的那种平衡状态。比如吃饱后的满足感,无病无灾的安宁,与朋友交谈时的宁静。
* 特点:它是温和的、持久的、自足的。
* 伊壁鸠鲁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基于此,他给幸福下了一个极简的定义,这个定义是消极的,但在乱世中却是最抚慰人心的:
幸福等于身体无痛苦加上灵魂无纷扰。
这就是伊壁鸠鲁主义的精髓。他不是教你去追求更多的刺激,而是教你如何减少痛苦。
他像一位精明的会计师,教导弟子们在做任何事之前,都要进行“快乐的微积分”:
* “如果我享受了这个快乐(比如酗酒),它会不会在未来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宿醉、伤肝)?”——如果是,那就放弃它。
* “如果我忍受了这个痛苦(比如治病的苦药),它会不会在未来给我带来更大的快乐(健康)?”——如果是,那就接受它。
经过这种计算,伊壁鸠鲁得出了结论:最持久、最纯粹、性价比最高的快乐,来自于简单的生活、节制的欲望,以及与朋友的哲学交谈。
因为面包和水容易得到,不会带来求之不得的焦虑,而友谊和智慧是免费的,且永远不会让人厌倦。

第四章:恐惧的解毒剂 —— 原子论的心理疗法
然而,伊壁鸠鲁发现,阻碍人类获得“灵魂无纷扰”的最大敌人,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更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挥之不去的恐惧。
特别是两种恐惧:对神灵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
只要人还害怕天上的神会因为心情不好而降下雷电,只要人还害怕死后会下地狱受苦,他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宁静。
为了消除这两种恐惧,伊壁鸠鲁做了一件在哲学史上非常独特的事:他借用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并将其改造成了一种“治疗性的形而上学”。他研究物理学,不是为了探索宇宙的奥秘(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而是为了治愈心灵的焦虑。
诸神的退场:神不关心我们
伊壁鸠鲁说,世界是由原子在虚空中碰撞而成的,这是一个机械的过程,不需要神的干预。
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脑海里有完美之神的形象,但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只是那些原子非常精细。
关键在于:神是完美的、幸福的。
既然神是完美的,他就不会有愤怒、嫉妒或偏私。他居住在“世界之间”的缝隙里,享受着永恒的快乐。他绝对不会哪怕有一丁点闲工夫来关心人类的琐事,更不会像暴君一样降下雷电去惩罚人类。
结论:神不关心我们,所以我们不必怕神。 那些关于神惩罚恶人的故事,都是祭司们编造来吓唬小孩的。
死亡的虚无:死与我们无关
针对死亡的恐惧,伊壁鸠鲁给出了那个著名的、充满逻辑力量的论证:
“死与我们无关。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
他的逻辑是:
* 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的,虽然比较精细。
* 人死后,身体的原子散开了,灵魂的原子也飞散了。
* 既然感觉需要原子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那么原子散开后,感觉也就彻底消失了。
* 既然死后没有感觉,也就没有痛苦,没有地狱的折磨,没有冥王的审判。
结论:死亡只是长眠,是无梦的睡眠。 我们在出生之前经历了漫长的虚无,我们并不为此感到恐惧;那么,为什么要害怕死后那段同样的漫长虚无呢?
通过这套物理学,伊壁鸠鲁试图把人类从宗教的恐怖中解放出来。他告诉他的弟子们:宇宙是冷漠的,但这也意味着宇宙是安全的。没有神在盯着你,没有鬼在等着你。你只需要在这个花园里,喝着水,吃着面包,和朋友谈论哲学,享受这有限但真实的生命。
这是一种多么温柔的虚无主义,一种多么令人心碎的清醒。
02
门廊下的战士 —— 斯多葛学派的崛起与神圣的宿命
第五章:走出花园,进入画廊 —— 芝诺与另一种选择
如果说伊壁鸠鲁主义是一剂温柔的镇静剂,教导人们通过降低欲望、躲避人群来获得乱世中的安宁;那么斯多葛主义,就是一针强效的兴奋剂,或者是战士上战场前喝下的那碗烈酒。它要教导人们的,不是如何“躲避”苦难,而是如何“征服”苦难。
斯多葛主义诞生于公元前三零零年左右,几乎与伊壁鸠鲁学派同时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它的创始人是来自塞浦路斯的芝诺。
罗素特别提到了芝诺的身世:他是一个腓尼基人。这意味着他带有闪米特文化的背景。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希腊化时代,纯粹的希腊理性精神开始逐渐枯竭,而来自东方的宗教热情开始像地下水一样渗透进哲学的土壤。斯多葛主义虽然用希腊语写作,用严密的逻辑学辩论,但它的内核里,燃烧着一种近乎希伯来先知的宗教狂热和道德严肃性。
当芝诺来到雅典后,他没有像伊壁鸠鲁那样买一块封闭的地产建立“花园”,以此隔绝尘世的喧嚣。相反,他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选择:他选择了雅典集市北面的一条著名的公共长廊——“彩绘画廊”——作为讲学的地方。在希腊语中,“画廊”发音为“斯多葛”,这个学派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这个地点的选择充满了深刻的象征意义:
* 伊壁鸠鲁的花园是有围墙的,象征着退隐。
* 芝诺的画廊是开放的,正对着熙熙攘攘的集市和庄严的法庭,象征着入世。
斯多葛主义者拒绝逃避世界。他们要在这个混乱、危险、堕落的世界中心,在这个充满了凯撒、将军、暴民和奴隶的修罗场里,锻造出一种坚不可摧的灵魂。
这种哲学不仅成为了希腊化时代的主流,更在后来彻底征服了罗马人的心,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官方精神支柱”。从带着沉重脚镣的奴隶,到统治世界的皇帝,都渴望从这口深井里汲取力量。
第六章: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生物 —— 泛神论与决定论
要理解斯多葛派那硬核的伦理学,我们必须先潜入他们那宏大的物理学(或者说是形而上学)深处。
斯多葛派复活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我们在第2集曾详细探讨过)。他们认为,宇宙不仅仅是一堆冷冰冰的原子在虚空中盲目碰撞(像伊壁鸠鲁所说的那样),宇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是一个巨大的、神圣的生物。
神即宇宙(泛神论)
斯多葛派认为,神不是外在于宇宙的造物主,神就是宇宙本身。
整个宇宙充满了神圣的“火”,或者叫“灵气”(Pneuma)。这股力量像血液一样渗透在万物之中,赋予它们形式和生命。
* 在沉重的石头里,它是“凝聚力”;
* 在生长的植物里,它是“生长力”;
* 在奔跑的动物里,它是“灵魂”;
* 在思考的人身上,它是“理性”,也就是“逻各斯”。
逻各斯:宇宙的剧本
这个神圣的宇宙火,不仅仅是盲目的能量,更是最高的智慧。
斯多葛派坚信,宇宙中发生的一切——星星的运行、季节的更替、帝国的兴衰,甚至你今天早餐吃了什么、你将在何时死去——都是由神圣的逻各斯精心安排好的。
这是一个彻底的决定论宇宙。没有偶然,没有随机,没有伊壁鸠鲁那种原子的“偏斜”。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为了整体的“善”而精心设计的剧本。
罗素的质疑与斯多葛的回答
罗素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逻辑难题:如果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神是全善的,那为什么世界上还有恶?为什么还有吸血的臭虫、毁灭城市的地震和残暴的暴君?
斯多葛派的回答非常具有辩证法色彩:你觉得是恶,是因为你的视角太狭隘,你只看到了局部。
* 对于被狮子吃掉的羚羊来说,这是恶;但对于维持生态平衡这一整体的善来说,这是必要的。
* 臭虫的存在是为了让你不至于睡得太死而变得懒惰。
* 暴君的存在是为了像磨刀石一样,磨练圣贤的品格。
总之,在宇宙的宏大剧本里,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的。如果你觉得不好,那是因为你是个蹩脚的观众,而不是剧本的问题。



第七章:那只被拴住的狗 —— 自由意志的艰难突围
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那么人类还有自由吗?如果我杀人是神安排的,我有罪吗?如果我注定要破产,我还需要努力工作吗?
这是决定论面临的最大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多葛派提出了哲学史上最著名、也最形象的一个比喻:“狗与马车”。
“想象一只狗,被一条皮带拴在一辆正在行进的马车后面。马车在向前走,这是不可改变的命运。
如果狗愿意走,它就是跟着马车跑,它的步伐与马车的方向一致,它是自由的,虽然它是被拴着的。
如果狗不愿意走,它死死地钉在地上,或者试图往反方向跑,结果是什么?它会被马车无情地拖着走,四脚磨出血,遍体鳞伤,最后它还是得去那个终点。”
斯多葛的全部智慧,就在于教会我们:做那只愿意跑的狗。
这就是斯多葛式的自由:自由不意味着改变命运(那是已定的,是神的意志),自由意味着自愿地顺从命运。
正如罗马哲学家塞内卡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这种自由观听起来很悲壮,甚至带有一种宿命的凄凉。但在乱世中,它给人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它意味着,虽然我不能控制外面的世界(马车往哪开),但我可以绝对控制我的态度(是跑还是被拖)。只要我的意志与神的意志(逻各斯)保持一致,我就和宇宙一样强大,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我。
第八章:唯一的善是德性 —— 一套只有黑白没有灰色的伦理学
基于这种宏大而冷峻的宇宙观,斯多葛派建立了一套极其硬核、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伦理学。
他们像外科医生一样,对世界上的事物进行了一次残酷的切割与分类。他们认为,事物只有三类:
善:
只有一样东西是善的,那就是德性,也就是智慧、正义、勇敢、节制。更准确地说,就是“顺应自然、顺应理性而生活的意志”。
恶:
只有一样东西是恶的,那就是恶德,也就是愚蠢、不义、怯懦、放纵。或者说,是“违背自然、违背理性的意志”。
无所谓的中性之物:
除了德性和恶德之外的所有东西。
请注意这份令人窒息的清单:健康、财富、名声、权力、美貌、快乐……甚至生命本身。
还有:疾病、贫穷、耻辱、奴役、丑陋、痛苦……甚至死亡本身。
这是一个惊人的、彻底反直觉的分类。它意味着:
* 如果你生病了、破产了、被流放了、被暴君砍头了,这本身并不是“恶”。因为这些事情并没有损害你的灵魂,没有让你变成一个坏人。它们就像天要下雨一样,是中性的自然事件。
* 如果你发财了、当了皇帝、健康长寿,这本身也不是“善”。因为一个坏人也可以拥有这些。这些只是身外之物,像衣服一样,随时可能被剥夺。
斯多葛的圣贤
基于此,斯多葛派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圣贤。
圣贤是完全自足的。因为他只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一样东西——德性。而德性是完全由他自己控制的(就像那只愿意跑的狗)。
* 即使把他关进暴君的监狱,他也是自由的,因为他的灵魂没有被囚禁。
* 即使把他放进铜牛(一种将人活活烤死的酷刑刑具)里,他依然是幸福的。他会平静地说:“这很痛,但这并不‘恶’。”
罗素在这里忍不住吐槽:这种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完美自洽,但在人性上太冷酷了。如果痛苦不是恶,那么看到别人受苦,我们为什么要同情?斯多葛派会回答: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但这只是出于“自然倾向”,而不是因为觉得他真的很惨。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内心应该保持绝对的冷静,不动感情。
“不动心”
这就是斯多葛修行的终极目标。它不是指麻木不仁,而是指“免于激情的奴役”。
斯多葛派认为,愤怒、恐惧、嫉妒、甚至过度的狂喜,都是“理性的疾病”。它们源于我们对“中性之物”的错误判断。
* 你为什么愤怒?因为你认为“别人侮辱我”是“恶”。但如果你意识到“侮辱”只是空气的震动,只有“我因此而生气”才是恶,你就不会愤怒了。
* 你为什么恐惧?因为你认为“死亡”是“恶”。但如果你意识到死亡只是原子回归自然,是命运的一部分,你就不会恐惧了。
这就是斯多葛的门廊。它不像伊壁鸠鲁的花园那样温暖舒适,它像一座冰冷、坚固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里,一个人可以独自对抗整个帝国的重量,对抗命运最残酷的打击,并宣称:“我的头流血了,但我没有低头。”
03
罗马的凯歌 —— 当奴隶与皇帝共享同一个灵魂
第九章:不仅是哲学,更是宗教 —— 斯多葛主义的罗马化
当希腊的城邦自由在马其顿的方阵下化为齑粉之后,斯多葛主义就像一颗顽强的种子,被历史的风吹向了西方,落入了一片更广阔、更肥沃,但也更冷酷的土壤——罗马。
罗素敏锐地指出,罗马人与希腊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希腊人爱思辨、爱争论、爱美,他们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充满了好奇心;而罗马人则像严肃的成年人,他们务实、坚韧、崇尚纪律和法律,充满了“重力感”。
对于罗马的将军和执政官来说,柏拉图那关于“理念世界”的玄想显得太虚无缥缈,不着边际;伊壁鸠鲁那躲在花园里喝水的建议则显得太软弱、太不负责任。唯有斯多葛主义——那种强调责任、忍耐、视死如归、为了大局而牺牲小我的精神——简直就是为罗马人的灵魂量身定做的。
于是,在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里,斯多葛主义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它不再仅仅是雅典画廊里的一种理论辩论,它变成了罗马精英阶层的非官方宗教。它为那些手握重权、同时也背负重任的罗马人,提供了一套在乱世中安身立命的道德盔甲。
在这个过程中,斯多葛主义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它变得不那么关心物理学和逻辑学了,而是将全部热情都倾注到了伦理学和神学上。它开始强调一种超越国界、超越阶级的人类友爱。
为了展示这种哲学的普世力量,历史仿佛特意安排了一场戏剧性的对照:斯多葛学派在罗马最伟大的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另一位是社会最顶层的皇帝。
第十章:爱比克泰德 —— 跛足的自由人与“控制二分法”
在尼禄皇帝统治时期(公元一世纪),罗马城里生活着一位名叫爱比克泰德的奴隶。他的名字在希腊语里就是“被买来的”意思,这本身就是一种屈辱的烙印。他不仅出身卑微,身体还遭受了严重的残害——据说他的主人在一次发怒中扭断了他的腿,导致他终身跛足。
如果是普通人,面对这样的命运,恐怕早已陷入怨恨或绝望。但爱比克泰德没有。他在斯多葛哲学中找到了灵魂的救赎,并最终获得自由,成为了一代宗师。他的讲录被弟子记录下来,成为了后世无数受苦之人的枕边书。
爱比克泰德哲学的核心,是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他用这把刀将世界一分为二。这就是著名的“控制二分法”。
他教导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类事物:
我们可以控制的:这是我们的内部世界——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好恶。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理性。
我们不能控制的:这是外部世界——我们的身体、财产、父母、名声、官职,以及无论是暴君的命令还是天气的变化。
人类痛苦的根源,就在于越界。我们试图去控制那些并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 当我们想要身体健康,却生病了,我们痛苦;
* 当我们想要别人尊重,却被侮辱了,我们愤怒;
* 当我们想要保全性命,却面临死亡,我们恐惧。
爱比克泰德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口吻告诫我们:“如果你想把不属于你的东西据为己有,你注定会失败、悲伤、焦虑,你会责怪神和人。”
那么,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彻底的撤退与坚守。
我们要像守卫一座城堡一样守卫自己的理性。当主人扭断他的腿时,爱比克泰德可以平静地说:“你扭断的是我的腿,而不是我的意志。腿属于你(因为你是主人),但意志属于我(因为我是理性的存在)。既然腿不属于我,它的断裂又怎么能伤害到我呢?”
这是一种令人战栗的自由。通过放弃对外部世界的一切执念,通过承认“身体也是身外之物”,爱比克泰德在奴隶的锁链中,获得了连皇帝都无法剥夺的绝对自由。
罗素评价道,这种哲学虽然带有“酸葡萄”的心理防御色彩,但它确实让人类尊严在最黑暗的时刻得以保全。它告诉我们:只要我不签字同意,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伤害我的灵魂。
第十一章:马可·奥勒留 —— 宝座上的孤独者与世界的公民
时间快进到公元二世纪,斯多葛主义迎来了它在世俗权力上的巅峰。罗马帝国的皇帝、被称为“五贤帝”最后一位的马可·奥勒留,成为了这种哲学的信徒。
如果说爱比克泰德展示了斯多葛主义如何帮助弱者忍受苦难,那么马可·奥勒留则展示了它如何帮助强者承担责任。
马可·奥勒留的一生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充满享乐。相反,他生活在一个帝国开始摇摇欲坠的时代。瘟疫横行,洪水泛滥,北方的蛮族不断冲击着多瑙河防线。作为皇帝,他必须常年生活在阴冷潮湿的军营里,指挥着一场接一场疲惫不堪的战争。
在那些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在多瑙河畔军营帐篷昏黄的烛光下,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写下了一本原本只给自己看的日记——这就是后来的《沉思录》。
读这本书,你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高贵的忧郁。这不是一本帝王心术的教条,而是一个疲惫灵魂的独白。
* 他告诫自己要像一块岩石,任凭海浪拍打而岿然不动。
* 他提醒自己,那些对他阿谀奉承的大臣,以及那些想要暗杀他的敌人,都将在转瞬间化为尘土,就像他自己一样。
* 他教导自己不要抱怨这繁重的公务,因为这是“宇宙的安排”,是他作为一只蜜蜂、一根手指所必须履行的职责。
马可·奥勒留将斯多葛主义的普世主义推向了高潮。
他写道:“如果理性是我们共有的,那么法律也是共有的。如果法律是共有的,那么我们就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宇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城邦。”
这是一个何其宏伟的概念!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被分为希腊人和蛮族人,主人和奴隶。
但在马可·奥勒留的眼里,从他这个皇帝,到最底层的蛮族奴隶,大家都是宇宙城邦的平等公民。大家的身体虽然有贵贱之分,但大家的灵魂里都分有同一团神圣的“逻各斯之火”。
罗素指出,虽然马可·奥勒留在现实政治中依然要镇压蛮族,甚至迫害过基督徒(这是历史的悲剧误会),但他在思想上确立的这种“人类大同”的观念,成为了后世“自然法”和“天赋人权”思想的直接源头。
第十二章:自然法 —— 斯多葛留给西方的最重要遗产
在这一部分的结尾,我们需要专门探讨一下斯多葛主义最具体、最持久的遗产——自然法。
在智者运动时期,我们看到了“自然”与“习俗/法律”的对立。当时的智者认为,法律只是人为的约定,没有神圣性。
斯多葛学派,特别是到了罗马时期的西塞罗等人,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综合。他们提出:
真正的法律,就是正确的理性,它与自然相吻合,适用于所有人,永恒不变。
这意味着:
法律高于权力:即便是皇帝或元老院制定的法律,如果违背了“自然法”(也就是理性),那么它就是无效的“恶法”。这为后来的宪政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石。
普遍性:自然法不分国界。罗马的法律不能只保护罗马人,还应该保护所有人,因为大家都是“宇宙城邦”的公民。这直接推动了罗马法从狭隘的“市民法”向普世的“万民法”演变。
罗素虽然对斯多葛哲学的形而上学部分(如神意决定论)持批评态度,但他不得不承认,在伦理和法理学层面,斯多葛主义是古代世界所能达到的最高道德水准。它在那个充满暴力和奴役的时代,第一次清晰地喊出了:每个人,无论境遇如何,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尊严。
04
理性的黄昏与信仰的黎明
第十三章:斯多葛的极限 —— 当英雄主义变成一种疲惫
斯多葛主义无疑是古代世界所能达到的道德最高峰。它教导人们在暴政下保持自由,在痛苦中保持尊严。然而,罗素以他那特有的历史心理学视角指出,到了罗马帝国晚期,这种哲学开始显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疲惫感。
为什么?因为斯多葛主义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它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上帝。它告诉那个刚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这并不邪恶”;它告诉那个正在忍受饥饿的穷人:“财富是身外之物”。
这种教导对于像马可·奥勒留这样拥有钢铁意志的精英来说,或许是崇高的;但对于广大受苦受难的普通民众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冷酷的嘲讽。
更重要的是,斯多葛主义是一种“孤独的哲学”。
虽然它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但这种兄弟情谊是建立在抽象的理性之上的,缺乏情感的温度。在斯多葛的城堡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独自守卫着自己的灵魂,拒绝任何激情的入侵,包括爱与同情。
这种“自力更生”的救赎之路,走久了会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人类的灵魂深处,除了渴望尊严,更渴望被爱、被安慰、被拯救。人们开始厌倦了仅仅依靠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对抗命运的暴风雨,他们开始渴望一位救世主。
正是这种心理上的真空,为基督教的进入打开了大门。基督教带来了一个斯多葛主义无法提供的福音:你不必独自承担一切,神爱你,神为你受苦,神会拯救你。
相比于爱比克泰德那句冷硬的“忍受并克制”,耶稣那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于那个动荡时代的人心来说,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第十四章:新柏拉图主义 —— 哲学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在古代世界的余晖中,在基督教全面接管西方心灵之前,希腊哲学还有最后一次辉煌的爆发。这就是由普罗提诺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
罗素对普罗提诺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
普罗提诺生活在公元三世纪的罗马,那是一个帝国濒临崩溃、战乱频仍的时代。他深感现实世界的丑陋与虚幻,于是,他将柏拉图的“理念论”推向了神秘主义的极致。
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流溢说”宇宙模型:
太一:宇宙的最高本原,超越了一切存在和思想,它是绝对的善,绝对的光明。
流溢:就像太阳自动发出光芒,或者喷泉自动溢出水流一样,“太一”因为过度充盈而流溢出了“努斯”(心灵),努斯又流溢出了“灵魂”,灵魂最终流溢出了物质世界。
回归:物质世界是光明的尽头,是黑暗和丑陋的。人类的灵魂是被困在物质中的火花。人生的目的,就是通过哲学沉思和神秘体验,沿着流溢的阶梯逆流而上,最终与“太一”重新合二为一。
普罗提诺羞于提及自己的肉体,甚至拒绝画像,因为他认为肉体只是灵魂暂居的幻影。
罗素指出,这种哲学彻底切断了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它不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对自然感兴趣,也不像斯多葛那样对公民责任感兴趣。它唯一的兴趣就是“逃离”——“从孤独者飞向孤独者”。
这种极致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成为了古代哲学“自杀”的标志。它把理性变成了一种通向神迷狂的梯子,当人爬上去之后,就把梯子踢掉了。它为基督教神学提供了最后的、也是最精致的形而上学框架,然后就此消亡。
终章:罗素的审判 —— 希腊化哲学的“主观主义”病灶
在这一集的最后,罗素对整个希腊化时代(从伊壁鸠鲁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总清算。
他承认这些哲学家在伦理学上达到了极高的高度,为在乱世中受苦的人们提供了心灵的避难所。但是,作为一位科学主义者,罗素敏锐地指出了这个时代思想的致命病灶:主观主义。
切断了与自然的联系
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家们充满好奇地向外看,试图理解宇宙的构造。那是一个“外向”的时代。
但在希腊化时代,随着城邦的毁灭和社会的动荡,哲学家们吓坏了,他们把目光收了回来,转向内心。他们不再问“世界是什么”,只问“我该怎么活”。
伊壁鸠鲁研究原子论,不是为了物理学,而是为了证明“神不干预人事”从而获得安宁;斯多葛研究宇宙论,是为了证明“一切皆有定数”从而获得顺从的理由。
真理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治疗心理焦虑的手段。 罗素认为,这导致了科学精神的全面衰退。
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
在古典时代,人是城邦的一部分。但在希腊化时代,人变成了原子式的个体。
无论是躲在花园里的伊壁鸠鲁,还是守在内心堡垒里的斯多葛,亦或是飞向太一的普罗提诺,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个人的救赎。社会、政治、改良世界,被视为不可能或无意义的事。
这种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使得哲学变成了一种精英阶层的精神游戏,无法阻挡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野蛮的入侵。
为迷信敞开大门
当理性不再用来认识客观世界,而是用来寻求内心的安慰时,它就很容易向迷信投降。到了罗马帝国晚期,占星术、巫术、东方神秘宗教泛滥成灾。理性已经疲惫不堪,它主动交出了权杖,跪倒在信仰的脚下。
古代世界的落幕
随着罗马帝国的夕阳落下,西方文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希腊那种自由、理性、充满好奇心的精神火种,虽然没有完全熄灭,但被深深地埋藏在了修道院的厚墙和神学的教条之下。
人类的心灵,从“探索自然”,转向了“关注社会”,最后在绝望中转向了“仰望上帝”。
这将是一个长达一千年的“信仰时代”。
在下一集《第10集:上帝之城——圣奥古斯丁的时间、记忆与历史》中,我们将跨越数百年的时光,目睹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基督教的崛起。我们将看到一位浪子回头的圣徒——奥古斯丁,如何利用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砖石,在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上帝之城”,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对“时间”、“罪”和“历史意义”的理解。
那将是另一种壮丽,一种属于信仰的壮丽。
(第9集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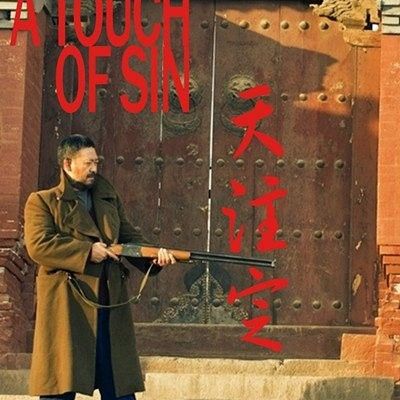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