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8日,库房小窗递进一张淡绿纸,三行字干净到有点冷,仇英《江南春图卷》、徐悲鸿《双马图》、明人山水册页,共五件,拟调剂给江苏省文物总店,申请栏里两个小字,凌波,交完单子又回身补了一笔,铅芯轻轻蹭在备注那一栏,“赝品,可售”,A5纸很薄,风从窗缝钻进去能打个颤,谁也没想到这张纸有一天会被翻回来读,读到每一个顿笔的位置都像在问话。

庞叔令第一次撞见“赝品”的说法,是2025年10月的一条推文,她在手机上放大那张图录,卷尾的“南京博物院藏品”火漆印冒出来,像一盏小灯,她把父亲1960年的捐赠收据翻出来,137件清清楚楚,对上《江南春》的编号,打电话给南博办公室,三通,回声里一句“档案在整理,稍等”,她把收据拍照丢到微博,配一句“捐真得假,求说法”,两小时的阅读数字一直跳,评论里有人贴出旧年展签,有人问拍场的来路。
凌波的名字被点亮,是一篇2008年12月18日的旧报纸,《新华日报》写南博发现失传千年的《金刚经》抄本,出席发布会的保管部主任正是他,履历往前倒,1993年进南博,保管部科员,1997年这张调拨单签了名字,2008年主持全院账本,直播镜头伸过去,他只说一句“按程序办事”,电话那头一声忙音,屏幕停在他的侧脸。

“程序”这个词被放在说明里,南博列得一排一排,1961年有专家意见,张珩、谢稚柳那一代,看法写在纸上,说《江南春》是赝,1986年有管理办法,院里又剔伪,1997年省文化厅做了一个批复,说同意调剂处理,庞叔令盯住的是空出来的那些框,历次鉴定报告没有“注销”章,没有给捐赠人出一纸书面通知,调拨单有省厅批复,却看不到专家签字页,文物总店接收那一刻没有当场拆箱复核,直接入库,直接售卖,她问的那个点没挪开,“既然1961年就判伪,为何收据仍写‘明仇英’,我父亲签字时,南博为何不提”。
疑问顺着拍卖场的路走开,北京保利秋拍撤下一本“明四家”山水册,图录写着“源自江苏省文物总店”,香港佳士得那边,一件陈洪绶《花鸟》在预展后被买家停掉,市场里的手脚收紧,国家文物局在12月5日进驻南博,封掉1990—2010年的外拨档案,仓库角落翻出一本1997年的手工台账,有一页被撕,纸屑下面隐隐露出“江南春”,同页写着徐悲鸿《双马图》,边上一个数字6800元,买家栏里铅笔轻轻写着三个字,艺兰斋,旁边一个“丁”。

镜头第一次对准丁蔚文,地点在老门东,艺兰斋的木牌有些掉漆,她把当年的发票拿在手里,说1997年6月确实从文物总店打包买过五件处理品,有票据,有清单,问到《江南春》为何在2025年拍卖出现,她顿了几秒,说当年一并转手给香港客户,赚了两千块差价,记者追问卷尾的火漆,她侧头把头发撩到耳后,反问“火漆能说明什么,说不定是套盒带过去的”,转身进屋,门板靠上门框的声音砰一下,招牌两个字在阳光下显出裂纹。
这团事往上走,是庞鸥在12月12日贴出的长文,他把1943年的庞氏遗嘱照片贴出来,《江南春》归长孙庞增和,1959年的捐赠签字也落在庞增和,所谓“让渡”没有出处,长文里还把艺兰斋的注册时间翻出来,1996年12月成立,1997年5月就拿到首批处理品,时间挨得太近,文物总店入账的五件书画,三件在2001—2014年间回到拍场,价格一路往上走,若是赝品,市场的判断从何而来。

凌波的履历被一页页摊开,1997年之后升到副主任,2003年主持新馆搬迁,2008年做保管部主任,2016年去了省文旅厅文物处副处长,2020年返聘回南博担任学术委员,另一摞表格是“处理品”的清单,统计口径里写着1873件,548件有拍卖记录,成交额对着数字上去了6亿元,律师发来一纸声明,说所有行为都在职务范围,个人没有参股拍卖公司,也没有在交易环节拿佣金,声明后面盖着“江苏省文物局”公章的2001年个人廉政登记表。
问到具体的细节,审计组把三点单拉了出来,1997年调拨单上“赝品”用铅笔,不合档案规范,同一批书画在总店账册里写的是“明清”而不是“赝品”,定价比同期处理品偏高,签字日期是5月8日,文化厅批复是4月21日,中间空了17天,权力从哪儿接过去,凌波说铅笔是后来补记,价格是总店评估小组定的,时间差记不清,问询笔录里他连续说了七次“不清楚”,舆论里出现一个词,“凌不清楚”,各方把问题又往原始凭证上挪,想把链条对齐。

外溢效应在12月中旬往各馆扩散,苏州博物馆公布1998年曾向南博“调剂”购入一件“清王翚山水”,签字人写的是凌波,成交价1200元,这件作品在2024年拍到2300万元,苏博的声明写了两个动作,“已冻结,待上级调查”,龙美术馆、西泠印社相继自查,至少六家机构在清点中标出“源自南博处理品”的藏品,国家文物局跟进一纸通知,做一次面向全国的1990年以来“调剂”书画专项核查,涉及文物预计超过两万件,史料、账册、票据都要翻到最早的那一页。
庞叔令把维权放进司法程序,12月18日,她向南京市中院交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1997年的文化厅批复,并判令南博返还《江南春》真迹或赔偿8800万元,法院的受理通知书下发到她手里,同事把《国家文物法》旧版的条文拿出来,对捐赠文物的处置权写得很笼统,捐赠人自知道权益受损起算,诉讼时效三年,庞家在2025年起诉,时间是否溢出了边界,成了案子要解决的分歧,她对着镜头说了一句,“他们瞒了六十年,还要怪我知道得太晚”。

凌波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里,是12月20日清晨,他从鼓楼区审计署临时办公点走出来,鬓角的白发比照片更明显,手里拎着一个90年代的公文包,有记者问“是否后悔”,他停了一下,说“如果再来一次,我会在备注栏用钢笔写”,当晚他的信息被改成“南京博物院原保管部主任”,履历停在2025年12月,词条锁定,留言区有人留下“等待官方通报”,新一轮问答开始挂在时间线上。
南博院里的银杏落了一地,库房铁门贴着封条,缝隙里能看到1997年的木箱还靠着墙,侧面那行墨迹“庞捐,待处理”,仓储味道混着木头味,风吹过,封条发出轻响,像在催一声迟到太久的回应,当“赝品”两个字被写在捐赠品上,否定的是图像的真伪,还是捐赠行为本身的信任,答案要从最早那张淡绿纸开始找,找签名,找印章,找复核,找告知,程序要一项项对齐,事实把每一格填满,争议才能落地。

市场那边还在校对图录,拍卖公司在源流栏补上“南博旧藏”四个字之前多一次核验,收藏机构把库房的卡片一张张翻出来,重新写清来源,研究者把1950—2000年的鉴定体系做一次复盘,指标、方法、流程放在同一张黑板上,公众看见了就多了一层理解,捐赠者的善意在制度里被妥善接住,透明是条耐心的路,公开是把灯打开,文件、实物、账目对照能经得起多年后的回看,这样的故事就会慢慢停下脚步,落在清楚可追溯的那一行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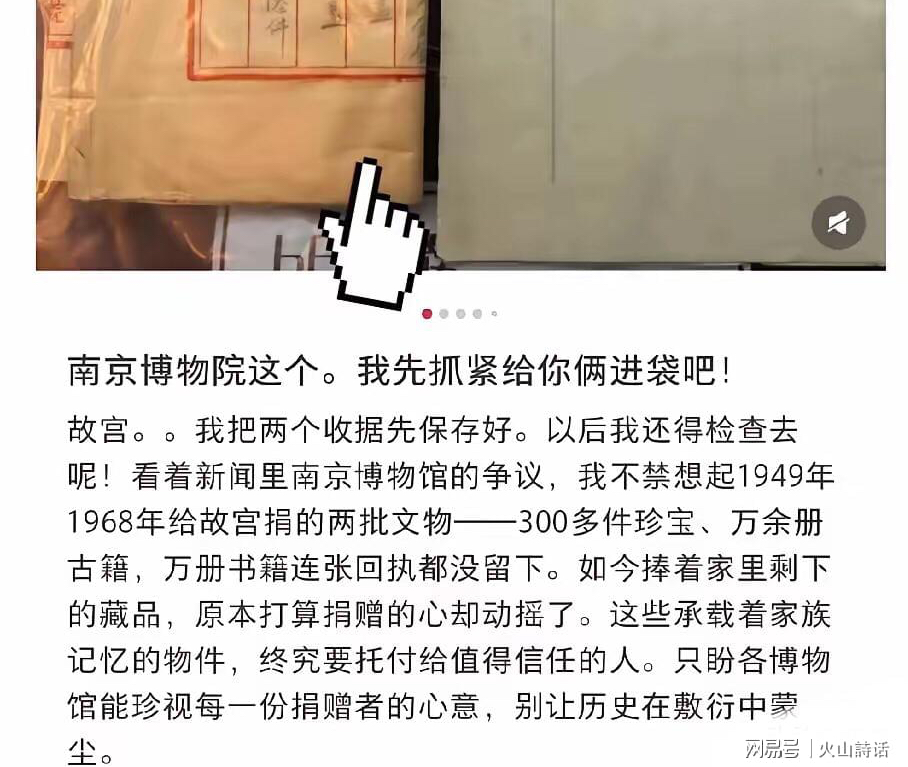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