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到老,心里头总有那么一两件合不上的旧账。
特别是张学良,这位活了一个世纪的少帅,晚年定居夏威夷,日子过得闲散。
可越是闲散,旧事就越往心上涌。
有朋友问他,汉卿兄,这辈子最遗憾的是什么?
满座皆静,等着他开口。
这位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老人,只是低头捻了捻手指,半晌才说,最后悔的,是天津那个女孩子。
要是当初敢娶了她,后半辈子,兴许就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他没提名字,但在场的人都懂。
他说的不是陪他幽居的赵四小姐,也不是那位“凤命”原配于凤至,更不是那位在欧洲重逢的蒋士云。
他说的,是一个叫梁青竹的姑娘。

1927年那会儿的天津,是个时髦的去处,洋楼、咖啡馆,处处透着讲究。
张学良正年轻,是整个北中国最扎眼的“大公子”,脚上的皮鞋锃亮,身后的随从成群。
他父亲张作霖的势力如日中天,他自己,自然也是意气风发,觉得没什么事是办不成的。
就在那时,他听闻天津的梁家藏有不少宋代名画,便以鉴赏古画的名义,登门拜访。
梁家是天津数得上的豪门,主人是买办出身,家底厚实。
张学良本是冲着画去的,没想到,画没怎么看进去,人却见到了。
接待他的,是梁家的九小姐,梁青竹。
这位梁小姐,跟别的富家千金不太一样。
她不爱随大流的旗袍,反倒喜欢自己裁一身小西装,眉眼里有股子藏不住的疏朗和自尊。
她才情也好,能用法语背诗,也能画一手好墨梅。
据说那天,张学良指着一幅画,随口说是范宽的作品,梁青竹当场就轻声纠正,“少帅,这是李唐的《万壑松风图》。”
这一句纠正,非但没让少帅下不来台,反而让他对眼前这个女孩刮目相看。
在那个年代,敢当面指出一个手握重兵的军阀统帅错误的女子,可真不多见。
梁青竹身上那股子鲜活劲儿,一下子就抓住了张学良的心。
从那以后,赏画就成了个由头。
张学良成了梁家的常客,三天两头往那儿跑。
今天说打网球,明天说喝咖啡,两人一起跳舞,一起谈天,感情迅速升温。
在张学良看来,这个梁青竹不光有才貌,更有独立的思想这让他着了迷。

感情到了份上,捅破窗户纸是迟早的事。
张学良年轻气盛,又是真心喜欢,很快就向梁青竹表达了爱意,想把她娶回家。
他大概以为,凭自己的身份地位,这事儿没什么难度。
可偏偏,他就在这儿栽了跟头。

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梁青竹是个心高气傲的女子。
当张学良提出要娶她时,她只回了一句,“你能娶我吗?”
这句反问,直接把天聊死了。
谁都知道,张学良家里已经有了一位明媒正娶的夫人于凤至。

那是他父亲张作霖拍板定下的政治婚姻,稳如泰山,根本动不得。
他能给梁青竹的,最多就是一个“姨太太”或者“如夫人”的名分。
但梁青竹是什么人?她坚持“一生一世一双人”,绝不给人做妾。
她对张学良说,要娶,就得光明正大地娶她做唯一的妻子。
一个,是无法摆脱家族和权位所限定的婚姻格局,另一个,是坚守着现代女性尊严,不肯妥协分毫。
两个人,就这么僵在了这道鸿沟面前。
张学良那一次沉默了。
他给不了这个承诺。据说,他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这一下摇头,就把所有的可能都摇没了。
恰好那时候军务紧急,一说是郭松龄反叛,张学良匆匆离开天津,这段感情也就这么搁置了下来。
张学良这一走,就成了梁青竹命运的转折点。
她不是那种能默默等待、没有名分的女人,她的性格太硬了。

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悲剧。
梁家虽然豪富,但老爷子偏偏在女儿的嫁妆上小气了一回,据说只给了四千块大洋。
这点钱,在叶家那种人家看来,简直就是个笑话。
因此,梁青竹一进门就受尽了冷眼。

她的丈夫叶查理也是个花天酒地的主儿,婚后对她百般虐待,不仅有家暴,还处处折磨她。
曾经那个神采飞扬的才女,迅速被这桩不幸的婚姻消磨得憔悴不堪。
1928年夏天,张学良和她还有过一次见面。
她只是苦笑着说,“怎么我的命是先甜后苦啊?”
他想安慰几句,她却说,“别劝了,他真的把我害苦了。”
到了这个地步,外人已经插不进一句话。
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得既突然又屈辱。
有一回,叶查理生病去青岛疗养,梁青竹也跟着照料。
在一次宴会上,叶查理不顾身体,喝得酩酊大醉,梁青竹上前劝了一句,“你病刚好,别喝太多。”
谁知,叶查理借着酒劲,当着满座宾客的面,反手就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一巴掌,打碎了她最后的尊严。
她是什么样的女子,哪里受过这种公开的羞辱。
据说她当场就离开了宴席,当晚便一个人去了火车站。
梁青竹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
在摇晃的包厢里,她想了些什么,没人知道。
或许是天津洋楼里的初见,或许是球场上的笑声,又或许是那句没能得到回应的“你能娶我吗?”。
最后,她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
她吞下了一整盒火柴头,用这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还不到二十三岁的生命。
她走后,她的五姐找到了张学良,把妹妹生前画的一幅《雪中梅花图》交给了他。
画上的梅花,在风雪里开得倔强又冷清,像极了她本人。
画轴里还夹着一张字条,只有四个字,“画给汉卿”。
拿着这幅画,叱咤风云的少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很多年过去,张学良被软禁,又重获自由,身边的人来了又走。
晚年,他对着朋友坦白,自己一生没有娶对过人,也没有真爱对过。
谈起于凤至,他说她是最好的夫人;谈起赵一荻,他说她是最患难的妻子。
唯独讲到天津那个姑娘,他总是会停顿一下,反反复复地说,“都是我害了她,她不该是这样的结局。”

夏威夷的阳光再暖,也暖不透心里那块几十年的寒冰。
他时常摩挲着那幅梅花图,喃喃自语。
如果当年他敢,如果当年他不是少帅,可惜,世上的事,从来没有如果。
那个风雪里的故事,只剩他一个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一遍遍地回想。
说到这儿,谁还会觉得他只是个风流公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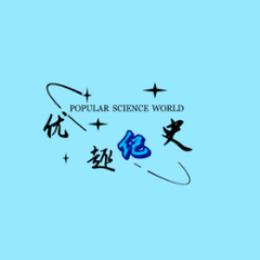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