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3月24日黎明,广西镇南关前隘山谷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中,一位白发老将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手持丈八长矛,如雷霆般吼出生命中最后的战号:“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
话音未落,他纵身跃出摇摇欲坠的长墙,身后紧随着两个持矛的儿子和千人大刀队,直扑法军阵线。
弹片如雨,70岁的冯子材须发皆张,矛尖在晨雾中划出寒光——镇南关的命运在此一搏。
冯子材的生命起点浸透贫寒的血泪。1818年生于广东钦州沙尾街的他,幼年即成孤儿,在生存的夹缝中摸爬滚打:做木工、跑牛帮、流落街头。
底层生活的淬炼赋予他一身武艺和嫉恶如仇的烈性,也埋下了反叛的种子。
19世纪中叶,两广地区天地会起义风起云涌。1850年,32岁的冯子材加入刘八领导的起义军,树起反清大旗。
次年形势陡转,他率千余人接受清廷“招安”,转身成为镇压农民军的利器。
在围剿太平天国的战场上,他因战功赫赫步步高升:都司、总兵、直至1862年擢升广西提督,获赏黄马褂。
清军悍将张国梁曾拍其背叹道:“子勇,余愧弗如!”
但官场的污浊最终吞噬了这位悍将的雄心。面对排挤倾轧,1882年,64岁的冯子材愤然“称疾解职”,回到钦州故乡。
当张树声奉命前来探访时,看到的景象令人愕然:曾经的提督“短衣赤足,携童叱犊归”,俨然乡间老农。
谁又能料到,放牛老者的胸膛里,仍奔涌着卫国御侮的热血?

法国殖民者的铁蹄踏碎了冯子材的田园梦。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势如破竹攻占越南,直逼中国西南门户。
1885年2月,法军炸毁镇南关城门,在废墟上竖起中文木牌:“广西的门户已不复存在!”
前线清军溃不成军。广西巡抚潘鼎新弃城逃跑,败兵“哭声震彻山谷”。
朝廷急诏四起,却无人能挽狂澜——直到一封请战书从钦州飞驰而至。
听闻镇南关陷落,67岁的冯子材拍案而起。他上书两广总督张之洞:“从钦州入越东北开辟敌后战场!”
获准后,他散尽家财招募子弟兵。乡民感其忠义,短短数日,一支以500钦州练勇为骨干、号“萃军”的九千子弟兵集结成军。
出征之日,冯子材指天立誓:“此行不胜,无颜见父老!”更令二子相荣、相华随军——此行实抱必死之心。
边关风雪中,溃兵们看到惊人一幕:老将军马后赫然随着一口棺木。他对将士们朗声道:“老夫此去,马革裹尸乃归宿!”
1885年3月的镇南关,风雨欲来。冯子材被推举为前敌主帅后,第一道军令便是抢修防御工事。
他相度地势,在关前隘东西两岭间督建三里半长墙,岭上筑五座炮台,构成纵深防御体系。这道土木长城,即将成为法军的葬身之地。

3月23日晨,法军司令尼格里率2000精兵,携重炮分三路扑来。炮弹如雨倾泻,东岭三座炮台相继失守,法军占据制高点向长墙猛轰。弹片在阵前堆积寸许,清军死伤惨重。
危急时刻,冯子材横矛厉喝:“退者斩!”亲率敢死队夜袭文渊城,搅乱敌阵,为决战赢得喘息之机。
24日黎明决战,法军乘浓雾总攻。千余炸弹将长墙轰出数道缺口,蓝眼士兵已攀上墙头。
此刻,冯子材突然“开壁持矛大呼”,如霹雳裂空。白发老将赤足跃出,身后二子与千名大刀队员如潮涌出。将士们见主帅父子以身为盾,“无不感奋,殊死斗”。
更令人泪目的是,关外游勇、边民千余人自发参战,越南义军也举刀杀入敌阵。
血战持续至25日,冯子材下令总攻。法军在肉搏战中溃不成军,抛下1000余具尸体、辎重无数,尼格里身负重伤狼狈南逃。
清军乘胜追击,收复文渊、谅山。诗人赞曰:“连宵苦战不闻金,枕借尸填巨港平...南人鼓舞喊嗟叹,数十年来无此战!”
镇南关大捷如惊雷震动世界。法军败讯传至巴黎,引发政治海啸。

1885年3月30日,愤怒的民众高呼“打倒茹费理”包围议会,法国内阁应声倒台。西方报纸惊呼:这是“拿破仑滑铁卢式的崩溃”!
冯子材正欲乘胜光复越南全境时,一道谕旨如冰水浇头:停战撤兵。
原来清廷竟在胜利之际签订《中法新约》,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老将军驻马边界,越南百姓“攀留哭泣”,他“挥涕不能已”。
弱国外交的荒诞剧,让英雄的热血凝成寒冰。
归国后,清廷授予冯子材太子少保衔、云南提督虚职。这位曾扭转国运的老将,终究未能扭转腐朽王朝的末路。
1903年,86岁的冯子材奉旨赴桂整军,途中中暑病逝。临终前,他是否又听见镇南关的炮声?是否想起长墙跃出时,扑面的硝烟与阳光?
今日钦州冯子材故居前,香炉青烟缭绕。雕像中的老将军目光如电,穿透百年风云。
当法国档案馆里仍陈列着镇南关败将尼格里的军刀时,广西边民口耳相传着“冯爷爷持矛杀番鬼”的故事。
1903年秋,灵柩归乡途中,沿途百姓设祭百里,纸灰如雪——民心铸就的丰碑,远比紫禁城的赏赐更永恒。
冯子材棺木出关的瞬间,已成为民族精神的图腾:一个白发将军抬着棺材走向炮火的背影,照见晚清最后一块硬骨头的锋芒。
这锋芒刺破“东亚病夫”的阴霾,昭示着一个古老文明的尊严——纵使王朝将倾,华夏脊梁犹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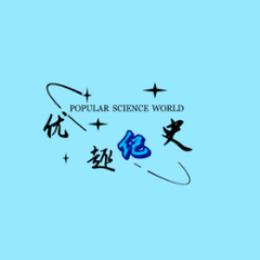
































热门跟贴